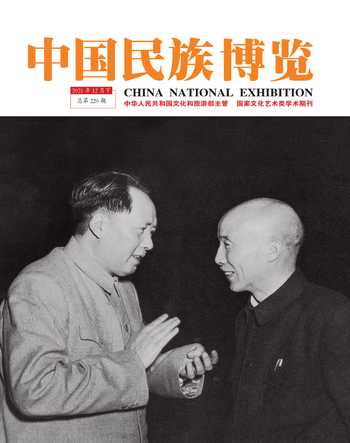試論廣西當代詩歌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建構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西民族詩歌通過對本民族民間傳說、民族英雄、歷史故事等民間文學的現代性關照,實現了民族詩歌的現代化轉型。20世紀80年代之后,廣西民族詩歌創作著力于地理文化生態表達,逐漸形成了“花山書寫”“美麗南方”等廣西經驗和廣西形態。可以說,廣西詩歌創作有效的參與了廣西民族文化建設,推動了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生新,并使兩者都朝著多元開放的方向發展,呈現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全球化視野與本土化意識的有機整合。
【關鍵詞】當代詩歌;民族文化;民族傳統
【中圖分類號】I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24-059-03
【本文著錄格式】封艷梅.試論廣西當代詩歌對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建構[J].中國民族博覽,2021,12(24):59-61.
一個民族的文學必定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同樣的,一個民族文化的建設也離不開文學的建構。當前,面對復雜多變的全球化、商業化環境,民族文學如何參與和推動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廣西是以壯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詩歌創作在廣西民族文學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對其研究多集中在文學本體研究,當然也有學者注意到廣西詩歌對廣西民族文化的作用,如羅小鳳認為廣西詩歌的發展對民族文化具有積極的重要作用[1],但具體如何作用卻未論述。對此,本文從整體性角度,探討廣西民族詩歌創作如何堅守民族精神,傳承與發展、豐富與生新廣西民族文化,實現廣西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
一、民間文學的現代性轉化
中華人 共和國成立后,廣西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本土少數民族詩人,如韋其麟(壯族)、苗延秀(侗族)、包玉堂(仫佬族)、蕭甘牛(壯族)、儂易天(壯族)等,他們在田野調查和采風中,重新發掘和整理了各民族民間敘事詩,創作出一系列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品,改變了以舊體詩詞創作和古漢語創作為主的廣西詩歌格局。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壯族詩人韋其麟,他的民族敘事詩《玫瑰花的故事》(1953)、《百鳥衣》(1955)、《鳳凰歌》(1964)等,對壯族民間神話傳說、英雄故事等原型意象進行了再創作,充分展現了其對壯族傳統敘事詩意象的吸收、借鑒及轉化[2]。具體而言,詩人們對民間文學的借鑒與改造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重寫民族神話
詩歌創作將民族神話意象作為現代生活重新書寫的方式,實現了民族神話與當代現實的奇妙鏈接。以韋其麟的創作為例,《百鳥衣》圍繞“百鳥衣”這一“神話意象”,重新書寫了壯族民間傳說,詩人將“百鳥衣”作為“神衣”來再現,“你看羽光亮閃閃/百鳥衣是件神衣/九洲里頭找不著/尋遍四海難得到”“穿了百鳥衣/老頭也變得后生俊俏/穿了百鳥衣/姑娘見了心歡就會笑” [3],這件具有無限神力的“百鳥衣”,最終幫助古卡戰勝了邪惡的土司。一方面,詩人整理講述這個經典的壯族神話傳說,另一方面,詩人又濃墨重彩地展示了“百鳥衣”的力量。《玫瑰花的故事》講述了尼拉與夷娜之間的悲劇愛情故事,兩人反抗國王和王子的“霸權”,最終撞向石臺生成了“玫瑰花”這一“有刺的奇花”。“玫瑰花”這一“神話意象”被詩人賦予了鮮明的壯民族特征。
(二)重建民族英雄
中華人 共和國后,廣西涌現出一系列英雄敘事詩,它們大都取材于壯族近現代民間傳說,重書了一系列近代壯族兒女的歷史故事。代表性的作品有:《郁江的懷念》書寫了郁江自太平天國到中華人 共和國成立期間的廣西歷程;《平天山傳奇》歌頌了太平天國時期壯族農民領袖黃鼎鳳領導的農民起義;《紅水河邊的故事》歌唱了赤衛隊與人民共同抗擊敵人的英勇氣概;《鳳凰歌》則立足于1949年前壯族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的戰斗生活,塑造了達鳳這位由壯家孤女成長為游擊隊的女英雄,是“民族文學創作上的新成績,是一曲優美動人的民族頌歌”[4]。這些歷史傳說經過詩人們的再創作,不僅建構出獨具壯族特色的英雄人物,也有效強化了民族地區的精神向度,影響著后人對民族歷史的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至今耳熟能詳、廣為流傳的民族英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文學不同程度的參與建構,可以說,對民族英雄的書寫是文學參與文化建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總之,中華人 共和國后的廣西詩歌創作對民族神話、民間傳說和民族英雄故事等進行了重寫與創新,完成了廣西詩歌從民間“韻體詩歌”至新詩的“民族書寫”的現代轉換。
二、民族精神的現代性重塑
1985年在文學領域興起了一股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文化尋根浪潮,作家們博采志怪傳奇、民間民俗、風物傳說等民間資源,同時又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在西方現代性的追索中不斷挖掘民族古老文化之根。廣西的民族詩人們以真切的民族情感、清醒的現代意識和理性的哲學思考為創作基礎,以壯族文化發源地“花山巖畫”與現代南方城市為視角,在詩意的想象中,尋找本民族歷史文化之根,重建民族精神。
(一)花山書寫
廣西左江花山巖畫主要分布在左江流域的寧明、大新等壯族聚居地的江河轉彎處的石壁上,其中寧明縣明江花山崖壁畫規模最為龐大,巖畫生動的再現了廣西壯族先民古老的駱越人的社會生活,這也成為當代廣西民族詩歌的源泉。1985年詩人楊克、梅帥元受到花山巖畫的啟示,提出了“百越境界”,創作出《走向花山》(楊克)、《巖畫與河》(聶震寧),一時間,廣西詩人集中于“花山”主題開啟了花山書寫。1992年在寧明花山出生成長的壯族詩人黃神彪創作了長篇散文詩《花山壁畫》,引起了全國轟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和文藝報社聯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成功舉辦作品討論會。《花山壁畫》展現了古駱越的民族史、布洛陀神的誕生,駱越民族的民族英雄布伯、岑遜、候野等,以及布洛陀傳說。從某種程度上說,《花山壁畫》將“花山”這一地理意象轉化為廣西民族詩歌創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將花山書寫推向一個高峰。1996年,廣西舉辦了“花山會議”,集結了20世紀90年代的廣西文藝家、民族詩人,從此花山書寫從文學邊緣走向了中心,花山書寫的原始性、神秘性、儀式感、民族性的群體意象與想象成為廣西詩人創作的重要意象,延續至今[5]。“花山”這一民族物質文化遺產,在廣西作家的努力下,以文學獨有意蘊豐富了壁畫的文化內涵,有效的實現了壁畫與文學的相互轉化和相互闡釋,構筑出昂揚向上的壯族民族精神。
(二)美麗南方
如果說“花山”書寫指向民族歷史,是一個民族的過去,那么對美麗南方城市的書寫,便是在當下城市化的現場,詩人們試圖對民族精神進行重建。詩人楊克作為“南方城市中靈魂的書寫者”,其創作具有典型性。他的詩以客觀、平靜的心態去觀察和記錄城市的每一處變化。南方在改革開放初期,新鮮事物層出不窮,詩人在《在地面和天空之間》中寫道,“股票,招標……迷離的聲音和色彩結構了神奇的多層次的南方。”改革的魔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影響南方大部分城市的原始面貌,“南方的岸,最早露出可以觸摸的希望”[6]。另一位城市書寫較為出色的是“自行車”詩人領軍人物非亞,他以城市生活常見的道路、建筑物、地點等各種“場所”來建構詩歌的當下性和現場感,《江南路,我看見一個長發青年在單杠上抽煙》《暮色中的城市》《每天的一些記錄》等,這些詩作直觀地反映了廣西的城市化進程,表達了詩人獨特的思考。[7]
總體而言,廣西民族詩人向著本民族歷史“尋根”,向內挖掘民族歷史敘事的內核,提煉出具有廣西民族特色的書寫意象——“花山書寫”,同時又探索城市建構與鄉土敘事中的“廣西形態”,逐漸形成別具一格的“廣西經驗”。
三、詩歌創作的“廣西經驗”與反思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摸索,廣西詩歌創作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經驗:在取材上,民族歷史、神話傳說、民俗風情、自然風物等都被納入詩歌關照的對象,極大的拓展了新詩的表現范圍;在精神向度上,廣西民族詩歌在民族精神的追尋中,逐漸爬梳出廣西特色民族文化符號,如“花山”“劉三姐”“壯錦”等,這些民族文化符號,極大的提升了廣西民族文化標識,使廣西成為鮮明的“這一個”;在創作追求上,廣西詩歌創作一直伴隨著新詩現代化的腳步,在全球化語境中,逐步建立起一種少數民族文人創作,既從本民族文化、民間文學中吸取養分,又從西方現代文學創作中尋求共識與突破,形成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格局。
首先,注重本民族文化意象的開掘。21世紀以來,當代詩歌從語言到形式呈現出多元的探索。可以說,從社會的劇烈變化和從兩元對立的書寫模式,急劇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如何將這種形而上的精神新質落實到形而下的具體書寫中,是新世紀詩人創作的難點[8]。對此,廣西民族詩人馮藝、黃堃、許雪萍、費城、林虹等,強調詩歌的存在感和體驗性,強調一種熱衷于解構單一維度的現實再重構多維度現實的寫作姿態,進一步深向人的內卷,探索時代精神解構的源頭,開創出一種廣西21世紀的民族詩歌突圍發展困境的可能[9]。他們的創作中出現了多種廣西的地域文化元素,諸如壯錦、銅鼓、繡球、儂智高、木棉樹、酒、古道、映山紅、鵝泉、紅楓、火塘等,這些地域文化元素因語言文字作為傳播介質已轉化為一種“文化意象”,在詩人們的作品中以較為原生態的狀態呈現,并通過與時尚元素的結合而具有了超越于區域原生地的現代文化形象。如歌劇《壯錦》以廣西物質文化遺產壯錦、銅鼓等民族意象的傳說為內容,又跳出傳說的敘事范圍,創造陌生化的歷史語境,展現了當代廣西民族文化精神。
其次,民族詩歌現代性表達的多元探索。隨著數字科技飛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民族文化傳承面臨著諸多困境,甚至出現部分民族文化面對主流文化的消退。在詩歌創作中,廣西的民族詩歌話語權也在這股潮流中進一步收縮陣地,是否能夠融入世界文化潮流中又堅守原有的民族文化個性,成為了每一個民族必須面對的問題。 為此,廣西民族詩人從個人經驗出發,以審美現代性對抗科技文明日新月異的網絡大數據的擴張,通過現代性意象、語言與修辭策略,書寫城市人的孤獨、焦慮等情感。如壯族詩人譚志表的詩集《泣血的飛翔》,以一位少數民族詩人的身份,對社會人生進行了飽滿哲理的思考,讓人深深感受到詩人向上、向善、向美的追求。詩人方學平詩選集《最后的麥子》,展現出新鄉土詩的獨特藝術追求,詩人也被稱為是“最后一粒風塵滿面的麥子”“山頂寒風和陽光的堅守者”。
再次,自覺探索民族共同體命題。詩歌在當代文學文類中,越來越居于邊緣,這已是當前的共識,而少數民族詩歌創作,更是處在邊緣的邊緣。但邊緣/中心的位置,也許是少數民族詩歌新生的契機。當下,民族詩人在民族書寫的轉向上,轉而尋求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在創作實踐中,注重民族文學共同體的建構,在歷史與現實生活中尋求民族精神的詩意表達。如廣西青年詩人湯松波跳出廣西民族詩歌的范疇,創作出的長篇組詩《東方星座》,有意隱去個體及單一民族的書寫方式,直接以56個民族、56首詩的形式,框架式地描畫出國家民族團結進步的多彩畫卷,全面展現和歌頌祖國大家庭56個民族團結共榮、和諧發展,十分富有時代風貌。
最后,傳播方式的多樣化開拓。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也改變著詩歌的傳播方式,詩人們通過詩歌記錄廣西的民族文化情感,以詩歌民族文化符號為基點,又將文化符號和視聽語言融為一體。如“岜萊詩會”采用以刊聚詩的方式,聚集廣西漢族、壯族、侗族等各民族的詩人117位,強調詩歌創作地域融合,關注現實熱點,常常采用多媒體聯動發布的方式,讓詩歌能夠實時地通過微信、微博、網絡平臺的線上推廣等,以及詩歌朗誦會、詩歌研討會、詩歌鑒賞讀書會等線下面對面的多種傳播形式,極大的擴展了詩歌的影響力,“岜萊詩會”已成為廣西詩歌創作、交流和展示的重要平臺之一,也成為廣西詩歌生態的一塊標志性的文學高地。
四、結語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魅力不僅在于作家筆下的詩情畫意的民族書寫,更在于文本和歷史之間,當下與歷史之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塑造的過程。一方面通過詩歌中的想象、比喻、象征等對歷史的超越能力,原生態的在作品中復原出民族、地域文化中的物質精神力量和民族形態;另一方面,從現實生活關系的基礎之上,生化出一種宏觀、超然、橫跨于真實生活關系的基礎之上的理想精神,超越現實和歷史規范的自由,在對民族的神話、歷史、語言以及文化智慧、生命體驗等元素的結構中,從鞏固發展民族團結、邊疆書寫和民族文化傳承等方面建構起一個新時代的民族譜系。可以說,廣西民族詩歌創作,承擔著民族文化傳承的重任,又不斷開掘新時代民族之魂,內化與重塑民族文化,進而持續推動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
參考文獻:
[1]羅小鳳.邊地的詩意堅守與曲折發展——廣西詩歌 60 年回顧[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
[2]董迎春,覃才.新世紀廣西青年詩歌觀察[J].河池學院學報,2019(4).
[3]韋其麟.百鳥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4]黃桂秋.論韋其麟《鳳凰歌》的民族特色[J].南寧師范學院學報,1982(4).
[5]黃偉林.從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廣西文學巡禮[J].南方文壇,2004(4).
[6]楊克.在地面與天空之間[J].詩刊.2008(9).
[7]羅小鳳.建構詩與現實生活的通道——論世紀初非亞的詩歌創作[J].梧州學院學報,2015(4).
[8]莫付歡.廣西新世紀詩歌發展問題研究[J].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20(2).
作者簡介:封艷梅,女,陜西渭南人,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廣西民族大學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華文文學。
317650190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