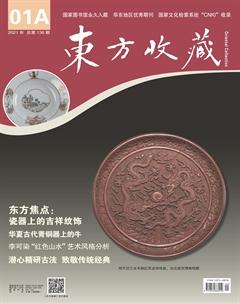河北出土唐三彩初步研究(下)
穆俏言



毗鄰河南的邯鄲地區
邯鄲位于河北省最南端,向北距內丘縣(邢窯)、向南距鞏義市(鞏縣窯)皆不足100公里。邯鄲市、曲周縣、臨漳縣、磁縣以及峰峰礦區都出土過唐三彩。
圖1,三彩三足爐,邯鄲市出土。高16、口徑12.5厘米。侈口,短頸,肩部有一道弦紋,鼓腹,三獸蹄形足。以白色為基調,交錯點染綠、棕黃色釉彩,形成斑駁淋漓的自然斑塊。
圖2,三彩缽,邯鄲市出土。高12.6、口徑12.4厘米。斂口,近口沿處有一道弦紋,鼓腹,小平底。外壁上半部分交織點染綠、棕黃、黃三色釉彩,形成自然流淌的條狀斑塊。
圖3,藍彩三足爐,曲周縣出土。高12、口徑11厘米。侈口,短頸,鼓腹,三獸蹄形足。以白色為基調,內口沿相間點染藍色斑塊,肩、腹部隨意點染出大小不等的藍色斑塊。
圖4,綠黃釉印花菱花口把杯,臨漳縣出土。高7、口徑7.5厘米。菱花形侈口,杯身呈扁圓形,一側安樹枝狀曲柄,平底。采用模制成型,杯外壁模印纏枝花卉,外口沿模印斑點紋。外施綠釉,內施黃釉。
圖5,三彩三足爐,臨漳縣出土。高12、口徑12.5厘米。侈口,短頸,鼓腹,腹部有一道凸弦紋,三獸蹄形足。口、頸及下腹部以棕黃色為基調,點白色斑點。上腹部以綠色為基調,用白色涂畫出三角形圖案,空白處點白色斑點。
圖6,三彩缽,磁縣出土。高13、口徑12厘米。斂口,鼓腹,小平底。外壁上半部分交織點染綠、黃、白三色,釉彩相互交融,斑塊形態變化無常,自然生動。
圖7,黃釉三足盂,峰峰礦區出土。殘高6、口徑4.4厘米。侈口,圓唇,溜肩,鼓腹,三足,覆盤形蓋,頂部鈕殘缺。通體施棕黃色釉,釉色深淺不勻。
河北出土唐三彩年代和產地的初步研究
河北本身就是唐三彩產地之一,南部區域距鞏縣窯不足百里,以洛陽為中心點的隋唐大運河流經河北五市總長近600公里,因此河北境內出土的唐三彩既有本地產品,也有河南鞏縣窯的產品。考慮到陜西唐三彩的服務對象主要是當地的皇親國戚,加之距離、運輸、成本等因素,輸入河北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亦不能完全排除。
(一)邢窯及周邊區域
目前河北三個燒造唐三彩的窯場中,邢窯遺址出土標本以及窯址周邊墓葬出土的三彩器最豐富。因此邢窯應當是河北燒造唐三彩規模最大的窯場。考古資料顯示,邢窯第三期(唐代早期)和第四期(唐代中期)的地層中,都發現了三彩器和模制的人俑、馬俑等。在窯址調查和發掘過程中,陸續出土了數量可觀的三彩標本(圖8)。在邢臺市、內丘縣、臨城縣的唐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三彩器。其中紀年墓葬有臨城縣東賈村唐調露元年墓(679)、邢臺市董村水廠唐大和五年墓(831)、臨城縣唐中和三年墓(883)等。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看出,邢窯至少從七世紀后期就燒造三彩,一直延續到九世紀。產品以日常用品為主,常見器物有爐、缽、盤、碗等。用于隨葬的人物俑、動物俑不僅數量少,尺寸也相對較小。內丘縣城東高速公路唐墓出土的侍女俑和鎮墓獸,高度都只有20厘米左右(圖9、10)。
邢窯燒造的日用三彩器在造型和裝飾技法方面與鞏縣窯有很多相似之處,如三足爐和缽,都與鞏縣窯產品非常相似。但總體來看邢窯三彩的色調與鞏縣窯相比顯得較為暗淡,光澤度較差,施彩手法也相對簡單。有學者對邢窯與鞏縣窯三彩釉料成分做過對比分析,發現邢窯三彩釉料鉛含量相對較低,這一點很可能是導致其色調暗淡的重要因素(圖11、12)。
邢窯三彩的流布范圍主要涵蓋邢臺市、內丘縣、臨城縣以及邯鄲地區,上述地域出土的唐三彩大多與邢窯遺址的三彩標本相似,但此區域內(特別是邯鄲地區)也出土有鞏縣燒造的唐三彩。
(二)井陘窯及周邊區域
井陘窯遺址自1989年發現以來進行過多次考古調查和局部發掘,但由于窯址發掘報告尚未發表,燒造三彩的具體情況還不清楚。不過井陘縣及周邊區域的唐墓出土了數量可觀的三彩塔形罐和鳳首壺,其獨特的風格與邢窯、鞏縣窯皆不相同,應當是井陘當地燒造的產品。
井陘窯燒造的三彩大多以淺綠色為基調,點染深綠、黃和棕黃色,單一色調的綠釉器多為深綠色。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藍彩。井陘窯釉彩色澤與邢窯相似,發色相對比較暗淡。施彩手法簡單粗放,多采用隨意涂點的方法,形成自然垂流的斑塊。塔形罐數量最多,罐身造型基本一致,口微侈,直頸,溜肩,深腹,圈足。鳳首壺的口部并不捏成鴨嘴形而是保持圓形,壺蓋也是在圓形基礎上堆塑出眼、喙、冠等。這些都是井陘三彩的地方特色。
井陘比較重要的唐、五代墓葬有井陘縣南陘鄉唐李氏墓(墓志記載下葬時間為天祐十五年,公元918年)和井陘礦區白彪村晚唐墓。李氏墓出土了4件三彩器,包括1件鳳首壺和3件塔式罐。白彪村兩座墓葬出土了十余件綠釉陶器,除了塔形罐外還有仿金銀器造型的海棠形杯、花口高足盤等。根據墓葬形制以及出土資料的排比,井陘窯燒造三彩的時段大約在晚唐至五代時期。產品流布涵蓋井陘縣、石家莊市、正定縣。上述地域出土的三彩大多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但亦不排除有少量邢窯和鞏縣窯的產品。
(三)定窯及周邊區域
在河北三處燒造三彩的窯場中定窯的資料最少。2009年對定窯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出土了少量三彩標本,經過修復可以還原形狀的有兩件爐(圖13、14)。當地墓葬出土的資料也不多,但曲陽澗磁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形罐和鳳首壺造型繁復,工藝精湛。兩件器物都是先在胎體上裝飾跳刀戳點紋和席紋,然后加施綠、黃、棕黃色釉彩。這種胎裝飾與釉彩裝飾相結合的獨特工藝極為罕見,可以看做是定窯三彩的地方特色(圖15、16)。在河南、陜西以及邢窯、井陘窯燒造的三彩中,均未見胎體上裝飾席紋的,這一點似乎可以看做定窯三彩的地方特色。澗磁村出土三彩塔形罐與鳳首壺的唐墓中還出土了二十余件精美的定窯白瓷,品種有盤、碗、海棠式杯、盒、茶碾等,其中有兩件塔形罐和一件鳳首壺(圖17)。根據同出白瓷的時代特征,結合窯址發掘出土三彩標本的地層關系,定窯燒造三彩的時段與井陘窯大體相同(晚唐至五代),但產量遠不及井陘窯。
(四)張家口蔚縣地區
蔚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境內曾發現過金元時期窯址,但未見燒造唐三彩的窯址。蔚縣多地唐墓出土了數量可觀的綠釉塔形罐和鳳首壺,體型高大,裝飾華美,多數采用單一綠彩。蔚縣三彩大量采用模印堆貼的裝飾手法,其風格與山西北朝墓葬出土的釉陶器頗為相似。這種有別于中原地區的裝飾風格,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色(圖18)。
蔚縣出土的綠釉塔形罐和鳳首壺高大易碎,不適于長途運輸,應當是本地窯場燒造。距蔚縣不遠的山西大同唐墓中也經常出土塔形罐和鳳首壺,但基本上都是彩繪灰陶,可見蔚縣綠釉陶器供應的區域非常有限。根據古代瓷窯大多距河流不遠的規律,燒造這種綠釉陶器的窯場應該在蔚縣境內的河流附近。發源于山西廣靈縣的壺流河自西向東流經蔚縣,燒造三彩的窯場很可能就在河流兩岸的某個地方。
蔚縣三彩出土地點非常集中,全部在蔚縣境內。目前發現的唐墓已有十幾座,其中紀年墓葬有貞元元年(784)、會昌元年(841)、大中十年(856)等,大致涵蓋了中晚唐時期。
(五)隋唐大運河流經地域
隋唐大運河流經河北東南部的5市(邯鄲、邢臺、衡水、滄州、廊坊),其中滄州段流經吳橋縣、東光縣、南皮縣、泊頭市、滄縣、滄州市區(包括運河區和新華區)、青縣共八個縣(市、區)。衡水段流經故城縣、景縣和阜城縣。河北東南部出土的唐三彩主要集中在大運河流經的這兩個區域,并通過與運河相交匯的河流向周邊擴散。
滄州、衡水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唐三彩品種豐富,釉色光潔鮮艷,很多器物與鞏縣窯三彩的相似度很高。例如泊頭縣出土的藍彩弦紋碗(圖19上)、三彩印花洗(圖20上),黃驊市出土的三彩水注(圖21左),衡水市出土的三彩豆形爐(圖22上),任丘市出土的三彩三足爐(圖23上)等,都能在鞏縣窯遺址出土的標本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器物。上述地區之所以大量出土鞏縣窯唐三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運河水運的便利。相比之下,河北本地生產的唐三彩在東南部區域反而較少。
(六)邯鄲地區
邯鄲位于河北最南部,著名的磁州窯就位于磁縣和峰峰礦區一帶。由于磁州窯遺址的考古發掘尚未發現唐三彩,因此目前尚無磁州窯燒造唐三彩的證據。從地理位置的角度看,這里恰好處于邢窯和鞏縣窯之間。大運河由邯鄲入境河北,流經魏縣、大名縣和館陶縣。因此,邯鄲境內出土的三彩既有鞏縣窯風格的產品(圖24),也有邢窯風格的產品(圖25、26)。
結語
河北是唐三彩的產地之一,邢窯、井陘窯、定窯都生產過三彩產品,其中以邢窯燒造規模較大。邢窯三彩在造型與裝飾方面與鞏縣三彩有諸多相似之處,但釉彩明顯不如鞏縣三彩明亮艷麗,品種也不如鞏縣窯豐富。井陘窯三彩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中以塔形罐和鳳首壺最具特點。釉彩與邢窯一樣偏于暗淡,施彩手法簡潔粗放。邢窯、井陘窯三彩以綠、黃、白色為主,邢窯還有少量藍彩。
此外,邢窯單一釉色產品有黃釉和綠釉器,井陘窯則僅見色調濃重的綠釉器。定窯三彩資料雖少,但曲陽澗磁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塔式罐和鳳首壺頗具特色,尤其是胎體上裝飾的跳刀戳點紋和席紋,在唐代三彩器中極為罕見,精美復雜的造型也充分彰顯了大型窯場高超的工藝水平。蔚縣唐墓出土的三彩器主要以綠釉塔形罐和鳳首壺為主,器型高大,裝飾華美,大量采用模印貼花,表現出與中原地區明顯不同的地域特色。目前燒造蔚縣三彩的窯場尚無線索,從出土地點集中在蔚縣來看,窯場很可能就在蔚縣境內。
河北三彩的燒造時間以邢窯最早,大約從七世紀后期一直延續到九世紀。其他幾處窯場(包括蔚縣)大多在晚唐五代時期。河北諸窯燒造三彩的規模普遍較小,產品主要供應距窯場較近的周邊區域。
河北出土的外來唐三彩主要集中在衡水、滄州以及邯鄲等東南部地區,這種現象顯然與運河有關。隋唐大運河的起點和中心在洛陽,鞏縣三彩經水路運往北方十分便利,衡水、滄州是南運河的重要地段,沿線區域出土鞏縣三彩的數量明顯超過了河北本地三彩。
由于資料搜集的局限性,特別是窯址考古發掘資料相對較少,本文對河北出土唐三彩的分析研究僅僅處于初級階段,希望隨著新資料的不斷補充,使我們對河北唐三彩的認識更加清晰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