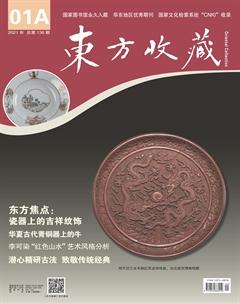以俗入佛:敦煌第98窟經變圖及供養人像釋讀


摘要:敦煌第98窟是五代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于公元914至924年間營建的功德窟,為曹氏歸義軍時代的代表性大窟。曹議金作為98窟“窟主”,從張承奉手中承繼歸義軍政權,外有回鶻、于闐、吐蕃等各民族政權的包圍,內部則是政權甫立,人心動蕩,統治不穩。面對內外困局,曹氏政權尊佛鑿窟,注入政權正統、和平邦交、團結內部的政治理念,凸現“托西大王”的政治野心。顯然,這些訴求在第98窟壁畫之中有強烈表達。本文選擇第98窟維摩詰經變圖以及供養人像,通過考古學、圖像學、文獻學方法進行初步闡釋。
關鍵詞:敦煌第98窟;經變圖;供養人像;象征性
曹氏歸義軍時期,崇信佛教。在曹氏的120年主政中,莫高窟開鑿41個新窟,重修248個舊窟,開啟敦煌石窟發展新高潮。新窟開鑿追求唐時代的恢宏大氣,多為大型石窟。形制上,洞窟多為晚唐風格的中心佛壇-覆斗頂殿堂窟結構,窟頂四角鑿淺龕繪制四大天王像。壁畫藝術方面,繪制精美,主題多元,涉及四大類:表現佛、菩薩與天人等的尊像畫;融匯當時流行俗講、變文內容的近20種經變畫;寫實風格的山西五臺山、于闐牛頭山佛寺等佛教史跡圖;大量身形高大、凸現權貴的供養人畫像。彩塑則由于此階段洞窟多開鑿于下層,幾經盜擾,幾乎沒有保存。
敦煌第98窟是曹氏歸義軍時代的代表性大窟。該窟為五代時期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于公元914至924年間營建的功德窟,敦煌遺書稱其為“大王窟”。第98窟為大型中心佛壇洞窟,窟前建有殿堂,長甬道,敞口前室,方形主室,覆斗頂。該窟壁畫內容豐富,繪制精美。前室壁畫殘毀不明,甬道頂部為佛教史跡及瑞祥圖,甬道南北壁為供養人畫像,主室東壁為維摩詰經變圖,主室西壁為勞度叉斗圣變圖,主室南壁為阿彌陀、法華等經變圖及曹氏女供養人像,主室北壁為華嚴、賢愚等經變圖及曹氏女供養人像,窟頂為千佛、十方佛等尊像畫。沙武田先生認為,之后開鑿的曹氏歸義軍洞窟,其結構布局、壁畫內容是第98窟風格、特征的延續,可見第98窟極具開創性。“窟主”曹議金面對張承奉金山國政權所遺留的內外交困局面,采取對外謀求和平、對內團結軍民的統治方略。該方略亦成為第98窟壁畫創作的重要指導。“維摩詰經變圖”“非曹氏幕僚供養人像”等壁畫內容都是這一統治意志的表達。
面對該現象,筆者選擇第98窟中的維摩詰經變圖以及供養人像,利用考古學、圖像學等方法汲取壁畫信息;結合文獻學,綜合分析敦煌石窟藝術特征和曹氏歸義軍所處的時代語境,對第98窟及其“窟主”進行解讀嘗試。
敦煌第98窟經變圖及其象征性
1.維摩詰示疾圖(圖1)
經變圖位于窟內東壁門北側位置,出自《方便品》。壁畫中維摩詰作老居士形象,稱病在家,坐于帳中,羽扇綸巾,與前來問疾的文殊眾人對話。維摩詰在佛教經典中是一位具有無盡財富以及極高威望的長者形象,儼然一位世俗世界的帝王。這恰好對應了窟主曹議金“托西大王”的政治身份,而圍繞在其周圍的聽眾及各國王子象征著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
2.文殊師利問疾圖(圖2)
經變圖位于窟內東壁門南側位置,出自《文殊師利問疾品》。維摩詰稱病,文殊受佛陀特派前去探病,二菩薩論說佛法,互斗機鋒,一旁的菩薩、羅漢、王公大臣為之嘆服。文殊師利問疾圖正是表現了這一中國佛教藝術獨有的經典壁畫題材。前來問疾的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在畫面布局上具有同等位置,當是與曹議金有著同等身份和權勢的另一個政治實體。文殊師利在佛教中的超然地位和《維摩詰經》中塑造的外來者形象,推測象征一位實際權力高于曹議金的非曹氏家族成員。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文殊師利可能是甘州回鶻政權。
3.各國王子圖(圖3)
經變圖位于窟內東壁門北側偏下位置,出自《方便品》。壁畫中各國王子問疾、聽法,前行兩組為來自南海一帶的黑膚王子,其后是回鶻、于闐、龜茲、吐谷渾等西域王子形象,拱手而立的則是漢族藩鎮官員像。曹氏歸義軍時期,面臨著與吐蕃、于闐、回鶻、 吐谷渾、 龍家等眾多民族政權的復雜關系。團結外邦,結善諸友是當時曹氏歸義軍政權的外交取向,亦是各國王子圖象征性所在。
4.饒益眾生圖(圖4)
經變圖位于主室東壁門上,出自《維摩詰經·方便品》,由七組圖構成,描繪了維摩詰對婆羅門、王子、長者、大臣、宮女等群體的教化,表達維摩詰“饒益眾生”之意。這是窟主曹議金借用《方便品》圖像中維摩詰對權貴階級的說教,傳遞團結幕僚、上下一心的企盼。
敦煌第98窟供養人像及其世俗性
1.曹議金像(圖5)
圖像位于甬道南壁,繪曹議金及曹氏家族人物像。曹議金被認為是粟特人,公元914年取代張承奉為歸義軍節度使。自公元914至1036年,歷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北宋,轄域為瓜、沙二州六鎮。曹氏歸義軍政權系漢民族占據主體的多民族混合政治實體。曹議金奉中原為正朔,對外關系上利用姻親結交友邦,娶甘州回鶻可汗的圣天公主為妻,一女嫁于闐國王李圣天,一女嫁甘州回鶻可汗。在曹議金內政外交努力下,其當政時期出現了刀兵罷散、四海通達的景象。作為曹議金的功德窟,第98窟在瓜沙地區的地位不亞于中原皇家石窟,其規模之大、壁畫之精美多元、題記之豐富,無不在彰顯其政治地位、經濟能力以及對瓜、沙二州六鎮的控制力。
2.回鶻公主供養像(圖6)
圖像位于窟內東壁門北側位置,繪回鶻公主等男女供養人七身,并附有題記:“敕受汧國公主是北方大回鶻圣天可……”若參照第100窟及第61窟有關題記的結銜,應是“敕受汧國(或秦國)公主是北方大回鶻圣天可汗的子隴西李氏”。該公主為甘州回鶻可汗之女,曹議金夫人,與曹議金同為此窟的窟主。公元911年,張承奉無力抵抗甘州回鶻進攻,無奈向回鶻可汗求和,奉可汗為父,甘州回鶻和歸義軍政權成父子之國。同時,甘州回鶻扼守曹氏東通中原的要道,這關乎曹氏歸義軍向中原朝貢、與中原經貿能否順利進行。面對回鶻之患,曹議金通過娶回鶻可汗之女為妻穩固了與甘州回鶻關系,后將女兒嫁予新任回鶻王,將城下之盟的頹勢扭轉,并為東進中原提供保障。
3.于闐國王、王后像(圖7)
圖像位于窟內東壁門南側偏下位置,繪于闐國王李圣天等男女供養人十一身。于闐國王像高2.82米,氣宇軒昂,頭戴冕旒,身披襄服。圖像中著王后裝的女供養人為李圣天之妻,曹議金之女。于闐國王像旁有墨書:“大明天子即是窟主”。這個墨書極具誘導性,似乎表明第98窟窟主是于闐國王,而非曹議金。事實上,于闐王李圣天畫像是第98窟建成之后的補繪作品。沙武天先生認為,當時曹氏政權迫于交好于闐的政治動機,進行政治聯姻拉攏于闐政權,并把李圣天畫像入窟,假稱其“即是窟主”。但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洞窟供養人畫像的位置與身份地位緊密關聯,節度使級別的尊者往往置于甬道位置,而不是李圣天所出現的洞窟主室東壁。當時曹氏面對東部甘州回鶻的盛氣凌人,自然重視向西與于闐謀求發展。兩個政權互通姻親,互派使節。史載沙州“于闐使”“于闐僧”往來無滯,曹氏亦有使節前往于闐。于闐太子久居敦煌,并為父王李圣天營建功德窟便是兩家密切關系的寫照。
4.張議潮、索勛像(圖8)
圖像位于甬道北壁,為張議潮、索勛形象。張、索為曹氏掌權前沙州統治者,張議潮為曹議金外王父,索勛是其岳父。第98窟將他們的供養人畫像置于曹議金像對面,寓意政權傳遞合乎法理。
5.幕僚畫像(圖9)
圖像位于主室南北兩壁西端、西壁及背屏后部的最下方。第98窟現存供養人畫像292身,數量僅次于北周第428窟。其中,非曹氏家族供養人236身,幕僚200身。如此高比例地將非家族的幕僚繪制于家族窟里,在敦煌石窟中非常罕見。同時,這些幕僚身份非常明確且趨同,即都是政權構成的主干力量。曹議金通過在功德窟的這種有意營造,顯示了其拉攏幕僚,穩定政權的意圖。正如其在第98窟功德發愿文《河西節度使尚書曹議金貞明六年(920)修成大窟上層功德記》中所愿:“府僚大將,各盡節于轅門;親從之官,務均平而奉主。”這種強調世俗政權、貫徹政治意志的供養人像,具有明顯的以俗入佛特征。
敦煌第98窟之“以俗入佛”
公元914年,曹議金接任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公元918年,曹議金被中央王朝正式授予節度使之職。敦煌第98窟正是在此背景下營建,以慶祝中原王朝的授節降恩。為什么曹議金掌控著中原無法染指的瓜沙二州,儼然獨立王國,卻甘為邊地節度使,對中原王朝唯唯諾諾?無它,強敵環伺,樹大招風。曹氏歸義軍政權承接自張承奉。唐朝滅亡后,張承奉建西漢金山國,稱白衣天子、金山國圣文神武帝。張氏的僭越引來了得到中原王朝支持的甘州回鶻征討。雙方多有沖突,最終回鶻軍兵臨城下,訂“父子之約”,要求張承奉尊回鶻可汗為父,稱臣納貢。公元914年,金山國滅亡,敦煌開啟曹氏歸義軍時代。前車之鑒,后事之師,曹氏主政歸義軍后,遂取消王號,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為強調政權合法性以及穩定本土漢人勢力,曹議金在位二十余年,朝貢中原王朝達九次之多。即使這樣,曹氏歸義軍政權在《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中仍被中原王朝認為是懸于關外的“外邦”“蕃夷”。總之,漢家制度的恢復成為其政權長期穩定性的法理依據。值得注意的是,曹氏歸義軍時代,瓜沙二州文化更加開放,這推動了佛教向世俗化方向發展,表現出與民間文化的合流之勢。
周邊關系方面,“敦煌郡,四面六蕃圍”。面對強敵之環伺,曹議金采取和平外交,通過政治姻親、使節互派、強化經濟文化往來以應對外局。為了體現其遙尊中原,團結外藩的外交理念,在壁畫中濃墨表現維摩經中“諸國王子問疾”“饒益四方”的內容,凸現了曹議金利用維摩詰的教化對幕僚們說教。同時,于闐王、回鶻公主等供養人場景亦是其具有明顯指向的討好外邦的象征。
除卻外交,曹議金在內政上亦用心良苦。張氏歸義軍時期,連年用兵,長期內耗,使得沙州之地經濟、民生嚴重受創,造成民怨沸起。因此,曹議金對外止戈的同時,力圖發展內政,收買臣屬,斬獲民心。第98窟作為曹氏家窟,出現了大量非曹氏家族的官僚供養人像。這些供養人身形不小,官階明確,朝向甬道曹議金畫像而非佛壇主尊,足可見曹氏意圖借助佛教力量強化統治威權。作為瓜沙地區的掌控者,曹氏雖然奉中原為正朔,但曹議金在郡內稱為“托西大王”,第98窟稱為“大王窟”,足可見其打造邊地王國的政治野心。
顯然,無論外交內政,曹議金都在第98窟的營建中將施政理念往精神信仰中澆筑。在歸義軍占有敦煌前的吐蕃時代,借助吐蕃崇佛力量,敦煌本土延續有一批強勢佛教團體。這種佞佛的宗教取向延續到了歸義軍時代。歷任歸義軍節度使莫不開鑿、整修功德窟,由此引發了敦煌石窟藝術發展新高潮的到來。曹氏的佛教崇信,在當時的寫經、禮佛文、發愿文、寺院各類文書上均有反映。曹議金多次在祈愿文書中袒露心跡,“風雨順時”“河清海晏”“歲熟時康”等祈語多次出現。這顯示了面對當時社會的動蕩不安,曹議金試圖通過佛界力量尋求心靈庇護。綜上,敦煌第98窟借助佛教來體現曹議金的統治意志,宣揚曹氏家族具備重塑瓜沙地區繁榮的能力,體現出推崇佛教思想與實現政治抱負的相輔相成。
(作者寧和平,武漢大學在讀研究生,考古學碩士,研究方向:漢唐考古,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參考文獻
(1)賀世哲,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J】,敦煌研究,1982(02):62—87;
(2)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敦煌壁畫全集09·敦煌五代-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09:第162頁,211—212頁;
(3)吳文星,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摩詰經變研究【D】,華南師范大學, 2002;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9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08頁;
(5)馮培紅,敦煌的歸義軍時代【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2013.12;
(6)沙武田、敦煌研究院編,歸義軍時期敦煌石窟考古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2017.09:第93頁,173頁;
(7)邵強軍,敦煌曹議金第98窟研究【D】,蘭州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