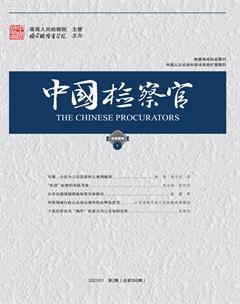“游戲托”入刑法理探析
薛津 孫超
摘 要:“游戲托”指在網絡游戲中扮演單身女性角色,以“奔現交友”“戀愛結婚”等理由誘騙男性玩家對其游戲賬號進行高額充值賺取提成的游戲推廣人員。被害人的承諾有效需基于其真實的意思表示,“游戲托”案中被害人對游戲賬戶進行充值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詐騙罪侵犯的法益應包含財產性利益,“游戲托”實施的行為侵害了被害人的財產性利益,被害人財產的社會性法益無法實現,因此以刑法手段打擊“游戲托”詐騙行為具有以預防為目的的處罰必要性。
關鍵詞:游戲托 詐騙 意思表示 目的失敗論 刑法預防
近年來,以互聯網平臺作為媒介依托,游戲運營服務商為自然人用戶電子終端提供的可以休閑、娛樂、競技并產生成就感的網絡在線游戲蓬勃興起。然而,在這一朝陽產業迅猛發展的同時,網絡游戲中的違法犯罪活動也應運而生,不僅讓受害人蒙受經濟權益及精神權益的雙重損害,同時也對網絡游戲市場的繁榮穩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關涉網絡游戲的違法犯罪活動,種類繁多、花樣翻新,成為了網絡游戲的“痛點”,也為社會埋下了不安定的“炸彈”。
一段時期以來,具有“游戲托”公司化性質的電信詐騙犯罪集團案件在全國各地多發。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是在網絡游戲公司的游戲推廣人員,其在網絡游戲中扮演單身女性角色,以“奔現交友”“戀愛結婚”等理由誘騙男性玩家對其游戲賬號進行高額充值,從而賺取提成返現。該類型案件屬于新型案件,針對上述人員的行為是否需用刑法打擊存在理論爭議,本文以T市J區檢察機關辦案實踐為例,以承諾效力的判斷及詐騙罪中目的失敗論為切入點,對該類型案件的性質進行法理探析,進而確定以刑法手段打擊“游戲托”詐騙行為具有以預防為目的的處罰必要性。
[基本案情]2018年2月23日,被告人劉某某在遼寧省盤錦市某某區某某路159號永泰廣告寫字樓五樓注冊成立并實際經營盤錦某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從事游戲推廣經營活動。2018年8月,劉某某通過鄧某某(另案處理)與江蘇某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約定代理推廣上述公司未在文化監管部門備案的《夢入凡情》《鳴劍風云》《夢昆侖》《仙侶世界》等網絡游戲,收取游戲玩家在上述游戲中充值總額的70%作為提成返利。被告人楊某某等四十余人先后通過招聘等方式進入盤錦某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底薪加業務提成的方式獲利。其間,楊某某擔任該公司風神部主管、姚某某擔任該公司林天部主管,文某某、趙某某、蔡某某分別擔任業務小組長,王某某負責公司招聘,劉某某負責游戲技術扶持。被告人高某某、郭某某等40余人具體實施犯罪,形成了以劉某某為首要分子,以楊某某、姚某某為骨干成員,其余被告人為一般成員的詐騙犯罪集團。
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2日間,楊某某、姚某某在劉某某的授意下,帶領部門內業務員推廣《夢入凡情》《仙侶世界》《鳴劍風云》等網絡游戲。上述被告人虛構年輕女性身份,在自己或公司配發的微信賬號上使用年輕女性頭像及昵稱,利用劉某某等人提供的“話術單”,以年輕女性身份通過《王者榮耀》《QQ飛車》等熱門游戲發送尋求男性游戲玩家組建游戲情侶的消息,添加被害人微信后發送相關游戲鏈接,引誘被害人下載游戲后與被告人組建游戲情侶,并假意與被害人發展戀愛關系,通過發送虛假的機票訂單信息截圖、共享位置截圖等方式持續騙取被害人的信任,誘騙被害人通過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等方式向游戲賬號充值獲利。其中,部分被告人以給付見面誠意金、報銷飛機票等理由,短時間多次向被害人索要錢款后向其游戲賬號充值獲利。經統計,上述被告人及涉案人員共計騙取他人人民幣1924551.67元。案發后,上述被告人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部分涉案財物被依法扣押。檢察機關以詐騙罪提起公訴。
現階段,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類型,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可分為數十種之多,由于標準不一,類型五花八門。主要有:按照詐騙行為的手段,可分為傳統類型詐騙、銷售類型詐騙和投資類型詐騙;[1]按照詐騙行為的冒充身份,可分為冒充公職人員詐騙、冒充特定職務詐騙、冒充特定身份詐騙和冒充近親屬詐騙;[2]按照詐騙行為的載體,可分為電話詐騙、短信詐騙、網絡詐騙及綜合運用上述三種載體協同作案的詐騙等等。[3]
然而,在T市J區的“游戲托”案件中,卻很難依據上述標準對其進行簡單歸類。其主要原因在于“游戲托”類型案件存在著多角度的法理爭議,但是經過綜合后認定,被告人通過網絡游戲平臺,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網絡游戲玩家數額較大的財物,該行為屬于冒充特色身份(女性婚戀對象身份)的變相銷售型網絡詐騙。
一、“游戲托”類案件是否入刑的法理爭議
關于“游戲托”類案件的定性問題,在刑事理論認識上與司法實踐過程中均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觀點。相關爭議主要體現在以下觀點之中。
(一)行為人不構成犯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認為,被告人獲取財物的關鍵環節在于通過被害人對游戲進行充值謀取提成。但被害人對游戲賬號進行充值主要是出于“組CP”“奔現”等心理因素考慮,而進行游戲消費是滿足被害人此種心理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根本不關心游戲的可玩性,但因怕與被告人“分手”,而自愿交付錢款。可見,被害人并不是因為對游戲存在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而是基于其他目的放棄自己的財物,因此,被害人自愿付款與被告人的虛構事實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特征,其行為屬于違規經營和商業欺詐。另外,被告人雖有誘騙被害人進行大額游戲充值的行為,但是,被告人確實通過游戲公司后臺為被害人游戲賬戶進行了充值,雙方存在真實的交易。可見,被告人實施上述行為只是為了獲取不合理的高額利潤,而并非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被害人事先知道游戲充值價值,且自愿選擇消費并轉賬,最終獲取了游戲元寶。那么,引誘他人高消費的行為只能算作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不能認為其具有欺詐交易的性質,不構成犯罪。
(二)行為人構成詐騙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意識到 “游戲托”首先通過網絡等方式搭識被害人,再約被害人共同玩游戲研發公司推廣的游戲,且誘使被害人進行高額游戲充值,利用被害人在“女友”面前要面子、維系情侶關系的心理,獲取非法利益。這種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消費活動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欺騙,被害人對游戲進行充值也是在受騙的前提下所為,因此,這種行為符合詐騙罪的要件。
上述理論爭議的焦點在于:男性網友對“處CP”、“奔現交友”“戀愛結婚”等目的上存在的認識錯誤,能否及于其對財產處分的認識錯誤?對于游戲是否具有與其充值等價的可玩性并無特別關注,其對賬戶充值時主觀上存在對消費的承諾及認可,且對于付款之后果也較為了解,客觀上被告人也履行了承諾,該種情形是否屬于陷入認識錯誤?男性網友在不愿繼續玩游戲情況下基于不在“女友”面前失面子,繼續維持男女朋友關系等考慮而選擇自愿充值,財產兌換成不能繼續交換的游戲“元寶”,是否存在財產損失?筆者認為,這些問題是關系到“游戲托”案能否以詐騙罪論處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游戲托”案能否定性為詐騙罪的法理基礎。
二、“游戲托”類案件司法判斷法理分析
人與一般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人的存在是一種目的性的生命活動,活動的目的在于做出一種意義性的判斷和選擇。因而,基于這種目的性的判斷與選擇,要求在詐騙罪構成中,錯誤與處分財產之間必須有實質的因果關系,換言之,只有當欺騙行為導致受騙者陷入處分財產的認識錯誤時,該欺騙行為才是詐騙罪中的欺騙行為,進而可能成立詐騙罪。
在“游戲托”案中,欺騙行為主要體現在“游戲托”提出“奔現”要求,與“游戲宅男”交友約會、戀愛結婚等,男性網友也是在這一問題上陷入認識錯誤,而對其游戲賬戶進行充值,被害人對游戲本身換來的“可玩性價值”事先是明知的,對于處分財產的范圍、種類具有一定認識,對這一行為本身并未存在認識錯誤,即便被害人認為該游戲非常無聊,但被害人對于游戲充值價格是默認的,可見被害人對于財產處分這一行為本身并無認識錯誤。被害人損失的金錢也以不可再兌換的“游戲元寶”形式客觀上進入了被害人的游戲賬戶內。這種情形下,對于“游戲托”案件以詐騙罪論處,需要在提高刑法的適應性,增強刑罰的預防目的前提下對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進行法理上的重新解釋。
(一)被害人承諾需基于真實意思表示
羅馬法有句諺語“得承諾的行為不違法”。被害人承諾,是指被害人同意他人侵害自身法益的情況。被害人承諾在刑法上承擔著重要的意義,可以影響定罪及量刑。應該說,男網友基于“處CP”“奔現戀愛”“結婚”等目的與“游戲托”共同進行游戲,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均存在對于游戲賬號進行充值的認可,其實質上屬于一種財產處分的“承諾”行為。法理上一般認為,被害人的承諾可以阻卻部分行為的違法性。“如果從憲法保護個人行動自由的角度出發,認為承諾涉及放棄身體、自由的法益或處分自己的財產,不管這樣的承諾是理性或是非理性的,都應該被理解為個人人格自由的行使與展現,因此可以阻卻不法性。”[4]在“游戲托”案件中,被害人基于處“游戲CP”“奔現戀愛”、結婚等目的對游戲賬號進行充值,是基于以放棄其自身利益(支付充值)去維持或者換取另外一個利益(“奔現戀愛”、結婚等可期待的誘惑),而這一情形,顯然屬于承諾的一種表現形式。“法益所有人的承諾之所以有可能對于行為人實施的侵害行為的不法評價產生阻卻作用,其主要思想基礎源自于個人的自我決定權與行為自由。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法益所有人基于其內在利益的抉擇而自愿決定放棄某個法益以維持或追求另外一個利益,由于其所放棄的屬個人法益,在不影響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原則上應當允許。”[5]
承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對其承諾行為的核心評價。要使得承諾有效進而阻卻違法性,承諾人所作出的承諾必須是在非受到強制、脅迫且基于真實意思表示而作出。但是,比較有爭議的問題是,承諾人如果受到欺騙而作出的承諾,是否當然屬于無效的承諾?“游戲托”案就是典型的這一情形。被害人之所以進行游戲充值,就是在“游戲托”虛構了“處CP”、“奔現交友”、戀愛結婚等目的而作出的。“游戲托”的欺騙行為,能否影響被害人承諾(游戲充值)的效力,這是“游戲托”案能否定性為詐騙罪的核心,也是理解“游戲托”虛構“奔現”事實與被害人進行游戲充值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重點。
對于被害人因受欺騙而作出承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理論界存在不同觀點。德、日刑法界對此有過激烈的討論,三種比較主流的觀點,即完全無意思瑕疵理論(全面無效論)、本質錯誤說(重大錯誤說、決定動機錯誤說)和法益關聯性理論(法益錯誤論)。完全無意思瑕疵理論是以“欺騙”為核心進行量度,只要存在被告人欺騙的事實,被害人的承諾即為無效。本質錯誤說認為,如果被害人沒有錯誤認識(或者知道真相)就不會做出承諾,或者說被告人的欺騙行為對于被害人的意思及行為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則該承諾無效。法益關聯理論則認為,僅僅是動機方面的錯誤且與法益無直接關系,不會阻斷承諾的效力。但是這種觀點在處理某些案件的時候常常會與人們的樸素正義觀相悖。
綜合上述有關三種承諾效力的觀點,對照“游戲托”詐騙行為,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游戲托”案中,被害人受到“游戲托”的欺騙而作出游戲充值的承諾,結合全面錯誤說和本質錯誤說,在此類案件中,“游戲托”的欺騙已經使得被害人形成了關于對等給付、所追求的目的(“奔現交友”、戀愛結婚等)的錯誤認識,此錯誤事關關鍵事實。因為被害人的支付行為基于這一錯誤,如果沒有該錯誤,就不會自愿實施充值行為。因而被害人關于游戲賬戶充值的錯誤想象屬于重大瑕疵,其決定性的動機是錯誤的,因此導致被害人承諾的無效,進而肯定“游戲托”行為具有犯罪屬性。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游戲托”是否向男性網友游戲賬戶提供“游戲元寶”,都會因為被害人承諾的無效而具有構成詐騙罪的可能。因而難以否定“無認識錯誤”承諾的效力,而會排除“游戲托”案的犯罪性,不利于普遍正義的實現。
(二)詐騙罪的目的失敗論
財產損失是詐騙罪成立的構成要件要素之一。在通常的詐騙中,被害人是因陷入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因而對自己的財產損失并不“明知”。對于“游戲托”類型案件中,被害人被誘騙向自己的游戲賬戶進行充值,換回“游戲元寶(不能再交換)”能否認定被害人存在財產損失?有不同觀點認為該種行為一般認為不構成詐騙罪。理由是,經營者擁有經營自主權,可以根據市場行情進行商品推廣,被害人并無財產損失,因為他的財產換來了游戲元寶,至于推廣的手段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引誘他人消費的行為只能算作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或者是欺詐消費行為,是行政法調整的范圍,故不構成詐騙罪。為了駁斥這種觀點,應該進行更深層次的刑事法理依據反思。
財產犯罪的法益,并不單指被侵害的財產本身,其既包括財產,也包括財產性利益,這已成為刑法學界公認的觀點。如同財產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一樣,財產利益包括“使用利益”及“交換利益”兩種類型。“事物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能夠被個人的主觀利用目的所投射,當得知該事物能夠滿足自己的某種需求時,則該事物存在使用價值。即物品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效用。”[6] “交換利益”又被稱之為“經濟利益”,“交換利益”表現為一種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存在的抽象,且“只是在揭露欺詐行為等時才在法律上區別于價格”。[7]財產權人所享有的交換利益是否受到損害,不能僅作形式上的判斷,而必須觀察整個交換過程,以此判斷財產權人所享有的財產“整體價值”是否有所減損。這個過程應是財產權人能以其自己的意愿,根據一定的價值規律進行交換,以達到自己的目的。[8]
由于交換利益與財產權人的主觀需求有關,因而交換利益是否損失的判斷,應當結合財產權人主觀需求、目的是否得以實現或者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性加以判斷。對于上述觀點,我國學界也予以認可。“與使用目的重大的背離,是一種財產損害……被欺騙而處分財產的人,所得到的給付如果與訂約目的重大違背,也是一種財產損害。”[9]此觀點在有關詐騙罪錯誤的解釋中引入了主觀目的,進而以此為基礎判定財產損失。行為人既可以利用事實,也可以利用價值判斷騙取他人財物。價值判斷有大體的公認標準,可以使人產生錯誤,從社會關系的復雜化以及刑法對現實的適應性來考察,應承認就價值判斷可以進行欺騙,這不違反我國刑法的規定。在“游戲托”類型案件中,受害人就所交付財產的用途、財產的接受者存在主觀上的認識錯誤時,即使受騙者沒有期待反對給付,也應認為存在財產損失,對方的行為應成立詐騙罪。詐騙罪中財產損失的認定與詐騙罪的特點是制造并利用受騙者的認識錯誤侵犯被害人的財產,如果能夠肯定受騙者因為行為人的欺騙行為產生了用途上的錯誤,進而處分了財產,就此造成了財產損失。在財產法益中,法益處分行為的社會意義的錯誤,就是法益關系的錯誤。通過財產的給付而得到的不僅是經濟利益,還包含社會目的得以實現,這就是法益處分的社會意義問題。據此,對財產的轉移被害者沒有主觀目的錯誤的場合,交付的結果是有交付權限的被害者所接受的,不能追究欺騙行為人對被害人“轉移財產”的責任;反過來,基于主觀目的錯誤轉移財產的場合,則由于被害者不接受轉移財產的結果,加上這又是行為人的欺詐所引起的,當然要追究他對自己引起對方不正當轉移財產的行為的責任。換言之,如果受騙者的財產交換失敗、處分財產的目的沒有實現,就意味著存在財產損失。[10]本案中,無論被害人如何處分自己的財產,其處分財產的目的(與“游戲托”戀愛、結婚)都無法實現。可以看出,通過交換利益以及財產損失的實質解釋,較好的解決了“游戲托”詐騙案在財產損失理解與認定上的理論。
(三)刑罰的預防目的及刑法適應性
刑罰的重要目的之一即為預防和減少犯罪,既警醒具有犯罪潛在危險者避免犯罪,又告示已經犯罪者基于刑罰威懾力量不能再次犯罪。司法人員要時刻考慮自己的司法活動是否符合刑法目的,從而有利于將刑法目的貫穿于刑事司法活動的始終。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然而其本身并不否定刑法應具備與社會發展相洽的刑罰適應性和刑罰規則效力。刑法的適應性,就是指相對固定、簡單和有限的刑法規范如何滿足紛繁復雜、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需要,這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極具實踐意義的問題。弗里德里曼曾經說過:“法律和社會工作者必須能描述和測量運行中的法律制度。他指出兩個方面的影響途徑:從社會到法律制度和從法律制度到社會。” [11]換言之,無論是立法者還是司法者都必須揭示法律制度的來源、社會力量如何評價或轉化為法律以及法律制度如何防止犯罪用于社會生活。由于法律通常滯后于社會情勢的頻繁變遷,刑法的立法目的只是通過固定的方式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的確會凸顯出一種忠實、保守的傾向。因此,司法者在適用法律時,尤其是面對法律規則與社會事實的摩擦地帶,必須充分考慮到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和變化可能。司法者在作出裁決時,除了必須依法裁判之外,也應當善于利用法律本身所具有的靈活性機制,充分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法律的“格式化”與案件的“非格式化”之間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在每一起案件中盡量尋求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合理平衡。刑法只有運用到現實生活中才具有意義,判決書、起訴書是對刑法活生生的解讀,刑法的內容越被一般人理解,刑法就越能發揮一般預防的作用。
“游戲托”電信詐騙行為已經嚴重影響了網絡空間和他人的財產權,刑法如果坐視不理,此類公司化運營的電信詐騙集團將會不斷發展,嚴重蠶食網絡環境。從形式上看,“游戲托”行為與傳統詐騙罪構成要件雖然存在不盡一致的地方,這實際上是邏輯與實在之間的沖突在刑法領域的再現。因此,以刑法手段打擊“游戲托”詐騙行為具有以預防為目的的處罰必要性。
三、結語
日前,上海市檢察機關及成都市檢察機關均對“游戲托”類案件提起了公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移動智能設備的迅速普及,各類網絡游戲呈現大火態勢。但是利用網絡游戲實施侵害的犯罪案件也同時日益突出,危害不斷凸顯。較之傳統的婚戀詐騙,在“游戲托”類案件中,被告人通過“婚托”方式將受害人引入游戲“陷阱”騙取錢財,犯罪分子與網絡游戲平臺相互“勾連”,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他們試圖利用游戲充值這種形式合法的交易方式,將詐騙錢款“洗白”,具有較強的欺騙性,因此,需要司法者以靈活的方式打擊犯罪,而不是以武斷的方式去裁剪實施。
注釋:
[1]參見張文波、鄭銳、李靈雁:《投資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辦理難點及應對——以A省L市檢察機關辦案實踐為樣本》,《人民檢察》2019年第16期。
[2]參見翟家圣:《信息化背景下我國電信詐騙的發展特征及防控探析》,郝宏奎主編:《偵查論壇》(第15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頁。
[3]參見何秀英:《淺析電信網路詐騙犯罪證據體系的構建難點及出路》,孫長永主編:《刑事司法論叢》(第5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頁。
[4]王皇玉:《強制手段與被害人受欺騙的同意:以強制性交猥褻罪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2013年第2期。
[5]吳耀宗:《被害人受騙之承諾》,《月旦法學教室》2013年第4期。
[6]張天一:《對財產犯罪中“財產概念”之再建構(下)——以“支配關系”所形成之財產概念》,《月旦法學雜志》2009年第2期。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頁。
[8]同前注[6]。
[9]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48頁。
[10]參見林東茂:《詐欺罪的財產損害》,《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1998年第3期。
[11]Lawence M.Friendman,The Legal System,1975b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p.27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