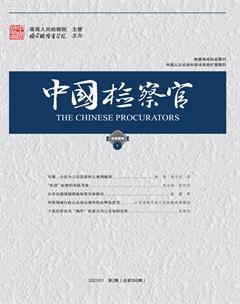持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經營走私煙的定性
黃河
一、基本案情
王某某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某底商經營“北京市四季眾利商貿中心”銷售香煙,其持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經營范圍為卷煙零售、雪茄煙零售、罰沒煙草制品零售。2016年9月11日7時30分許,王某某在其位于北京市房山區的家門外,指使鄧某某(另案處理) [1]駕駛汽車向外運輸香煙時,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和房山區煙草專賣局聯合執法人員當場查獲。在車內和房山區的家中當場查獲卷煙若干。經北京市煙草專賣局認定,涉案香煙中,無標志外國卷煙和專供出口卷煙(走私煙)共計30488條,價值4176856元。
二、分歧意見
本案的主要問題是:持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經營走私煙的行為是否屬于“超范圍經營或不按照規定渠道進貨的行為”?
第一種意見認為,有許可證超范圍經營或不按照規定渠道進貨的行為不構成犯罪[2],外國煙草需要從煙草專賣企業統一購進,走私渠道獲得的外國煙草也屬于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因此,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有證經營走私煙的行為不構成非法經營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在有許可證的情況下,超范圍經營和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的行為僅處以行政處罰[3]的前提是該煙草是合法的、允許在中國國內流通的。走私煙本身是違法的,無法在中國境內合法銷售,非法經營走私煙的行為嚴重擾亂市場秩序,不適用“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4]的相關規定,應認定非法經營罪。
三、評析意見
要準確判斷這個問題,有必要深入了解相關司法解釋制定的背景以及煙草專賣制度的發展和變革。
《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簡稱《煙草解釋》)自2010年3月26日起施行,《煙草專賣法》于2015年4月24日進行了修訂并施行。在《煙草專賣法》修訂前,煙草許可證包括煙草專賣生產企業許可證、煙草專賣批發企業許可證、特種煙草專賣經營企業許可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四種。其中,特種煙草專賣經營企業許可證針對的主體僅是經營煙草專賣品進出口業務、經營外國煙草制品寄售業務、在免稅店經營外國煙草制品的企業,與普通的零售商戶、企業并無關系。換言之,在2015年4月24日之前,所有商戶和普通煙草專賣企業無法經營外國煙草。修訂后的《煙草專賣法》刪除了特種煙草專賣經營企業許可證的相關規定,放開了對外國煙草的管控力度,普通煙草專賣企業可以經營外國煙,持有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的商戶可以從其所在轄區的煙草專賣公司購買外國煙草用于銷售。隨著外國煙草經營權的下放,有證商戶可以經營外國煙草,市場上的外國煙草越來越多,而有證商戶超范圍經營或從走私渠道獲得外國煙草的行為定性問題才成為實務工作的新難題。
走私煙包括“無標志外國卷煙”和“專供出口卷煙”兩種。外國卷煙須經煙草專賣公司統一進口、統一分配[5],允許有證銷售;專供出口卷煙不允許回購,禁止在國內市場銷售。可以看出,“無標志外國卷煙”和“專供出口卷煙”都不是通過正規渠道獲得,也都在正常煙品銷售范圍之外,那么有證經營走私煙該如何定性?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經營走私煙具有相當的法益侵害性
無論是《煙草解釋》還是兩高研究室對該解釋的理解與適用均明確,“有證超范圍經營或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的行為,違反有關行政法規但社會危害性不大,不宜按照犯罪處理”[6]。因此,除了判斷有證經營走私煙是否具備“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的行為表征,我們還需要采用實質的判斷標準,即判斷經營走私煙是否具有相當的法益侵害性。
國家設立非法經營罪在于管控特殊商品的經營秩序,有證超范圍經營和不按照規定的渠道進貨之所以不能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的原因在于,這兩種行為并沒有破壞市場上流通煙草的生產總量和供銷關系,其破壞的只是煙草職權部門對于煙草“由誰賣、賣多少”的內部流轉秩序,國家對于煙草的管理和監管仍然是動態可控的,其既沒有妨害煙草專營專賣的市場秩序,也沒影響國家的財政稅收,處以行政處罰即可。事實上,這部分煙在被煙草局查獲后,可以以“罰沒煙”的形式二次銷售,亦證明了這點。但走私煙未經國家批準擅自入境,未經煙草管理部門檢驗登記,“一經查獲,一律銷毀”[7],不存在任何再次合法化的途徑。經營走私煙的行為使得相當數量的煙草脫離了國家控制,排擠了合法香煙的市場份額,直接破壞了市場上煙草的生產總量、專賣經營的計劃性和進出口專賣管理秩序,嚴重擾亂國家對煙草行業的管控秩序,造成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
(二)經營走私煙構成非法經營罪符合立法本意
《煙草解釋》頒布實施時,由于特種煙草專賣經營企業許可證的存在,所有個體商戶甚至普通煙草專賣企業都不可能獲得此許可證,個體商戶或企業若“經營外國煙”屬于無證經營而不是超范圍經營,可直接認定為非法經營罪。顯然,在司法解釋制定之初,商戶經營外國煙不在立法考慮之列,更不可能涉及從走私渠道獲得外國煙是不是“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的考量,因此商戶的哪些行為應被排除在非法經營罪之外的討論也是在煙草是國內合法煙草的大前提下展開論述的。故從司法解釋及理解與適用的出臺背景來看,該解釋針對的經營對象應該是我國法律允許進入市場流通、交易的煙草,因行為人的經營手段和方式僅違反煙草管理相關法律的規定,無刑事處罰必要,兩高研究室才特意對“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和“超范圍經營”的行為定性進行了列舉和補充說明。
進一步探究立法本意,不難發現,“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中的“渠道”指的是合法的進貨渠道,即煙草公司配貨,不應包括走私等非法渠道,其前提的是煙草本身都是合法取得、國家認可的,主要規制的是零售商之間私自串貨的行為;“超范圍經營”中的“范圍”指的是國家或地區允許香煙銷售的地域范圍和種類范圍,可以涵蓋數量范圍[8],但不應包括走私煙、假冒注冊商標且偽劣煙[9](下簡稱假煙)等違法煙,其規制的是合法煙草跨區域(國內)流動及跨種類經營的行為[10]。
(三)主觀上認定經營走私煙的故意不存在障礙
假煙和走私煙一樣存在天然的違法性,同樣不應適用“超范圍經營和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的規定,已具有非法經營罪的刑事違法性。只要經營的煙不是“國內真品卷煙”,都應當構成非法經營罪,但實務中,“有證經營假煙”卻鮮有以非法經營罪論處的,雖然結論上與以往“以有無許可證作為認定非法經營罪唯一依據”的審查思路不謀而合,卻不能據此認為“有證經營走私煙”也不應該定罪處罰,原因在于假煙和走私煙在有責性層面認定故意的難度不盡相同。
這種差異性的評價主要源于煙草外觀標識的差別:“國內真品卷煙”外包裝印有各零售商獨特的煙草專賣碼,一店一碼;“假冒注冊商標且偽劣煙”外觀上與真煙基本無異,若無專業知識較難區分;而兩類走私煙,按規定,凡正常進口的卷煙在箱包、條包和箱包上應印有“由中國煙草總公司專賣”字樣[11],否則即為“無標志外國卷煙”;專供出口卷煙印有“專供出口”字樣。
所以,雖然假煙和走私煙都是串貨所得,但因假煙與非渠道真煙在外觀上較難識別,存在不知情被摻假的可能性,客觀證據只能推定出行為人具有與經營非渠道真煙一樣的行政違法故意,很難認定具有非法經營罪的故意[12],無法對該行為進行非難和譴責。而走私煙在外觀上與國內煙(包括假煙)極易區分,認定行為人明知是走私煙而經營不存在障礙。
綜上,雖然“有證經營走私煙”是2015年《煙草專賣法》修訂后才逐漸進入實務視野,但如果僅從字面上機械的認為走私渠道也是“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簡單的“唯許可證有無定罪”,不僅忽略了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縱容了犯罪,而且不啻于要求任何法律在制定時就應該包羅萬象,不允許有任何字面含義之外的解釋空間,這顯然是錯誤的。所以,綜合考慮法益侵害性、立法背景及主觀判斷后,我們認為有證經營走私煙的行為具有刑事可罰性,應當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也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
注釋:
[1]無法查清鄧某某是否明知是走私煙而實施的運輸行為,作存疑不起訴處理。
[2]參見李曉:《〈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10年11期。陳國慶、韓耀文、王文利:《〈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檢察》2010年8期。
[3]同前注[2]。
[4]因“超范圍經營”和“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進貨”兩種違法方式有一定重合且處理結論一致,為討論方便,側重分析“走私渠道是否屬于不按照規定的進貨渠道”。
[5]由中國煙草國際有限公司和國外的煙草公司簽訂供貨協議,按照雙方約定的數量及日期生產,并且在生產時就讓生產商在外包裝上印上“由中國煙草總公司專賣”的字樣,后入關轉入國內進行銷售。
[6]李曉:《〈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司法》2010年11期。
[7]參見《海關總署 財政部 國家煙草專賣局關于進一步加強海關罰沒走私卷煙管理的通知》(署財發[2013]131號)第1條;《北京海關 北京市煙草專賣局進一步加強罰沒走私卷煙管理的實施辦法》(京關財[2014]11號)第3條。
[8]如果認為數量范圍也屬于“超范圍經營”,自然能推導出“有證進行煙草批發業務不構成犯罪”,而這符合2011年5月6日最高院《關于被告人李明華非法經營請示一案的批復》的批復精神,也與實務中的無罪結論一致。
[9]實際上應細分為假冒煙、偽劣煙和假冒偽劣煙,因實踐中假冒煙和偽劣煙多一并出現,而且定罪量刑的方式差不多,故不再單獨討論。
[10]從當時的立法背景看,應該只包括國內香煙的種類范圍,不包括目前可能存在的這種不應當經營國外(某種)合法香煙卻超范圍經營(某種)外國煙的情況,因為無論是國內煙還是國外煙都是有煙草公司統一配送到經營店,若存在超范圍經營(某種)外國煙的情況只能是商戶之間串貨導致,直接適用“不按規定進貨渠道進貨”的相關規定出罪即可。
[11]《國務院關于嚴厲打擊卷煙走私整頓卷煙市場通告的批復》(國函[2000]13號)第2點。
[12]經與煙草行業工作人員了解,事實上,雖然同樣是串貨所得,但商戶間會就煙品提前溝通,所以行為人對“假煙”和“真煙”還是心知肚明的,但我們認為,這種行業內部的潛規則、商業“誠信”和商業默契卻不能作為推定主觀故意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