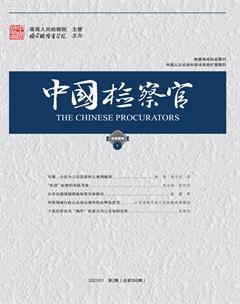騙取銀行帶追索權保理融資的行為定性及共犯認定
鐘曉宇 孟祥宇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于某成立A公司從事糧食貿易,后從多家銀行借貸從事糧食種植、煤礦開發等經營項目,因投資失敗、經營虧損嚴重,至2014年8月已欠數家銀行貸款本金合計近4億元,并欠民間高利貸數千萬元。其自2011年開始從H銀行貸款,一直由該行客戶經理王某(另案處理)負責其貸款業務,于某在王某催要下,于2014年5月以其他借款還清前筆貸款。2014年9月,于某欲繼續從H銀行續貸、周轉資金,因擔保物不足,在王某建議下,以保理融資形式申請授信。即于某以A公司作為賣方,與買方某國有企業B公司的貿易合同為背景,將A公司的應收賬款轉讓給銀行,約定A公司按月還息,以帶追索權的公開型保理申請授信3000萬元。因此時資金狀況已無力開展經營,于某遂找人偽造B公司的印章,虛構貿易合同,并指令A公司期貨風控部員工朱某冒充B公司員工參加H銀行現場核保(公開型保理需通知B公司確認應收賬款轉讓,方可授信)。朱某稱于某讓他代替擔保公司蓋章,好讓銀行放貸,囑咐朱某現場不必講話,直接蓋章就行。朱某擔心工作不保,遂按指示提前到B公司大廳等候,王某發現是A公司員工朱某來假冒確認,但考慮到于某系其長期客戶,誤以為其本次也能及時還款,遂隱瞞真相,提示朱某在《應收賬款債權轉讓確認函》及回執上蓋章,予以現場核保通過。后H銀行放款3000萬元,被于某用于歸還高利貸借款。隨后,于某逃匿,造成H銀行3000萬元損失無法清償。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于某和朱某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共犯。保理業務是以債權人轉讓其應收賬款為前提,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融資于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1]其核心在于應收賬款轉讓,故保理合同是債權轉讓合同,涉及債權人、債務人和保理人三方債權轉讓關系,與借貸雙方還本付息的借款關系在功能作用和法律性質上都有本質區別。所以,保理融資不屬于“貸款”,不能用貸款類犯罪評價。根據刑法第224條的規定,于某明知自己沒有歸還能力,指使員工偽造印章、假冒買方公司確認應收賬款轉讓,利用保理合同騙取銀行資金占為己有,隨后逃匿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朱某不了解保理業務,其錯誤的認為自己是冒充擔保公司員工給A公司申請貸款提供擔保,其對蓋印確認相關文件的法律意義不知情,未與于某達成共謀,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于某和朱某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共犯。結合民法典規定,保理的法律性質取決于其具體構造而非概念,有追索權的保理,是借貸合同與間接給付的結合,核心是債權人與保理人的資金借貸關系;而無追索權的保理,才是真正的債權轉讓。本案約定有追索權保理,即銀行屆期未能收回應收賬款,可以向賣方主張返還保理融資款本息或者回購應收賬款債權,此時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與貸款關系相似,可以用貸款類犯罪予以評價。因合同詐騙與貸款詐騙存在一般法條與特殊法條的競合關系,故應認定為貸款詐騙罪。朱某受于某指使,假冒買方公司員工虛假確認保理合同成立的關鍵文件,參與詐騙行為,其雖誤以為自己假冒擔保公司蓋章,但屬于貸款詐騙不同行為手段之間的認識錯誤,系同一犯罪構成內的具體事實認識錯誤,不影響故意犯罪的成立,故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共犯。
第三種意見認為,于某構成貸款詐騙罪,朱某構成騙取貸款罪,二人在騙取貸款罪范疇內構成共犯。對于某的分析和對朱某手段行為認識錯誤的分析同第二種意見。朱某雖參與騙取貸款,但其對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貸款并不知情,二人更未形成共謀,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貸款詐騙與騙取貸款屬于侵害同種法益的重罪與輕罪,存在重合性質,可在重合范圍內認定為共犯,同時又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分別予以定罪。
三、評析意見
民法典首次將保理合同納入典型合同予以規范,為我們準確認定相關犯罪提供了基礎依據。結合民法典規定,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關于合同詐騙罪與貸款詐騙罪的辨析
1.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額較大資金不能歸還,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非法占有目的:(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于某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卻偽造印章、虛構貿易背景、指使員工冒充買方公司騙取銀行保理融資,且改變約定用途,全部用于歸還個人高利貸借款,隨后逃匿,造成銀行特別巨大損失,可以認定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銀行保理融資。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客戶經理王某在核保現場已發現于某指使員工冒名虛假確認,對于某騙取貸款的行為已察覺,卻隱瞞真相予以核保,但此時的王某并不能代表銀行作出處分財產的決定。于某的詐騙行為導致銀行具有決定權的領導陷入認識錯誤,從而處分財產,符合詐騙類犯罪的行為結構。銀行相關金融業務,都要依托書面合同完成,故這里存在貸款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詐騙罪之間的法條競合關系。根據特殊法條優于一般法條的原則,我們先考慮是否構成貸款詐騙罪。根據刑法193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做擔保等特定詐騙行為,騙取銀行貸款,數額較大的,就構成貸款詐騙罪。于某私刻B公司印章,虛構與B公司貿易合同,指使員工假冒B公司在保理合同成立的關鍵文書——《應收賬款債權轉讓確認函》上蓋印同意,并使用上述虛假證明文件,非法獲取保理融資3000萬元,符合貸款詐騙罪特定的行為手段和危害結果。所以定性的關鍵在于確定本案涉及的保理融資能否認定為本罪的特定對象——貸款。
2. 貸款是指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約定的利率和期限還本付息的貨幣資金,基本特征就是還本付息。保理又稱保付代理,前文已述,其是以債權人轉讓應收賬款為前提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因缺少法律規范,以往對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質有多種分歧意見,造成司法實踐中的爭議。而民法典首次將保理合同納入典型合同,予以規范,不僅從民商事領域提供了認定保理合同性質的基本準則,也為刑事領域對騙取保理融資行為的定性提供了方向。保理的法律性質取決于其不同類型的具體構造,而非概念本身。依據應收賬款到期無法獲得債務人清償,保理人能否對債權人行使追索權分為有追索權保理合同和無追索權保理合同,民法典766、767條分別對這兩種合同采取不同的理論構造。無追索權保理業務,又稱買斷型保理,由保理人自行承擔應收賬款的壞賬風險,是債權轉讓關系,即由保理人取代債權人地位,其支付給債權人的融資款由債務人清償,與二者間的借貸關系有本質區別。而現實中,我國商業銀行大多使用有追索權保理合同。民法典充分吸收司法審判經驗,從權利實現的角度,對有追索權保理采用“借貸合同與間接給付”相結合的構造,“有關追索權的約定是具有擔保債務履行功能的間接給付合同。間接給付指為清償債務而以他種給付代替原定給付的清償”[2],而核心是債權人與保理人的資金借貸關系。主要體現為:一是債權人承擔信用風險。保理人既可以要求債權人返還保理融資款本息或者回購債權,也可向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盡管保理融資的第一還款來源是應收賬款債權的回款,但債權人對融資款負有最終的清償責任,如果應收賬款無法正常收回,債權人需履行回購義務,向保理人償還融資本息,與還本付息的貸款相似。二是保理商收取固定收益。保理人向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債權,在扣除保理融資款本息和相關費用后有剩余的,應當返還債權人;而無追索權保理則無需返還。表面上是應收賬款的轉讓,實際上是債權人以應收賬款作為對保理人債務清償之替代給付,回款雖優先清償保理融資款,但余款仍應歸還債權人。區別于債權轉讓的“買斷”,卻類似于擔保型借貸,故有追索權的保理融資本質上是債權人與保理人之間的資金借貸關系,因與貸款關系相似,可以用貸款類犯罪予以評價,故可以認定于某構成貸款詐騙罪。
(二)關于朱某行為的定性分析
朱某在騙取貸款的范疇內與于某構成共犯,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
1. 朱某對其參與騙取貸款具有認識。朱某稱老板告訴他是替擔保公司蓋章,為本公司申請貸款。朱某作為期貨風控部的員工,對金融知識有一定理解,其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假冒擔保公司員工,為本公司申請貸款提供虛假擔保;而實際上他是假冒保理融資業務的買方公司虛假確認應收賬款轉讓文件。根據法條對貸款詐騙罪行為手段的列舉規定,朱某無論是配合于某提供虛假擔保,還是冒充保理融資的買方公司在確認函上蓋章,從而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和證明文件騙取保理融資,都符合本罪的行為特征。朱某雖發生了認識錯誤,但屬于同一犯罪構成范圍內的具體對象認識錯誤,根據主流觀點法定符合說: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只要在犯罪構成范圍內是一致的,就成立故意的既遂犯。[3]故可以認定朱某對于某騙取貸款的行為具有認識,并現場默認身份、幫助隱瞞真相,假冒蓋章、參與實行行為。
2. 朱某并未與于某就貸款詐騙達成共謀。朱某作為公司員工,迫于老板壓力,參與騙取貸款,但其對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貸款并不知情,其正是基于相信老板有實力、企業有能力歸還貸款,他還要靠這份工作繼續養家糊口,才同意按老板指示,冒充其他公司員工參與銀行現場核保。因其對于某貸款詐騙的主觀心態不明知,其不具有參與貸款詐騙的主觀故意,故不構成貸款詐騙罪的共犯。
3. 朱某在騙取貸款的范疇內與于某構成共犯,應認定為騙取貸款罪。朱某明知自己假冒其他公司員工,在申請貸款的關鍵文件上作假,配合于某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3000萬元貸款,其具有騙取貸款罪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構成騙取貸款罪。根據主流觀點部分犯罪共同說,如果數個犯罪的構成要件之間存在重合部分,該部分本身是刑法所規定的一種犯罪時,就可以認為兩人以上就重合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而在重合范圍內成立共犯[4]。在此前提下,又存在分別定罪的可能性。騙取貸款與貸款詐騙的手段行為基本一致,關鍵區別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兩種犯罪侵犯了同類法益,貸款詐騙比騙取貸款更為嚴重,嚴重犯罪包含了非嚴重犯罪的內容,存在重合性質,能夠在重合范圍內成立共同犯罪,故朱某可以認定為于某的共犯,但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通過本案辦理,筆者認為,在辦理經濟犯罪案件時,首先要準確認定基礎的民事法律關系,才能準確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正如張軍檢察長在《全國檢察機關貫徹落實實施民法典工作會議》中提出,民法典不僅是保障民事權利的寶典,也為刑事司法等提供詳實的規范,對各項檢察職能融合發展創造了難得契機。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民法典,將民法原則、民法典精神融入執法辦案中,準確界定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精準認定犯罪性質,不斷提升刑事檢察工作水平。
注釋:
[1]參見《商業銀行保理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6條。
[2]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3次會議紀要:保理商能否同時行使追索權和償債請求權。
[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頁。
[4]參見周光權:《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3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