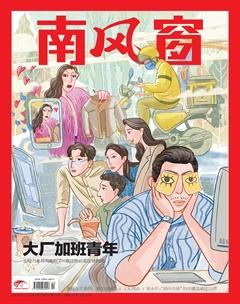尋找和平相處之道
趙義
近日,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了央視的專訪。全世界都在關心,中美關系會走向何方。雖然隨著特朗普下臺,中美關系改善的契機已經出現,但是美國并沒有放棄把中美關系定義為戰略競爭關系,因此籠罩在中美關系上空的陰云并沒有真正消散。那么,崔大使的發聲透露了什么重要信號呢?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中國明確給出了讓中美關系重回合作這個唯一正確軌道的根本前置條件,即兩個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很不相同的國家能不能、要不要和平相處,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來真正造福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于美國來說,能不能接受中國這個跟它很不相同的國家發展起來,能不能尊重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這是個根本性的問題。
這樣的表述不是頭一次出現,但在拜登政府正式就位不久,由駐美大使再次提出來,無疑是中國為接下來雙方的官方接觸定下了基調。
的確,一段時間以來,兩種制度、兩種價值體系的沖突明顯加劇。在美國那里,這樣的沖突進一步簡化為所謂威權和民主的二元對立。從歷史上看,制造這種二元對立其實就是冷戰的前兆。
關鍵的問題就來了:不同社會制度的中美兩國能否找到和平相處之道呢?這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影響自身以后很多年的世紀性質的設問,關系到兩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預言自我實現。對中國來說,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國內發展創造良好環境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新發展階段的一個基本方針。
和平相處是需要基礎的。這個基礎包括利益,但不局限于或者說不能僅僅局限于利益。先不說美國,實際上,從中國來說,這樣的基礎是在不斷呈現。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多次表明對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堅守,并且是把共同價值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通在一起。1月2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并發表特別致辭時就指出,“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擺脫意識形態偏見,最大程度增強合作機制、理念、政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在中美關系波折不斷的這幾年里,外交系統官方人士也借助多個正式場合呼吁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堅守全人類共同價值。
既然是“共同價值”,那自然就是超越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的差異。堅守“共同價值”,就有了維系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和平相處的價值紐帶。某種意義上說,反復重申堅守“共同價值”也是一種對堅決反對打新冷戰的宣示。
其次,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相處是有具體抓手的,就是妥善處理好不同發展模式之爭。從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積極進行各種區域自由貿易區談判、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持積極態度等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中化解不同發展模式之爭的。
不久前,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演講中就澄清了,指責中國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誤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力圖把中國排除在未來經濟全球化之外的一張牌。實際上,在經濟全球化導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人為的“脫鉤”是違背經濟規律的。繼續堅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符合中國最大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的。
不同發展模式在同等規則的基礎上的相處相融,總是可以談出來的,并且反過來通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來制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滑向危險的陷阱。比如國企補貼問題,中歐投資協定可以談成,那么其他類似協定也能夠談成。即使是一些更加困難的分歧,比如獨立工會問題,郭樹清在前述演講中也提出,“我們認為,罷工游行不是解決雇員與雇主爭議的有效辦法”,通過相互協商和多方監督,可以更好地實現互利共贏。可以設想,在以后的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的談判中,這個問題會逐漸找到答案。只要雙方的誠意夠,再難的問題總可以找到辦法來處理。
如果中美之間能夠談出來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相處之道,那就是創造了歷史。“不畏浮云遮望眼”,歷史不正是人創造出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