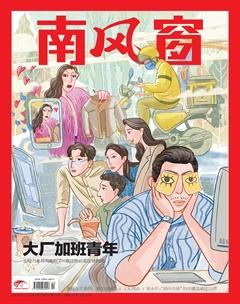中西部制造業大城的未來
楊閏然

重慶近年來發起猛攻,2020年GDP突破2.5萬億,備受熱議,成都、鄭州等中部城市也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我們無法忽視中國西部城市在工業制造業等方面的突飛猛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們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制造業過去的不斷轉移。但后疫情時代,一些國家依然可能會推進逆全球化趨勢,也會強化企業收縮產業鏈或多元化產業鏈的動機。
制造業資本不會永遠青睞同一個地方,尤其是當成本和要素在不斷發生變化的時候。那么,位于中國中西部城市的制造業是否會被其他新興經濟體,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所替代?中國中西部城市如何更好地與東南亞競爭?
產業轉移的全球競爭
重慶、成都、鄭州等城市抓住了全球產業競爭,走在了屬于自己的道路上,憑借先進制造業崛起,無疑是振奮人心的。
在傳統的概念里,全球產業鏈具有三級分工:消費、生產、資源,對應不同的國家區域,生產國從資源國購買資源進行生產,再賣到消費國。長期以來,中國都是一個生產國的角色。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中國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具有吸引力的優惠政策,形成制造業巨大的洼地優勢,把全世界的產能吸引到了中國。
20世紀,全球總共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第一次產業轉移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將紡織、鋼鐵等傳統制造業向日本、西德轉移,進行海外投資以及資本運輸。第二次產業轉移則在20世紀70到80年代,日本、西德將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推動了“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
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了第三次產業轉移。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將失去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一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
那一時期,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產業鏈相對較短。產品的零部件、原材料從全世界運到中國沿海,又從中國沿海把整機銷售到世界,依靠的是沿海地區強大的區位條件和物流優勢。因此佛山、東莞這類外貿明星城市工業和制造業非常發達。
但在產業由中國沿海地區向內陸轉移的過程中,制造業的產業鏈逐漸發生了變化。比如重慶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產量約占全球的40%。重要的是,筆記本電腦生產企業英業達、富士康、仁寶、緯創等已在重慶落地研發中心。
當然,對于重慶等這幾座迅速崛起的中西部內陸城市,區位優勢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大部分位于長江流域。此外,成都、鄭州等城市在空港經濟方面逐步發力,增強了產業鏈中的資源配置能力。
再看看東南亞國家的發展現狀,從國家工業增加值來看,東南亞國家工業增加值遠不及中國。有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現價工業增加值為5.59萬億美元,印度體量為7153億美元,僅為中國的12.8%;泰國、菲律賓、越南體量則更小,分別為1815億美元、1136億美元和903億美元,為中國的3.3%、2%和1.6%。
印度工業生產能力約為中國制造業第一大省廣東省的1.3倍。泰國、菲律賓、越南工業生產能力可位列中國省市第9、第16、第18位,分別與湖南、重慶、內蒙古相當。
從整體趨勢上來看,這幾個國家的增速也遠低于中國。有研究者計算過,如果將中國各地工業增加值折算為美元,印度工業生產能力約為中國制造業第一大省廣東省的1.3倍。泰國、菲律賓、越南工業生產能力可位列中國省市第9、第16、第18位,分別與湖南、重慶、內蒙古相當。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
全球產業鏈就好比串聯電路,一環扣一環,中國一直嘗試通過產業升級,在全球制造業的產業鏈上不斷攀登高附加值環節。從美國的加稅目錄也可以看出,它主要針對中國的先進制造業,因為它們都代表著國家的硬實力。
中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階段,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孕育著大量消費升級需求,在這足夠大的市場中,將會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創新點。
這些年,中國勞動力漲幅大于東南亞國家,勞動力絕對成本優勢在逐步削弱。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約為381美元/月,為美國的9.8%,而到了2018年,這一比例攀升至19.6%。8年間,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上漲138.8%。2018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制造業薪資是泰國的約2倍,菲律賓、越南的約3倍。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對勞動力的要求,隨著全球產業鏈的升級也發生了變化,整體趨勢是逐步由“人口紅利”過渡到“人才紅利”。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勞動力質量上,中國受教育程度遙遙領先,2010年中國超過60%的人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
而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勞動力中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比例,均與中國存在約20個百分點甚至更高的差距。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教育普及程度近幾年仍在不斷提高。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勞動力質量的重要指標,與產出能力具有正向關系。
中國勞動力生產率也穩步提高,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制造業依然具有相對成本較低的優勢。因為中國勞動力生產率在8年間提高30.7%,從2010年的4315美元/人上升到2018年的5638美元/人。
事實上,類似于全球手機及電子產業已經滲透到了一定階段、增長趨緩,“代工帝國”們也摸到了天花板,試圖通過轉型來重新定義自己。比如被譽為世界工廠的富士康早已不滿足于“蘋果代工廠”的頭銜,一直在尋求更多業績增長點,譬如數字醫療、機器人和汽車等領域。
2021年開年的第一個月,富士康先后與拜騰、吉利聯合發布消息,為前者提供制造工藝、運營管理經驗和產業鏈資源,加速推進拜騰汽車旗下首款車型M-Byte的量產工作,與后者成立一家合資公司,為第三方汽車企業代工。
汽車代工,其復雜程度完全不同于“電子廠”,很有可能成為一家企業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過渡到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關鍵。
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大企業之間的競爭。中國出口產品不斷向價值鏈上游攀升,象征著中國制造業將進一步走向高附加值領域。2020年11月,機電產品出口占比提升至62.0%、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提升至32.1%,集成電路、計算機、醫療器械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強勁,同比增速分別達26.4%、31.2%和 19.5%。
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勞動力生產率仍有一段距離—2018年為美國的61.9%,德國的71.2%,日本的62.1%。但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菲律賓、越南以及泰國,并且不斷拉大差距。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勞動薪資增長,但中國制造業,尤其是在高端技術產業方面依然具有相對成本較低的優勢。
制造業配套至關重要
短期內,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制造業的替代有限。但從長期來講,東南亞國家的發展仍存在一定的挑戰。比如中國能源成本已不占優勢。能源價格是企業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柴油、汽油零售價與印度相近,越南、泰國、菲律賓均相對比之下更具優勢。
這些年,一些韓國和日本企業紛紛南下設廠。隨著中國手機產業的崛起,三星手機在中國競爭失勢,韓國早已布局東南亞,培育配套產業鏈的生長。
2019年豐田曾發布過消息,決定在緬甸迪拉瓦建立新廠房。彼時,正值緬甸政府提高進口壁壘,試圖建立當地的汽車產業。此前豐田也考慮在緬甸建廠,除了緬甸,豐田在泰國、印尼等國家也有工廠布局,但這些地區無一例外都擁有同樣的劣勢,當地市場相對較小,相關供應商的配套不是很充足。所以豐田計劃在當地進一步建設供應鏈,實現零部件的本土化。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大陸地區物流績效綜合指數達到3.61,在全球范圍內名列前茅,印度、菲律賓、泰國、越南分別為3.13、2.93、3.41、3.27。
但在豐田當年的目標中,中國依然是最重要的市場。中國是許多大企業最重要的市場,但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生產基地了。富士康也是如此,原本在廣西南寧生產的網通產品,如今已轉移到越南北寧,主要原因在于蘋果已經規劃在中國及海外搭建兩套供應鏈體系,貿易安全是主因之一。
對中國而言,龐大的經濟縱深確實使得中國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產業配套能力。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220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且產業鏈條非常完備。隨著下游企業步入數字化升級,傳統的工業制造業模式有可能面臨終結,制造業內需潛力也將不斷釋放。
制造業配套,很重要一點就是國家基礎設施水平的建設,正如豐田長期以來在東南亞布局的顧慮。
世界經濟論壇數據顯示,2019年,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國在交通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不同維度上都與中國存在明顯差距,尤其是內外暢通的綜合運輸大通道。
另外在物流方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大陸地區物流績效綜合指數達到3.61,在全球范圍內名列前茅,印度、菲律賓、泰國、越南分別為3.13、2.93、3.41、3.2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慶是中歐班列的開拓者,它正成為重慶及整個內陸地區一條穩定、高效的貨物通道,以此來構建國際物流分撥網絡體系。
2020年,中歐班列(渝新歐)“中國郵政號”專列順利首發。此后,以中歐班列(渝新歐)為載體,重慶承擔起疏運國際郵包尤其是中歐間國際郵包的重任。目前,中歐班列(渝新歐)已成功疏運全國總量1/3、歐洲將近七成的國際郵包,這種影響還能擴大到整個成渝城市群,為中西部城市提供強有力的樞紐競爭力。
但競爭遠未結束。短期內,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制造業的替代有限。在未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中西部城市依靠強大的制造業配套,包括產業鏈、物流、金融等,還是能夠拉開與國外的成本差距,守住這一點至關重要。
對于一座城市、一個國家而言,成為制造業的強者,融入世界的開放道路是大國經濟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在面對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時,更需依托于強大的市場,未雨綢繆,放大優勢,將主動權牢牢抓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