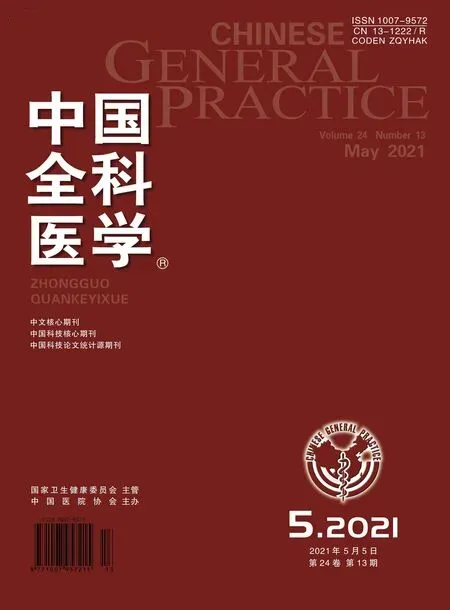基層門診問診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的直接觀察性研究
周夢萍,匡莉*,羅卓君,梁翠瑩,李麗娜,楊斯曼,鐘陳雯
臨床預防服務能有效地控制疾病惡化、預防或延緩各種并發癥、降低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提高質量調整生命年、減少后期昂貴醫療資源(如住院服務的可能性),是公認的成本效益良好的預防服務[1-3]。基層全科醫生是國際公認的最恰當的臨床預防服務提供者[4],其擁有最多的提供臨床預防服務的機會,也最可能為患者提供貼近需求的個體化預防服務。門診問診是基層全科醫生提供臨床預防服務的最適合時機[5-6]。據調查,70%~80%的患者首診發生在基層,大多數患者及家屬一年內都有機會去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7]。但是目前評估我國居民預防服務提供率的研究主要來自兩類:一是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計算獲得,由于CHNS數據基于居民自報,且調查樣本中大部分為健康人群,所以所得評估結果存在低估可能;二是通過醫生自我報告進行估算,但由于醫生自報可能存在社會期望效應,所以評估結果存在高估可能。此外,也有研究從患者角度測量其對綜合性服務(包括臨床醫療服務和預防性服務)的感受度[8-9],但目前暫無研究從服務提供者即全科醫生的角度測量我國臨床預防服務的實際提供水平。本研究運用直接觀察研究方法,以基層全科醫生問診作為觀察對象,采用規范的醫生問診內容編碼工具,對全科醫生問診內容中的預防服務項目進行結構化和定量化描述,以測量真實臨床環境下基層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同時將本觀察結果與國外同類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借此評價本土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及差距,進而提出政策建議。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8年7月—2019年1月,采用三階段抽樣策略確定調查對象。首先,選取廣東省8家全科醫療發展較好、全科醫療實踐模式多樣化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作為調查機構;其次在每家調查機構,招募2~3名全科醫生作為觀察對象,醫生納入標準為臨床經驗較豐富、患者量較多、工作在臨床一線、知情同意并自愿參加本研究者;之后,隨機選取觀察醫生開診日,將全科醫生開診日接診的所有患者問診納入觀察,患者納入標準為年齡≥18歲、本人知情同意且自愿參加本次研究。本研究共觀察了18名醫生的649名患者的門診問診。本研究項目通過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中大公衛醫倫[2018]第014號)。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設計 本研究采用直接觀察及錄音方式,具體研究設計和方法可見本課題組前期發表的國際期刊論文[10]。
1.2.2 醫生問診內容的編碼工具與編碼實施 采用經過信效度驗證的戴維斯觀察代碼(Davis Observation Code,DOC)編碼工具,對全科醫生門診問診內容進行結構化和定量化描述[11]。DOC編碼將全科醫生問診內容分為5個大類27個服務項目,具體類別包括臨床技術、健康行為、患者主動參與、預防服務和文書及其他類別。其中,預防服務類別包括7個服務項目,具體有疾病篩檢和疫苗接種、心理情緒咨詢、營養咨詢與建議、運動咨詢與建議、睡眠咨詢與建議、物質依賴咨詢與建議、吸煙行為咨詢與建議。
采用NVIVO 11.0軟件,對醫生問診過程中所有內容進行編碼。按照DOC編碼要求,將醫生對患者問診全過程按15 s作為一個時段單位進行劃分,編碼員根據音頻內容,將每個時段中所發生的服務項目逐一進行DOC編碼,同時記錄服務項目持續的時間長度。
1.2.3 內容分析與指標 通過記錄DOC編碼、時長(s)、時段數(15 s為一個時段),得到全科醫生對每個患者問診過程中是否提供某服務項目、該服務項目的時長、出現該服務項目的時段數及該時段數占總時段數的比例等基礎數據。進而利用基礎數據計算出描述全科醫生提供預防服務的指標值:(1)某服務項目的患者覆蓋率,表示醫生在所有接診患者中,總體上為其中多少患者提供了某項預防服務,反映提供某預防服務項目的廣度。(2)全科醫生在所有接診患者中,提供某服務項目的平均時段數,大致表示醫生平均到每一個患者所花費的該服務項目的時間,反映醫生總體上提供預防服務項目的時間消耗。(3)全科醫生在所有接診患者中,提供該服務項目的時段數占總時段數比例的平均值,表示醫生問診過程中對某服務項目的時間分配比例,反映對該服務項目的重視度。(4)提供某項預防服務項目平均花費的時間,表示全科醫生提供該服務項目所消耗的時間資源。顯然,消耗時間越長,表明醫生提供該服務項目越精細和全面,反映提供該服務項目的精度。
1.2.4 質量控制 (1)調查過程中,調查員坐在距離醫生和患者較遠且不醒目的位置,保證不影響門診問診過程。(2)4名編碼員均為接受過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教育的碩士研究生,正式編碼前經過共同培訓和DOC編碼學習;編碼員間的編碼一致性系數為0.81,一致性程度高。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描述性方法分析全科醫生的基本情況和門診問診中各項臨床預防服務項目的情況。連續性變量用(±s)表示,分類變量用相對數表示。
2 結果
2.1 全科醫生基本情況 18名全科醫生中,13名(72.2%)來自西醫科室,11名(61.1%)為男性,平均年齡為(40.2±6.5)歲,16名(88.9%)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他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18名全科醫生基本情況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18 general practitioners
2.2 18名全科醫生提供臨床預防服務的水平 在649名門診患者問診中,18名全科醫生為28.7%(186名)門診問診提供了至少一種臨床預防服務項目;其中僅有3名醫生為≥50%的門診問診提供了至少一種臨床預防服務項目(見表2)。

表2 各全科醫生提供臨床預防服務門診就診比例Table 2 Proportion of consultations incorporating clinical preventive services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2.3 全科醫生提供各預防服務項目的情況及與國外同類研究的對比 表3顯示了649名門診患者問診中基層社區全科醫生提供預防服務項目的情況及STANGE等[12]、WEYER 等[13]和 CALLAHAN 等[14]對美國基層家庭醫生問診內容的測量結果。由于這些研究均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編碼工具,結果間具有良好的橫向可比性。
本研究所觀察的18名全科醫生的平均每個患者問診時長為(5.4±3.5)min。表3包括了7類預防服務項目提供情況。以疾病篩查和疫苗接種項目為例,在接診的649名患者中,該服務項目的患者覆蓋率為9.4%(61/649),即醫生約為9%的門診接診患者提供了該服務項目;在提供了該項服務項目的問診中,該服務項目所花費的平均時間為(15.8±15.6)s;在總體問診中,即以平均到649名患者計算,醫生為每一個患者提供該服務項目的時段數為0.23個,即平均花費在每個患者的時間為3.45 s(0.23×15 s);醫生提供該服務項目的時段數占總時段數比例的平均值為(0.93±5.35)%,表示醫生僅將不到1%的接診時間分配到疾病篩查和疫苗接種項目。與國際同類研究比較,STANGE等[12]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基層家庭醫生為33%的門診接診患者提供了疾病篩查和疫苗接種項目;在總體問診中,以平均到4 401例患者計算,醫生為每一個患者提供該服務項目的時段數為1.0個,即平均花費在每個患者的時間為15 s(1.0×15 s);醫生提供疾病篩查和疫苗接種項目的時段數占總時段數比例的平均值為3.0%,WEYER等[13]研究該指標結果為3.7%。

表3 全科醫生門診問診臨床預防服務項目的提供水平Table 3 Level of clinical preventive services provided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during outpatient consultations
3 討論
本研究以廣東省8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8名基層全科醫生649例患者門診問診作為觀察樣本,運用直接觀察研究方法和DOC編碼工具,測量基層臨床預防服務的提供水平。結果顯示,在真實臨床環境下,基層全科醫生的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不足,無論是患者覆蓋率、預防服務精度、預防服務重視度都低于國外同類研究結果。
從醫生提供預防服務項目所花費的絕對時間看,平均花費時間僅為5.9~17.6 s,50%的患者預防服務項目時間為2.8~26.0 s。顯然,醫生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向患者提供健康行為的咨詢和建議內容,只能限于表述為“少吃一點、多運動、早點睡覺、不要抽煙了”等泛泛和粗淺的建議,難以展開深入細致的專業性咨詢建議,預防服務的精度無法到位。
以醫生接診的所有患者計算,本土醫生提供預防服務項目的患者覆蓋率為2.0%~13.4%,遠遠低于STANGE等[12]報道的9%~33%的結果,表明本土全科醫生只向較少的患者提供了預防服務,預防服務的患者覆蓋率較低。這與國內學者研究結果也較為一致,研究表明基于CHNS數據計算獲得的2006年45歲以上成人接受預防保健服務率為3.78%[2],2009年18歲及以上居民接受預防保健服務率為4.2%[15]。就提供預防服務項目的平均時段數和提供服務項目時段數占總時段數比例而言,本研究結果均低于STANGE等[12]、WEYER等[13]和CALLAHAN等[14]的研究結果,而美國這三項研究結論都揭示了美國基層家庭醫生的臨床預防服務提供率低于該國臨床預防服務指南推薦標準。基于此,可以認為研究所觀察的本土基層全科醫生的預防服務提供水平處于很低水平。
導致我國基層全科醫生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過低的可能原因較多:一是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全科醫生基本都是由歷史上地段醫院的專科醫生經過在崗培訓后轉換而來,其觀念和知識結構的更新和鞏固與政府和居民的期望值還存在較大差距,大部分家庭醫生在提供服務過程中還習慣于采取專科醫療服務的理念和模式。二是因為全科醫生工作量大,患者問診時間短,沒有多余時間提供臨床預防服務。研究表明診療量大和時間有限是醫生認為的導致臨床預防服務提供不足的最重要障礙因素[16-17]。全科醫生在一次患者問診過程中需要完成多重任務,首先要考慮滿足患者的即時主要需求,在問診時間短的情況下,提供預防服務可能就退而求其次。本研究中649例患者門診問診時間平均為(5.4±3.5)min,與國內其他類似研究結果一致(5.6 min)[18]。醫生問診時間短的背后,是基層全科醫生每次高企的門診量。本次觀察的18名全科醫生,有7名醫生在當天當班次(即半天的出診時間)的患者超過40人,最高的一個醫生門診量竟高達72人。而英、美、加等部分國家全科醫生全天患者數為15~30人,每個患者問診時間多在10~20 min[19]。三是我國目前尚沒有專門的臨床預防服務指南,基層全科醫生執行臨床預防服務項目時缺乏規范統一的指引,有些臨床醫生對臨床預防服務的理解存在較大偏差,甚至認為臨床預防服務就是到社區開展人群調查,完成人群行為與生活方式的監測[20]。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是盡快制定專業的臨床預防服務指南,幫助醫生系統了解和掌握臨床服務指南知識和技能,提高自我效能,增強服務的可執行性;二是解決基層全科醫生人力資源極度缺乏的問題,增加基層全科醫生的培養和招募,保證門診問診充足的醫患接觸時間;三是要盡早建立健全全科醫學的臨床預防醫學教學體系,培養全科醫生具備充足的臨床預防醫學知識和技能;四是改變患者就醫環境,提高患者對臨床預防服務的感知。例如,通過設置宣傳欄、張貼海報、播放電視和散發紙張材料等方式介紹臨床預防服務,加大環境誘因,激發患者對預防服務的認知和需求,提高服務利用。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兩點局限性:一是本研究選取了發展較好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經驗較豐富的全科醫生,機構和醫生不能代表整體水平,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高估整體的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二是本研究觀察的臨床預防服務以咨詢類服務為主,不能夠反映一些問診時候進行的篩查服務和預防性用藥等,一定程度上可能會低估臨床預防服務提供水平。
作者貢獻:周夢萍、匡莉、鐘陳雯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周夢萍、羅卓君、梁翠瑩、李麗娜、鐘陳雯負責數據收集;周夢萍、羅卓君、梁翠瑩、楊斯曼、鐘陳雯負責數據整理;周夢萍負責統計學處理、結果的分析與解釋、論文撰寫;周夢萍、匡莉負責論文的修訂;匡莉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