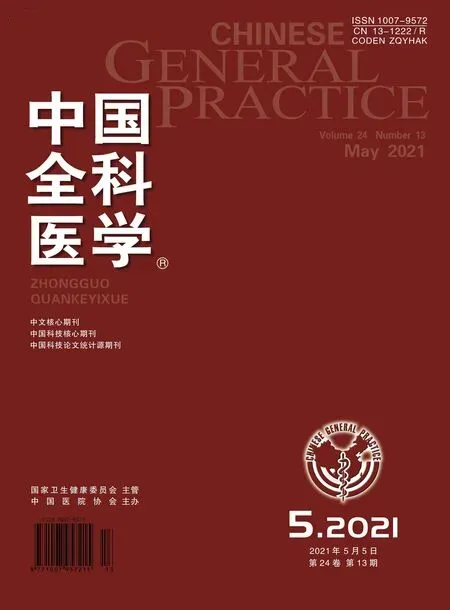醫教協同背景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及影響因素研究
鄧黎黎,廖曉陽*,鄒川,伍佳,程春燕,趙茜,王莉斐,羅曉露
《關于深化醫教協同進一步推進醫學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加強以全科醫生為重點的基層醫療衛生人才培養,必須強調醫教協同[1]。該培養模式以醫學衛生人才的崗位勝任能力及社會需求為導向。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與成都市武侯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早在2010年就實現了跨院區全科醫生醫教協同培養模式。在醫教協同人才培養模式實際運行中發現存在醫學教學內容與崗位需求、培養目標不能完全對接等問題[2]。世界家庭醫生組織(WONCA)明確規定溝通技能是全科醫生必備的核心能力之一[3]。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只有49%的中國醫學院校開設了醫患溝通課程[4],而全科醫生溝通技能相關培訓研究僅占所有醫療教育培訓研究的4.9%[5]。2019年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全科醫生溝通能力整體水平較低,尤其是社區全科醫生[6]。如何開展針對性溝通技能培訓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顯示以需求為導向的培訓模式可快速滿足臨床需要,提高教學質量[7-9]。因此很有必要對全科醫生的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及影響因素進行調研。鑒于此,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法,了解“華西醫院-社區”醫教協同體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制定以需求為導向的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內容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18年10月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華西醫院-社區”醫教協同體下承擔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社區基地內所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共12家的全部104例全科醫生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經過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或轉崗培訓,并取得合格證書;(2)目前從事臨床一線工作的全科醫生;(3)工作年限≥1年。排除標準:外聘專家。
1.2 研究方法
1.2.1 調查問卷 在查閱文獻和專家咨詢的基礎上自行編制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括以下3部分:(1)全科醫生基本信息(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稱、工作年限、接診時間、與患者溝通是否使用技巧)、對醫患溝通重要性的認識、醫患溝通能力自評、醫患關系滿意度自評、醫患信任程度自評(采用Likert 5級量表分別賦值1~5分)及既往參加溝通技能培訓情況(包括是否參加及參加培訓的內容)。(2)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多項選擇)及參與意愿。溝通技能培訓需求是根據“卡爾加里-劍橋指南”內開始接診、采集病史、傾聽、表達同理心、建立關系、解釋病情、共同決策、結束會談8個溝通技巧進行設計。“卡爾加里-劍橋指南”是北美地區常用的教學和評估溝通指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全世界各級醫學教育中作為主要教學資源使用[10-12]。(3)(醫生層面)醫患溝通影響因素(多項選擇)。
1.2.2 調查和質量控制 通過查閱文獻和專家咨詢保證了問卷設計的科學性。在調查問卷確定后制作成問卷星在10例全科醫生中進行預調查,測得問卷Cronbach's α系數為0.963。于2018年10月將問卷通過二維碼或鏈接先發送至各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人,然后再由中心負責人發送給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全科醫生,由全科醫生自愿填寫提交,為期1周。在發送問卷前采用統一指導語通過口頭講授對2名志愿者進行調查目的、重要性及填寫注意事項的培訓。其中1名志愿者在全科醫生進行電子問卷填寫時,進行網上答疑,另1名志愿者進行后臺問卷質量控制確保數據合格真實。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3.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或Fisher's確切概率法;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的影響因素。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共發放問卷104份,回收有效問卷104份,有效回收率為100.0%。其中,男28例(26.9%),女76例(73.1%);年齡25~60歲,平均年齡(40.3±7.6)歲;從事全科工作1~30年,平均工作年限(10.3±5.5)年;學歷以本科及以上學歷為主,占76.9%(80/104);職稱以中、高級職稱為主,各占54.8%(57/104)、30.8%(32/104);全科醫生接診1位患者所用時間為5~10 min占比最多,為54.8%(57/104);會使用溝通技巧的占比為94.2%(98/104),有培訓經歷的占比為66.3%(69/104)。全科醫生對溝通能力自評為好和非常好、醫患關系自評為滿意和非常滿意、醫患信任自評為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占比分別為55.8%(58/104)、77.9%(81/104)和78.8%(82/104);認為醫患溝通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全科醫生占95.2%(99/104);有培訓參與意愿的全科醫生占81.7%(85/104,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比較〔n(%)〕Table 1 Comparison of need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s in general practitioners by demographic factors

(續表1)
2.2 全科醫生既往溝通技能培訓內容參與情況 既往參加過溝通技能培訓的全科醫生占66.3%(69/104)。在培訓內容選擇方面接受過建立關系培訓的人占比最多,為82.6%(57/69),接受過傾聽、采集病史和共同決策培訓的人占比分別為68.1%(47/69)、53.6%(37/69)和37.7%(26/69),接受過表達同理心培訓的人占比最少,為29.0%(20/69)。其中培訓內容全部參加過的全科醫生占比為17.4%(12/69),參加了4、3、2、1項培訓內容的全科醫生占比分別為13.0%(9/69)、17.4%(12/69)、29.0%(20/69)和21.7%(15/69)。
2.3 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情況 104例全科醫生均有提升溝通技能的需求。在培訓需求方面,選擇共同決策需求人數最多,占59.6%(62/104),其次為建立關系,占51.0%(53/104)(見表2)。

表2 醫教協同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情況Table 2 Content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s needed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synergy of health care system and medical educational system
2.4 醫患溝通影響因素 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醫患溝通的醫生原因選擇方面,93.3%(97/104)的全科醫生選擇“工作任務繁忙,沒有時間精力”,53.8%(56/104)的全科醫生選擇“缺乏溝通技巧,不會和患者有效溝通”,39.4%(41/104)的全科醫生選擇“對醫患溝通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看病是醫務人員的事,和患者溝通作用不大”,27.9%(29/104)的全科醫生選擇“醫學專業知識欠缺,臨床水平低”,26.0%(27/104)的全科醫生選擇“沒有熱情和耐心”,9.6%(10/104)的全科醫生自訴是“對患者和自己情緒、認識覺察不夠”。
2.5 不同特征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比較 不同性別的全科醫生對開始接診、采集病史的培訓需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年齡的全科醫生對表達同理心的培訓需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文化程度、職稱的全科醫生對共同決策的培訓需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培訓經歷的全科醫生對傾聽的培訓需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溝通能力自評情況、醫患關系滿意度的全科醫生對建立關系、解釋病情的培訓需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6 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稱、培訓經歷、醫患溝通能力自評和醫患關系自評為自變量(賦值詳見表 3),分別以各項培訓需求內容(除外結束會談)為因變量(賦值:是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1,否=0)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是采集病史和表達同理心是否為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影響因素;培訓經歷是傾聽是否為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影響因素;年齡是表達同理心是否為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影響因素;溝通能力和醫患關系自評情況是建立關系和解釋病情是否為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影響因素;文化是共同決策是否為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4)。

表3 影響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回歸模型賦值表Table 3 Assignment fo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ent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s needed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alyzed with a regression model

表4 醫教協同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影響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ent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s needed by general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synergy of health care system and medical educational system
3 討論
3.1 需重視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使培訓內容更規范化、系統化 隨著醫患關系緊張升級,以及在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大力發展全科醫學、建立社區衛生服務的大背景下,開展溝通技能培訓、提高全科醫生溝通能力已成為必然趨勢。隨著醫教協同培養模式的加強,我國建立了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優化了全科醫生培養結構,緩解了全科醫生短缺的問題,但還存在“重技術培養、輕人文教育”的現象[13]。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只有49%的中國醫學院開設了醫患溝通課程[4],針對全科醫生的溝通技能培訓則更少[5]。在本次研究中,95.2%的全科醫生認為醫患溝通重要,全科醫生的溝通技能培訓需求率為100.0%,與徐婷等[14]對上海市全科醫生溝通需求的調查結果相似。這說明現有全科醫生培養中,非常欠缺溝通技能的培養。此外,在本次調查中全科醫生參加過的溝通技能培訓內容數量各不相同,說明既往培訓缺乏規范性、系統性。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滿足不同全科醫師崗位角色轉變需求的溝通培訓內容。
3.2 動態持續評估培訓需求是保證培訓效果的關鍵 研究顯示溝通技能是可以傳授、學習的,而且總是可以提高,掌握的能力可以保持多年[15-17]。研究顯示與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相比,醫教協同人才培養模式學員崗位核心能力得到提高,教學質量得到提升[18]。但2019年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全科醫生溝通能力SEGUE量表評分總分為〔(14.6±6.7)分,n=300〕, 低于美國通科醫生〔(17.3±1.8) 分,n=500〕[6],可能原因是培訓內容與培訓需求脫節。本研究調查顯示全科醫生既往參加溝通技能培訓內容中建立關系占82.6%,傾聽占68.1%,采集病史占53.6%,共同決策占37.7%,表達同理心占29.0%,而在培訓需求中建立關系占51.0%,傾聽占18.3%,采集病史占16.3%,共同決策占59.6%,同理心占34.6%。提示既往培訓內容與對未來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之間存在差異;既往培訓內容不能滿足全科醫生醫患溝通技能培訓的需要;隨著工作時間、實踐、經歷及工作環境等的變化,為了保證培訓效果,需要動態持續評估培訓內容,構建新的溝通技能知識體系。
3.3 對全科醫生進行醫患溝通技能培訓需要重視個性化影響因素 本研究通過Logistic回歸篩選出影響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因素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培訓經歷、溝通能力和醫患關系滿意程度。其中性別是影響開始接診、采集病史需求的因素,相對女性,男性對開始接診、采集病史的培訓需求更高。這可能是由女性的性格特點決定,女性比男性更加細膩、委婉。有研究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加以患者為中心,能收集更多社區心理問題[19-20]。培訓經歷是影響傾聽需求的因素,與有培訓經歷的全科醫生相比,沒有培訓經歷的全科醫生對傾聽的培訓需求更高。這可能是因為參加培訓后全科醫生掌握了傾聽技巧,因此培訓需求減少。年齡是影響建立同理心需求的因素,這可能是因為:(1)隨著年齡增長,全科醫生在生活、工作中的經驗體會更加深刻,能夠更加以患者為中心,理解患者內在的體驗和感受;(2)年輕全科醫生由書本理論知識轉變真實實踐操作中缺乏表達同理心的能力。文化程度是影響共同決策需求的因素,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對共同決策的培訓需求減少,這可能是因為文化程度越高知識儲備越多,告知信息越豐富,與患者交換信息更便捷,達到共同決策越快速容易[21]。溝通能力與醫患關系滿意度是影響建立關系、解釋病情需求的因素,隨著溝通能力與醫患關系滿意度的提高,對建立關系、解釋病情的培訓需求減少,這可能是因為溝通能力、醫患關系滿意度越高,全科醫生越自信,患者越信任醫生,因此在與患者溝通過程中關系融洽,患者更能理解信任醫生解釋有關其病情的內容。因此在以后的溝通技能培訓中應加強男性開始接診、病史采集的培訓,對未接受過溝通技能培訓經歷者應加入傾聽的培訓,對工作年限短者應加強同理心的培訓,對文化程度低者應加強共同決策的培訓,對溝通能力差、醫患關系滿意度低者應加強建立關系、解釋病情的培訓。在對全科醫生進行溝通技能培訓時,不能一概而論、持久不更,應該根據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有無培訓經歷等全科醫生的培訓需求,設置培訓目標,構建培訓內容,才能具有新穎性、針對性、實操性,才能調動學員學習積極性,使培訓真正行之有效。
3.4 關注全科醫生視角下醫患溝通的影響因素 加強醫教協同,雖然緩解了全科醫生短缺的問題,但這與“到2030年,城鄉每萬名居民擁有5名合格全科醫生”的目標還有一定的差距[22];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每2 000人配置1名全科醫生的標準相比,估計我國全科醫生缺口至少在45萬人左右[23]。全科醫生數量嚴重不足,導致其工作強度大,職業倦怠嚴重。2019年調查顯示我國全科醫生平均每日工作時間為7.3 h,需要加班者占94.4%[24],過高的工作強度導致全科醫生沒有時間精力與患者溝通。這與本次調查發現基于全科醫生視角影響醫患溝通醫方因素主要是“工作任務繁忙,沒有時間精力”結果一致。因此醫教協同還需繼續深入,加大合格全科醫生培養力度,緩解其工作壓力和負擔,讓其有時間和精力參與溝通學習;同時可以增加“互聯網+”的培訓模式讓全科醫生可以利用碎片化時間進行系統化培訓。另外,影響醫患溝通的醫方因素還包括“缺乏溝通技巧,不會和患者有效溝通”,這與醫教協同“重技術培養、輕人文教育”的現象不謀而合,也說明加強醫教協同背景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的必要性。
3.5 局限性 本研究樣本量較小,采用整群抽樣法,只能代表武侯區綜合醫院-社區醫教協同體下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需求。但因所選區域不乏示范性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且承擔著全科醫生規范化培訓工作,調查結果也能說明當前全科醫生對溝通技能的需求高及對培訓的迫切需要。今后研究應該增大樣本量、擴大調查范圍,在定量研究基礎上增加定性研究,探究影響全科醫生不愿意參加醫患溝通培訓的因素,剖析深層原因,從而更加全面地評估全科醫生溝通技能培訓。
綜上所述,全科醫生對醫患溝通重視,對溝通技能培訓需求高,參與意愿強烈。全科醫生培訓需求內容與既往培訓內容存在差異。培訓內容受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諸多因素影響。因此需要持續動態評估培訓需求,明確培訓目標,才能保證培訓質量。
作者貢獻:鄧黎黎、廖曉陽、程春燕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羅曉露負責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數據收集;鄧黎黎、王莉斐負責數據整理;鄧黎黎負責統計學處理和論文撰寫;鄧黎黎、鄒川、伍佳負責結果的分析與解釋;廖曉陽、鄒川、伍佳、程春燕、趙茜負責論文的修訂;鄒川負責英文的修訂;廖曉陽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鄧黎黎、廖曉陽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