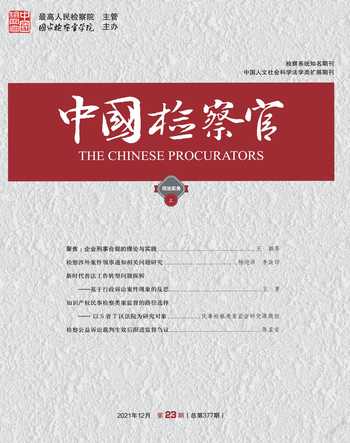檢察涉外案件領事通知相關問題研究
楊迎澤 李政印
摘 要:領事通知制度對于堅持程序正義,保障在華外國人以及我國海外公民權(quán)利,避免外交摩擦等具有重要意義。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第一審外國人犯罪案件,除刑事訴訟法第20條至第22條規(guī)定的以外,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基層檢察機關在履行領事通知義務中面臨新的問題,特別是義務履行中的程序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和規(guī)范。面對領事通知權(quán)利救濟困難的現(xiàn)實窘境,其權(quán)利保護應該在國內(nèi)法和雙邊條約層面共同發(fā)力,形成權(quán)利保護的國內(nèi)法、國際法體系。
關鍵詞:領事通知權(quán) 程序問題 權(quán)利救濟 國際法 締結(jié)條約
一、問題的提出
領事通知權(quán)是《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以下簡稱《維約》)中規(guī)定的權(quán)利,主要是指被采取逮捕、監(jiān)禁、羈押等拘禁措施的外國國民有權(quán)被立即告知,其有權(quán)得到派遣國領事協(xié)助,接受國有義務迅速通知國民國籍國;經(jīng)被拘禁外國國民請求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立即通知派遣國領館,派遣國領事可以在法定范圍內(nèi)為本國國民提供協(xié)助。
國際司法實踐中,國際法院通過在一系列判決中解釋《維約》第36條,明確指出公約創(chuàng)設了領事通知這項個人權(quán)利。當前,世界經(jīng)濟全球化和國際交往日益頻繁,領事保護逐漸同外交保護和人權(quán)保護相聯(lián)系,促使各國更加注重保護在海外公民的合法權(quán)益。[1]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沿線國家國民在華人數(shù)和各種活動日益增多,各國不斷加強對在華國民和在華利益的保護,進而產(chǎn)生了諸多領事通知權(quán)問題。
司法實務中,領事通知權(quán)保護存在著實踐不足、規(guī)范缺乏雙重問題。一方面,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第一審外國人犯罪案件,除刑事訴訟法第20條至第22條規(guī)定的以外,均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由于刑事涉外案件數(shù)量總體較少,有些基層檢察院一年甚至數(shù)年沒有涉外案件發(fā)生,因此涉外案件一旦發(fā)生,或忽略了履行領事通知義務,或因程序不明、規(guī)范缺乏而不能有效保護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quán)益,甚至引發(fā)外交事件。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對領事通知僅進行了粗線條的規(guī)定,相關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層面,都存在救濟乏力的現(xiàn)實困境。
因此,本文聚焦于檢察機關履行領事通知義務中的程序問題,對其基本原則、法律適用、具體實踐問題進行分析論述并提出合理化建議。
二、領事通知的程序問題
(一)領事通知義務主體的區(qū)分性
根據(jù)《維約》第36條規(guī)定,領事通知權(quán)主要是針對派遣國國民受逮捕或監(jiān)禁或羈押候?qū)彛蚴苋魏纹渌绞街薪樾巍T谖覈I事通知義務主要體現(xiàn)在對外國人采取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拘留、逮捕等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時。根據(jù)《維約》規(guī)定,領事通知義務一般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將相關權(quán)利迅即告知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包括:(1)有權(quán)選擇是否通知其本國領事的權(quán)利;(2)請求轉(zhuǎn)遞其書信給其本國領館的權(quán)利;(3)接受或者拒絕任何領事協(xié)助的權(quán)利。二是經(jīng)外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應迅即通知派遣國領館。[2]受逮捕、監(jiān)禁、羈押或拘禁之人致領館之信件亦應由該當局迅予遞交。
根據(jù)權(quán)利內(nèi)容來看,本文認為,應該對檢察機關領事通知的義務主體進行二元區(qū)分。首先,具體辦案部門負責向外國人告知其所享有的相關權(quán)利。其次,省級人民檢察院承擔向外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屬使領館通知的義務。對于檢察機關在何種情況下負有領事通知義務,存在全程負責說和檢察辦案環(huán)節(jié)說兩種不同觀點。
全程負責說認為,檢察機關全流程參與刑事案件立案偵查、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刑事執(zhí)行等,因此應全流程負責涉外案件辦理中的領事通知事宜。檢察辦案環(huán)節(jié)說認為,刑事訴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我國司法辦案是接力式,如普通刑事案件,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從公安偵查到檢察院審查起訴再到法院判決,具有明顯的流程性,檢察機關主要針對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案件的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履行領事通知義務更為合理。
對此,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期印發(fā)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涉外案件領事通知、領事探視等事項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若干規(guī)定》),對檢察機關領事通知義務進行了狹義界定,采用了檢察辦案環(huán)節(jié)說,對于人民檢察院在檢察辦案環(huán)節(jié)決定對外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及時履行告知義務。對于立案偵查、刑事審判、刑事執(zhí)行各階段,本文認為,檢察機關應當同時兼顧全程負責說的合理性,對涉外案件的領事通知義務進行監(jiān)督,充分保障外國人領事通知權(quán)利。當然,《維約》對于辦案處于何種過程、何種環(huán)節(jié)進行領事通知沒有規(guī)定,只要我國境內(nèi)采取強制措施告知即可,有關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公安廳(局)、國家安全廳(局)已經(jīng)通知外國駐華使、領館的,檢察機關不宜再次進行重復告知。
(二)領事通知義務履行的及時性
根據(jù)《關于處理涉外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外發(fā) [1995]17號,以下簡稱《規(guī)定》)第2條第1款,辦案檢察機關應當將有關案情、處理情況,以及對外表態(tài)口徑于受理案件或采取措施48小時內(nèi)報上一級檢察機關,同時通報同級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規(guī)定》既對通報時間也對通報的程序進行了明確要求,由于《規(guī)定》制定時間較早,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外國人犯罪案件由市級人民檢察院調(diào)整為基層人民檢察院辦理,《規(guī)定》沒有及時調(diào)整予以銜接,這就導致實踐中出現(xiàn)三個問題。一是通報主體發(fā)生變化。基層人民檢察院負責涉外案件辦理,意味著實際上將通報的政府外事部門下放到縣(區(qū))級政府。但在實踐中,有的基層人民檢察院向縣(區(qū))政府外事部門通報案件時,對其在外國人犯罪案件辦理中所處的地位及應辦事項并不了解。二是通報時間需要明確。《規(guī)定》中要求48小時內(nèi)報上一級主管機關,對于檢察機關而言對應為市級人民檢察院報省級人民檢察院。外國人犯罪案件下放基層人民檢察院辦理后,是否仍為48小時內(nèi)報省級人民檢察院,還是基層人民檢察院48小時內(nèi)報市級人民檢察院,市級人民檢察院48小時內(nèi)報省級人民檢察院需要予以明確。三是通報程序需要規(guī)范。若48小時內(nèi)報省級人民檢察院,基層人民檢察院能否直接向省級人民檢察院通報,還是必須逐級通報?對此,《若干規(guī)定》進行了回應,要求人民檢察院在檢察辦案環(huán)節(jié)決定對外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應當在48小時內(nèi)層報省級人民檢察院,并通報同級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
1.根據(jù)領事通知的及時性要求,對于涉外案件應當在48小時內(nèi)上報省級人民檢察院。除司法辦案時效性的必然要求外,還有幾方面的考慮,一是確保領事通報的規(guī)范性。外國人犯罪案件未下放基層人民檢察院辦理前,市級人民檢察院48小時內(nèi)上報省級人民檢察院,省級人民檢察院及時通報省級人民政府外事部門,由省級人民政府外事部門通知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屬國有關使領館。下放基層人民檢察院辦理后,若48小時內(nèi)無法上報省級檢察院,就會導致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屬國有關使領館接到通報時間較晚,甚至違反相關領事條約,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3]二是保障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quán)利。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zhí)行監(jiān)視居住、拘留、逮捕后24小時以內(nèi),通知被監(jiān)視居住人、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屬。由于涉外案件的復雜性,且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我國境內(nèi)沒有家屬的,盡早通報其所屬國使領館能充分體現(xiàn)我國司法辦案中平等保護的司法理念。三是維護我國司法公信力。長期以來,我國已經(jīng)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領事通知時間,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涉外案件辦理權(quán)限下放到基層院是我國內(nèi)部法律調(diào)整,若因為內(nèi)部法律調(diào)整而延長領事通知時間,可能會影響我國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司法公信力。
2.根據(jù)《若干規(guī)定》中領事通知的程序性要求,對于涉外案件,要層報省級人民檢察院。一方面,涉外案件辦理中,由省級人民檢察院作為涉外案件的協(xié)調(diào)部門與有關國家駐華使領館或者外國政府和機構(gòu)對接,更便于工作的展開。另一方面,層報制能夠保障上級人民檢察院了解案件信息。為加強對基層人民檢察院涉外刑事案件辦理情況的指導與監(jiān)督,對涉外刑事案件的敏感因素、政策掌握等進行充分研判,要求基層人民檢察院在審理涉外刑事案件時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通報相關情況和備案相關信息,確有必要。
(三)領事通知審核義務的全面性
領事通知內(nèi)容的全面性是領事通知必含之意。根據(jù)《規(guī)定》《若干規(guī)定》,通知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外文姓名、性別、入境時間、護照或證件號碼;二是案件相關信息和法律適用情況,包括案件發(fā)生的時間、地點及有關情況,違法犯罪的主要事實,涉嫌罪名,已采取的強制措施、地點及法律依據(jù)。此外,還應當就告知領事通知及探視權(quán)利的情況通知外國駐華使、領館,具體包括是否告知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領事通知及探視權(quán)利及告知時間、是否希望領事通知、是否接受領事通知等。
領事通知內(nèi)容全面性應以內(nèi)容準確性為前提,特別是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信息需要準確。實踐中,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國籍、姓名等需要準確核實,只有國籍身份明確,才能啟動通知外國駐華使領館工作。檢察機關審查認定國籍,首先,應當以其所持護照或者其他有效國際旅行證件為依據(jù)進行認定。其次,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持有多個外國護照或者其他有效國際旅行證件的,以其入境時持有的有效證件確定其國籍。也有觀點認為如果具有雙重國籍的人在第三國被逮捕或拘留,應以負有強制通知義務的國家優(yōu)先。對此,《維約》第36條沒有強制規(guī)定選擇其中哪一個國籍國通知,而是取決于各國實踐。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入境時持有的有效證件是對其身份的自我認可,以其入境時持有的有效證件確定其國籍,是尊重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個人選擇的體現(xiàn)。再次,由于我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對于同時持有他國有效護照和我國有效身份證件的外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根據(jù)我國國籍法的相關規(guī)定認定其國籍。最后,國籍不明的,根據(jù)公安機關或有關國家駐華使、領館出具的證明確認。國籍無法查明的,以無國籍人對待。[4]
三、領事通知權(quán)救濟缺陷與制度完善
(一)困局:領事通知權(quán)救濟三重難
由于國際社會和法治環(huán)境不斷變化,國際法領域也出現(xiàn)了領事保護與外交保護、國際人權(quán)保護相融合的傾向,領事通知權(quán)的內(nèi)涵與外延不斷豐富。人權(quán)保護理念上的革新對于外交和領事關系法也產(chǎn)生了影響,正當程序刺穿了外交和領事關系法的外衣[5],各國領事保護工作更加重視保護海外公民的權(quán)益。有權(quán)利即有救濟,但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國際法還是國內(nèi)法,都存在救濟乏力的現(xiàn)實困境。
首先,《維約》沒有規(guī)定有效的救濟方式,此為第一重難。從國際救濟實踐看,在發(fā)生損害個人領事通知權(quán)的情況下,一般有兩種解決途徑。一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即由派遣國領事與接受國進行交涉,必要時也可以由使館出面進行外交保護。二是如果無法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可以援引《關于強制解決爭端之任擇議定書》將爭議訴至國際法院。但《維約》效力有限,雖然有的國家如美國承認《維約》是自動執(zhí)行的條約,但仍然不能直接產(chǎn)生拘束美國法院的效力。至于違反領事通知義務的接受國如何提供救濟,這是國內(nèi)法上的問題,《維約》更無法做出有效規(guī)定。
其次,國際法院在案件審理中一般適用不干涉內(nèi)政原則,判決并不一定能拘束國內(nèi)法院,即便國際法院的判決對當事國有拘束力,但在一國國內(nèi)不一定有直接效力,此為第二重難。以國際法院先后審理的“Breard案”“LaGrand案”為例,美國司法部門未盡到《維約》中規(guī)定的領事通知義務,國際法院均指示了臨時措施,要求美國延遲執(zhí)行死刑。但美國未根據(jù)國際法院的指令采取有關臨時措施,Breard、LaGrand被執(zhí)行死刑。[6]
最后,從國內(nèi)法律看,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相應的救濟措施,此為第三重難。雖然我國法律法規(guī)中已經(jīng)確定了及時通知義務,但并沒有具體規(guī)定如果在司法執(zhí)法過程中,辦案機關未告知當事人相關權(quán)利,是否屬于程序違法,如何進行救濟等。[7]
(二)破局:加強國內(nèi)立法,實現(xiàn)權(quán)利源頭保護
軟法是國際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維約》以及《規(guī)定》等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屬于軟法范疇[8],軟法是原則上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有實際效力的行為規(guī)則[9]。但由于違反領事通知義務的國內(nèi)救濟不盡如人意,這促使從源頭保護的理念逐漸獲得認可。軟法硬化,提高軟法硬度的國內(nèi)創(chuàng)新立法的種子不斷萌芽,甚至一些國家通過修訂國內(nèi)立法來履行國際義務或警察規(guī)則,要求自拘留外國公民時就告知其所享有的領事通知權(quán),防止權(quán)利之侵犯,消弭救濟之不足。[10]
根據(jù)對等互惠原則,我國關于領事通知權(quán)的國內(nèi)立法和實踐也影響我國海外公民的利益保護。權(quán)利和義務相一致,如果我國要在接受國運用領事通知權(quán)保護我國海外公民的利益,我國就必須相應、對等地承擔保護該國國民領事通知權(quán)的義務。因此利用國內(nèi)立法,提高國際軟法硬度是強化權(quán)利保護的重要途徑。
1.建議在現(xiàn)有國內(nèi)立法中明確領事通知權(quán)的法律地位,增加對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外國人領事通知權(quán)保護的規(guī)定。一是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或制定司法解釋,賦予檢察機關對領事通知的監(jiān)督權(quán),對于未履行相關義務的辦案機關通過制發(fā)檢察建議的形式予以督促。二是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時,詢問當事人是否已經(jīng)被告知其所享有的領事通知權(quán),并得到相應的幫助。
2.完善《規(guī)定》等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雖然《若干規(guī)定》的印發(fā)對于檢察機關如何規(guī)范履行領事通知義務具有指導意義,但隨著國家立法體制不斷完善、立法能力和立法質(zhì)量的不斷提高、法律和司法實踐的不斷深化和演變,《規(guī)定》等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已經(jīng)“不合時宜”,適時修改完善相關規(guī)范性文件應該提上議程。
3.制定執(zhí)法司法手冊,規(guī)范執(zhí)法司法的標準和程序。制定專門服務于執(zhí)法司法人員的執(zhí)法手冊,明確操作程序、指引和規(guī)則,提高執(zhí)法司法規(guī)范化建設,保護外國國民在我國享有的領事通知權(quán)。
(三)新局:擴大雙邊條約的締結(jié),創(chuàng)造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
隨著國際社會人權(quán)保護理念的不斷發(fā)展,正當程序、無罪推定、辯護權(quán)保障等刑事司法原則已為大多數(shù)國家所接受和采納,領事通知作為保護派遣國犯罪嫌疑人人權(quán)的有效措施,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重視,《維約》第36條第1款第2項下的接受國領事通知義務被進一步強化。“強制性通知”的理念和國際司法實踐逐漸產(chǎn)生,許多國家通過締結(jié)雙邊領事條約(協(xié)定),明確將《維約》36條所確立的領事通知權(quán)從“請求下的義務”變成“強制通知義務”,從“請求通知”變?yōu)椤白詣油ㄖ保粗灰汕矅鴩裨诮邮車硟?nèi)被采取強制措施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無論該國民是否提出通知其國籍國使領館的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就有義務盡快通知派遣國領館。[11]截止到2018年4月,在我國對外簽訂或重新簽訂的雙邊領事條約(協(xié)定)中,共有48個國家規(guī)定了“強制領事通知權(quán)”。[12]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國內(nèi)自貿(mào)區(qū)建設不斷深入和廣泛開展,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海外公民數(shù)量將日益增多。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情況復雜,我國海外公民安全面臨不同程度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13]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護我國海外公民權(quán)利,是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保護我國海外公民利益可以有多種選擇方式,雙邊條約是保護我國海外利益的一種有效、合法、可行的方式。[14]一是履行條約是締約國的義務,根據(jù)《維約》第27條規(guī)定,締約國不得以其國內(nèi)法包括憲法的規(guī)定為由不履行條約義務。二是領事通知不僅是國際公約中規(guī)定的義務,從對等互惠原則看更體現(xiàn)了國家間關系,國家關系更適宜用雙邊條約來調(diào)整。雙邊條約有利于將權(quán)利和義務固化,利益和訴求細化,法律秩序具化,從而更好地保障雙方的利益。三是條約是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國家之間簽訂的協(xié)議,雙邊條約能夠為我國海外公民領事通知權(quán)在內(nèi)的利益保護提供比較穩(wěn)定的預期。即使發(fā)生政府變更,面臨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也能夠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爭端提供辯護根據(jù)。四是有利于我國參與乃至構(gòu)建自身及國際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范。“一帶一路”等倡議的提出,表明我國從被動接受和遵守國際社會規(guī)則逐漸向主動探索構(gòu)建國際社會發(fā)展新秩序不斷演變,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也在不斷變化。[15]因此,無論從國家戰(zhàn)略角度還是我國海外公民利益保護角度看,雙邊條約均應成為優(yōu)先選擇方式。
但目前國家通過締結(jié)雙邊條約的方式保護我國海外公民利益的實踐還有很大發(fā)展空間。例如,據(jù)統(tǒng)計,目前我國和外國共簽訂44個雙邊領事條約(協(xié)定),然而44個雙邊領事條約(協(xié)定)中除2014年7月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領事協(xié)定》外,其余都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簽訂的[16],無法反映“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和簽約國情況的變化,也無法反映國際法的變化。
鑒于目前利用雙邊條約保護海外利益上的缺陷,我國應擴展雙邊條約的締結(jié),讓雙邊條約成為保護我國公民走出海外的堅實的法律基礎和支撐,最大化保護我國海外公民利益。
[1] 參見夏莉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發(fā)達國家領事保護機制變化研究——兼論對中國的啟示》,外交學院2008年博士論文。
[2] 也有國家認為領事通知權(quán)是強制性權(quán)利,不需要外國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請求,有關當局應迅即通知派遣國領館。
[3] 我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簽訂的相關領事條約規(guī)定3日內(nèi)通知派遣國使領館,與俄羅斯簽訂的領事條約規(guī)定領事通知時間是3個工作日內(nèi)。
[4]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94條。
[5] 參見謝海霞:《領事保護制度的新發(fā)展》,《國際法學刊》2020年第1期。
[6] 參見王秀梅:《〈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36條第1款的解釋與適用——試析國際法院布雷德案、拉格朗德案、阿維納案》,《法學雜志》2009年第12期。
[7] 參見王秀梅:《領事通知問題論要》,《法律科學》2009年第6期。
[8] 參見姜明安:《軟法的興起與軟法之治》,《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
[9] 參見[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張文顯、鄭成良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10] 參見謝海霞:《領事保護制度的新發(fā)展》,《國際法學刊》2020年第1期。
[11] 參見顏梅林、陳亮:《論國際法人本化趨向下領事通知權(quán)的性質(zhì)與救濟》,《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12] 參見我國外交部領事司2017年4月印發(fā)的《涉外案件處理法律法規(guī)須知》,第26頁。
[13] 如緬甸政治轉(zhuǎn)型導致中國企業(yè)在緬投資被停止或被取消。由于我國海外華人很多在外投資,企業(yè)投資引發(fā)的問題有可能導致刑事案件的發(fā)生。
[14] 參見李鳴:《雙邊條約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性》,2019年12月6日在第四屆“法治河南青年論壇”主題報告。轉(zhuǎn)引自周曉偉:《李鳴:雙邊條約更有利于保障我國海外利益》,《公民與法(綜合版)》,2019年第12期。
[15] 參見楊思靈:《“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沿線國家關系治理及挑戰(zhàn)》,《南亞研究》2015年第2期。
[16] 參見中國與外國締結(jié)領事條約(協(xié)定)一覽表,中國領事服務網(wǎng):http://cs.mfa.gov.cn/zlbg/tyxy_660627/t1131869.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0年11月14日。
137450118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