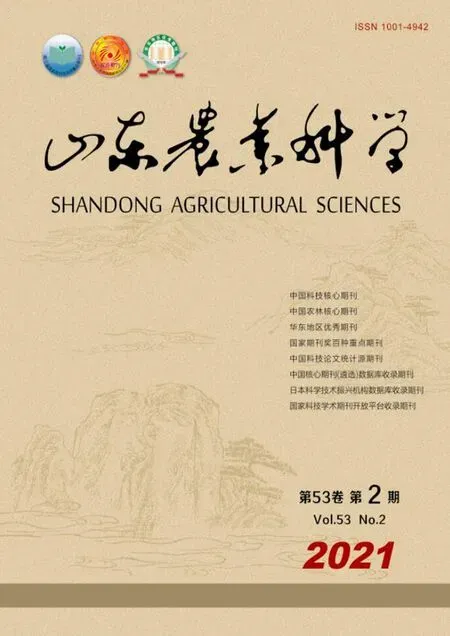基于CNKI和WOS的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知識圖譜研究
趙光明,王萍
(曲阜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山東 日照 276826)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人類活動和生態過程變得更為復雜,多尺度生態風險的出現使得和諧人地關系遭受破壞[1]。土地利用格局、深度和強度不斷變化,土地利用類型趨于多樣化[2,3],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大氣和水體污染、土壤沙化、物種滅絕等地域性和累積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4]。生態學的研究已從二元生態鏈(生物—環境)轉向三元生態環(生物—環境—人類)和多元生態網(環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5],土地作為一個社會自然綜合體在多元生態網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土地利用是指人類為獲取一定的經濟、環境或政治福利(利益),對土地進行保護、改造并憑借土地的某些屬性進行生產性或非生產性活動的方式、過程及結果[6];既是人與土地耦合關系集成的動態系統,又是人類開發、利用、改造自然環境最直觀的表現形式之一[7]。生態風險和生態風險評價的內涵不斷延伸、轉化[8,9],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已成為近年來生態學等領域的熱點話題之一。1992 年美國國家環保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將生態風險評價(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定義為“評估暴露于一種或多種壓力因子后,可能出現或正在出現的負生態效應的可能性過程”[10]。生態風險評價為風險管理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的同時,也為土地利用定量評估帶來了新思路[11,12]。
目前國內外對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生態風險評價部分,有兩種主要模式:一是基于源-匯景觀理論的傳統風險,合理設計源-匯景觀空間格局,促進非點源污染物質的再分配,Walker[13]、王金亮[14]、許學工[15]等做了相關研究;二是從景觀生態學的視角入手,構建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建立景觀生態風險評價模型與體系,揭示景觀生態風險的時空演變規律。相對前一種模式,該模式不僅重視對區域生態風險的定量評價,還側重于分析風險時空分異特征以及特定空間格局對生態功能、過程的風險表達[16]。
國內外針對具體的研究區域已有不少關于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成果,是時機采用文獻計量的方法對土地利用與生態風險這個交叉研究領域進行定量化評析。本文基于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和WO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借助CiteSpace引文分析軟件,對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從文獻數量年度分布、關鍵詞頻次、聚類分析等方面探究該領域的研究主題變化和前沿發展,明確研究熱點、知識演變、演化路徑和未來趨勢,以期對土地生態領域及其相關研究提供借鑒參考。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為客觀展示國內外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前沿,數據樣本分別取自于中國知網知識網絡平臺CNKI和美國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開發的科研信息檢索平臺WOS數據庫中的核心合集(包括SCI-EXPANDED、SSCI、CCR-EXPANDED和IC)。時間跨度設為2001—2018年,并根據需要去除了重復、偏離主題的文獻。
CiteSpace是由美國德雷塞爾大學計算機與情報學終身教授陳超美博士使用Java開發的一款用于科學計量分析、挖掘潛在知識的引文可視化分析軟件[17],其主要依靠繪制出的科學知識圖譜,并結合文獻計量法通過文獻數量分布、關鍵詞頻次等信息可視化來展現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知識演變、發展脈絡和研究熱點。
2 可視化分析
2.1 文獻數量年度分布
在CNKI數據庫中選擇高級檢索,檢索主題為“土地利用”并“生態風險”;在WOS數據庫中選擇基礎檢索,檢索主題設為“land use AND ecological risk”或“land use AND ecological risks”,分別獲得有效中文文獻720篇和外文文獻1883篇,并進行文獻數量年度分布統計(圖1)。2001—2004年國內文獻數量增長緩慢,學術界開始關注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2005年文獻數量增加到10篇以上;此后13年間,僅2008、2010年文獻數量略有下降,整體上一直處于平穩增長狀態,表明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持續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但重視程度不夠,需要進一步開展突破性相關研究。相較之下,從2006年起,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一直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年均發文量高達134.5篇,基本上呈線性增長的態勢,表明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土地利用生態風險已成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和全球變化研究的熱點話題之一。同時表明,國際研究仍是該領域的“領頭羊”,中國不是主導研究力量,但已是主要研究力量。由于學校購買的WOS數據庫中核心合集僅有2006年至今的文獻,國際文獻數量存在一定缺陷。
2.2 研究機構與作者
從表1看出,國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研究機構分布相對分散,發表論文較多的機構為中國科學院大學、新疆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大部分作者的研究成果相差不大,發表論文最多的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張永福(7篇)。排名前10的研究機構中有4所師范類院校,接近一半的貢獻力量來自于此,這與國內大多數師范類院校開設的相關專業、方向(土地資源管理、公共管理、地圖學和地理信息系統等)和碩、博士點關系密切。

表1 國內排名前10研究機構與作者頻次統計
從表2看出,相較國內,國際研究同樣沒有高產作者,但值得關注的是, Univ.Chinese Acad.Sci.(中國科學院大學)是發表論文最多的國際研究機構,發表172篇論文,占總發文量的45.7%,該研究機構可視為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的核心力量。其次是發表33篇論文的US Forest Serv.(美國森林服務公司),占比8.7%,排在第3位的是發表28篇論文的Beijing Normal Univ.(北京師范大學),占比7.4%。中國科學院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的發文量之和占國際高頻研究機構總發文量的一半以上;國際排名前10研究作者分布中,中國作者有7人,發表論文總計41篇,占國際高頻研究作者總發文量的69.5%。由此可見,國內土地生態領域的科研成果大量外流已成為普遍現象[18],中國學者才是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真正的“主力軍”。

表2 國際排名前10研究機構與作者頻次統計
2.3 關鍵詞頻次
關鍵詞是對論文的高度概括和總結,聚焦了研究者關注的核心,對論文關鍵詞的提煉和系統歸類,通常能夠真實地反映某個研究領域和對象的研究價值[19]。高頻關鍵詞的引入,更是成為辨識該領域發展方向和前沿熱點的重要參考依據。關鍵詞共現分析相比文獻的共被引和耦合分析,其得到的結果更加直觀明了,即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共現分析的結果,對所研究領域的主題進行分析[17]。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能反映其在整個關鍵詞共現網絡中的重要程度,代表一定時期內該領域核心的研究主題[20,21]。分別選取國內外研究中前30個高頻關鍵詞,有助于反映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發展方向和前沿(表3)。
國內研究中關鍵詞主要分為四類:①“生態風險評價(中心性高達0.58)”方面的關鍵詞,頻次之和共占所有關鍵詞頻次總和的25.5%,主要含有“生態風險評價”“風險評價”“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等關鍵詞,代表了國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熱點與前沿。②土地利用及景觀格局變化方面的關鍵詞,頻次占31.5%,包括“景觀格局”“土地利用變化”“土地利用/覆被變化”“土地利用方式”“空間分析”“景觀指數”“空間自相關”和“時空分異”等關鍵詞,如田鵬[22]、許鳳嬌[23]和汪翡翠[24]等利用多期土地利用數據研究生態風險時空特征變化,程文仕等[25]基于生態風險的空間異質性研究土地整治優先序。③“生態安全(中心性高達0.52)”方面的關鍵詞,頻次占20.3%,圍繞 “生態安全”“重金屬”“土壤”“土壤重金屬”“多環芳烴”和“污泥”等,多從生態毒理學的角度針對土地利用進行生態健康評價,評定人類健康的潛在危害[26]。④“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技術方面的關鍵詞,頻次占8.2%,注重各類信息技術與數學方法相結合,剖析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時空變化特征。

表3 高頻關鍵詞統計
國外研究關鍵詞頻次分析:①“climate change(氣候變化)”“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management(管理)”和“conservation(保護)”等關鍵詞頻次均超過160,共占關鍵詞頻次總和的30.3%,反映了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熱點和前沿。②中心性大于0.10的關鍵詞,有 “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landscape(景觀)”“heavy metal(重金屬)”“pattern(模式)”“vegetation(植被)”“extinction risk(滅絕風險)”和“adaptation(適應)”,是目前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核心和熱點關注。③“ecosystem(生態系統)”相關研究的高頻關鍵詞較多,且頻次均高于50,主要有“ecolsystem service(生態系統服務)”“vulnerability(脆弱性)”“adaptation(適應)”和“resilience(恢復力)”等,表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及生態系統脆弱性、適應性、恢復力等研究是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④風險源—風險受體方面研究的高頻關鍵詞,包括“heavy metal(重金屬)”“forest(森林)”“soil(土壤)”“ecosystem(生態系統)”和“sediment(沉積物)”等,頻次均介于60~100左右。由此可見,重金屬、沉積物、殺蟲劑等污染物是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罪魁禍首,危害涉及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農田、水域、森林等)。⑤“China(中國)”和“United States(美國)”的頻次同樣很高,說明中國和美國已成為研究者選取研究對象和研究區域的熱點關注,研究者多以此開展相關實驗研究等實證分析。⑥“model(模型)”“system(系統)”和“pattern(模式)”,共占關鍵詞總頻次的9.1%,說明該領域多進行定量化的模型研究和模擬研究。此外,“agricultural soil(農業土壤)” “urban(城市)”“social ecosystem(社會生態系統)”和“surface soil(表層土壤)”等關鍵詞同樣頻繁出現,未來的研究重心或將轉向農業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城市生態系統及復合生態系統的生態風險評價、生態管理和驅動機制等方面[27,28]。
2.4 聚類分析
CiteSpace軟件中的聚類分析是指在關鍵詞共現網絡的基礎上,展示共現關鍵詞之間的親疏關系,并依據它們的親疏關系程度進行聚類[29]。根據表3高頻關鍵詞統計和圖2所示的聚類情況,國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主題可劃分為兩大聚類集群(圖2)。
集群1由“#1風險評價”“#3生態風險評價”“#4生態風險”“#8地理信息系統”和“#9風險管理”構成。國內土地利用方面的生態風險評價研究較晚,從健康風險過渡到環境風險再向生態風險轉移經歷了近20年的漫長演變歷程[30],目前尤以土地利用變化生態風險評價研究居多。生態風險研究能夠為風險管理提供理論依據和技術支持,同時伴隨GIS和RS等新技術手段的開發與應用,結合土地統計分析和生態風險指數等方法研究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相關文獻不斷出現,其主要通過構建CLUE-S模型、PSR模型等關系模型對地類轉變、土地損毀和土壤侵蝕等引起的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進行評價,為區域生態風險預測及管控提供決策支持,進而實現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與優化配置、生態系統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的整體統一。
集群2由“#0低丘緩坡”“#2紅寺堡區”、“#5土地利用/覆被變化”“#6土地利用變化”和“#7城鎮化”構成。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土地利用生態風險方面的問題層出不窮,人地關系矛盾日益突出[31]。因此,從縣域、市域和省域等不同尺度出發,基于遙感影像數據研究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或土地利用變化生態風險的實證案例研究越來越多,其主要對景觀結構、土地用途、植被覆蓋率等地理空間信息進行分析處理,探索土地利用生態風險及其時空分異和空間沖突,如李月月[32]、何莎莎[33]等分別以長汀縣和揚州市為研究區進行的相關研究。而低丘緩坡作為土地綜合利用的后備開發資源,廣布于我國東南沿海和武夷山區,已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空間擴展的重要選擇[33],未來可能會在農業農村發展、土地用途管制和國土空間規劃中扮演重要角色[34]。同時,作為生態移民安置區的典型代表,紅寺堡區是近5年來國內學者關注的典型研究區,生態移民對遷入區土地利用的深廣度、類型、景觀破碎度、異質性和多樣性等的影響逐漸得到重視[35,36]。
國際研究劃分為三個聚類集群(圖2):
集群1-風險源,由“#1 climate change(氣候變化)”“#5 phoshorus(磷)”和“#7 surface sediment(表層沉積物)”構成。氣候變化是全球變化的最大誘因之一,同時也給土地利用帶來了巨大的生態挑戰。氣候變化對土地利用的直接影響一般表現為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對土地的影響,如暴雨洪水對土地的危害(以農田為例):土壤流失加劇、毒害物質堆積、土壤結構破壞等;間接影響表現為氣候變化迫使農田作物的播種期、收獲期和全生育期發生變化以及種植界限的變更,從而影響以土地為載體的生態系統內生物間及其與環境間“流”的傳遞(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37]。而氮、磷循環是從微觀尺度研究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重要切入點,以磷、氮等為代表的營養元素含量超標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風險因子[38],氮磷污染不僅造成湖泊、水庫等水體的水質變差、魚蝦及其他生物大量死亡,還會脅迫小區域范圍內物種多樣性空間格局變異和生態系統多樣性“換血”。另外,針對表層沉積物中的重金屬元素(鉛、鎘、汞、砷、鉻等)和有機污染物(多環芳烴、鹵代烴等)的空間分布、生態風險評價及其來源等方面的研究,是近年來江河、湖泊和海域表層沉積物研究的重點。無機污染物中重金屬所占比重較大,其在生物體內累積、沉淀后的危害相當大。因此,預防重金屬中毒需從源頭抓起。將空氣、泥土、食物和水中重金屬含量控制在安全范圍內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生態安全問題現已上升到國家高度,如習近平于2014年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39]。
集群2-風險受體,由“#2 home range(家域)”“#4 vegetation(植被)”“#8 transmission(傳遞)”和“#1 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構成。單風險受體向多風險受體和復合風險受體的轉變過程與城市化發展的演化過程相契合,風險受體的選擇已從個體、群落、植被、家域、保護區等小尺度擴展到森林、河流、景觀、生態系統等中、大尺度,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方向也從景觀生態風險研究發展到區域生態風險研究,土地利用和景觀格局動態變化對自然植被分布、動物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將更加明顯,生態系統中生物和無機環境的耦合關系也會更加復雜[40]。家域中動物的生態需求、活動路線和生境選擇對生態過程的影響為土地利用和森林景觀的生態風險研究提供新的視角[41]。植被類型在土壤形成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改變土壤物理結構、化學成分等)。一方面,植物根系可以固土鎖水、提高土壤抗侵蝕力、優化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森林砍伐、火災對植被蓋度、覆蓋率產生不同程度的生態效應,成為定量研究森林生態系統覆被演替的重要切入點。
集群3-風險評價,由“#0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生物多樣性保護)”“#3 North America(北美)”“#6 forest management(森林管理)”“#9 remediation(修復)”和“#10 England(英國)”構成。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德國、加拿大等國都對土地利用生態風險評價的框架和指標體系做過相關研究,基本路線為結合內梅羅指數法、相對風險模型(RRM)、景觀格局指數等風險評價方法,進行問題表述、問題分析、風險表征[42,43],美國和英國已成為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相關領域重點關注的研究區所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有利于全球土地生態的平衡與可持續,已發展為當今國際學術界重點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對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的保護研究已得到世界各國的積極響應。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養水源、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一旦遭受破壞將會波及整個地球生態系統。森林管理一直處于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相關領域的研究前沿,森林生態風險研究正逐漸成為森林范疇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熱點前沿。而當土地利用生態風險出現或即將達到臨界值時,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減少風險損失。生態修復方式與技術(生物、物理與化學修復及工程技術)的快速更新與推廣,使土地短時間內恢復其原有的生態價值變為可能。

圖2 關鍵詞共現網絡聚類
2.5 時區圖
時區圖是從時間維度上研究文獻關鍵詞年度分布的一種表現方式,側重于展示某年首次出現的關鍵詞,有助于某領域的演進路徑研究,以后再次出現將在之前年度區間進行累加。如圖3所示,國內外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主題演進分為三個階段:
起步探索階段(2006年之前),國內關注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思想來源與理論方法,從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和土地科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界定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研究范疇、方向,可稱為基礎層;國外主要涉及風險源-風險受體[如“community(群落)”“forest(森林)”“habitat(生境)”和“landscape(景觀)”等]方面的土地利用生態風險評價,強調自然風險源對生態系統管理、恢復及其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影響機制研究。
穩步發展階段(2007—2013年),國內出現了大量實證研究,涉及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依托條件(“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生態系統服務”)、技術層(“地理信息系統”“遙感”)、理論層(“模型”與“指標體系”,“風險評價”與“風險管理”);國外研究注重化學污染物對生態風險的危害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包括“water quality(水質)”“management(管理)”“heavy metal(重金屬)”和“pollution(污染)”等問題,圍繞土地-生態系統的研究:“resilience(恢復力)”“vulnerability(脆弱性)”“adaptation(適應)”及其對策(“conservation(保護)”、“management(管理)”、“restoration(修復)”),這與關鍵詞頻次分析的結果基本一致。
快速發展階段(2014—2018年),國內開始關注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風險源(“多環芳烴”等)、多尺度的生態風險(“景觀生態風險”等)及“評價模型”和空間分析(“空間沖突”等)等多個方面。國際研究內容不斷細化,如風險源從“heavy metal(重金屬)”到“trace metal(痕量金屬)”。從農業、社會、自然及復合生態系統視角下探索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spatial distribution(空間分布)”及“desertification(荒漠化)”“environment change(環境變化)”和 “ecological impact(生態沖擊)”等問題,“health risk(健康風險)”研究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3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系統梳理了CNKI和WOS數據庫中2001—2018年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有關文獻,針對生成的知識圖譜及相關數據進行分析,探索出該領域的知識演變、研究熱點和演進趨勢。結果表明:①國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領域的研究雖已初具規模,但整體發展較為緩慢,而國際研究日臻成熟。②國內的研究熱點為“生態風險評價”“景觀格局”“土地利用變化”和“生態安全”等,國際的研究熱點為 “climate change(氣候變化)”“management(管理)”“conservation(保護)”“biodiversity(生物多樣性)”和“land use change(土地利用變化)”等。③國內外研究各自形成了主題關聯的研究集群,國內分為區域性研究和技術性研究兩大集群,國外分為風險源、風險受體和風險評價三大集群。④國內外的研究發展具有相似的階段性特征,皆可分為2006年之前、2007—2013年、2014—2018年三個階段,國外研究相對發展較早、內容更為深入。
從文獻數量看,近年來國際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已步入發展的快車道,而國內還停留在平穩增長階段,未來期待更多學者和研究群體的投入關注。大量科技成果外流已成為普遍現象,不利于國內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研究的長期發展。從關鍵詞頻次看,國內外皆重視景觀生態風險研究,主要從landscape(景觀)尺度研究土地利用變化、景觀格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過程,通過構建土地利用生態風險指數、評價模型和評價體系進行生態風險分等定級,解析多源風險的綜合生態空間表征,進而提出土地可持續利用和降低生態風險的對策建議。結合關鍵詞頻次和聚類集群看,重金屬與多環芳烴相關研究是國內外的共同關注點。國內更注重土地利用變化對人地關系的影響,而國際側重于從風險源-風險受體方面對生態風險進行評價。
本研究文獻數量有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主題的客觀性,但也致使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關鍵詞選取上按照國內、國際文獻中關鍵詞頻次的前30位,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低頻關鍵詞不重要,它們成為未來的研究熱點亦有可能。今后應多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耦合研究,多視角、多尺度、多層次的共同考量,研究對象和主題緊密契合國家發展戰略需求,提出適宜的風險響應策略與制度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