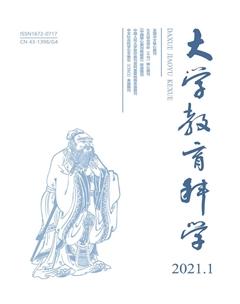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背景下人文學(xué)科的生長困局分析
張慶玲
摘要: 人文學(xué)科是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要元素。從已公布的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名單來看,人文學(xué)科所占比例偏低、發(fā)展空間不足且呈現(xiàn)出鮮明的工程化、國際化、數(shù)據(jù)化思維導(dǎo)向。究其根源主要是:學(xué)科評估的計算主義哲學(xué)導(dǎo)向、技治主義思維對人文學(xué)科的鉗制、資本邏輯對人文學(xué)科的束縛、國際化偏好對人文學(xué)科的誘導(dǎo)。對此,亟需通過學(xué)科交叉實現(xiàn)顛覆式創(chuàng)新,找準人文學(xué)科的“內(nèi)心視點”;強化學(xué)科主體意識,重建中國特色“國家+”人文學(xué)科知識體系;走出指標(biāo)“陷阱”,構(gòu)建適切的人文學(xué)科評價體系;超越數(shù)字人文,找準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xué)科的主體性優(yōu)勢。
關(guān)鍵詞:世界一流學(xué)科;人文學(xué)科;國際化;學(xué)科評估;學(xué)科交叉;數(shù)字人文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1)01-0044-0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教育學(xué))重大招標(biāo)課題“‘雙一流建設(shè)背景下高校學(xué)科調(diào)整與建設(shè)研究”(VIA170003)。
人文學(xué)科是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要元素,是人類知識譜系的基本構(gòu)成要件,也曾被公認為人類最有價值的知識。人文學(xué)科的發(fā)展態(tài)勢直接決定了大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總體水平與“雙一流”建設(shè)的預(yù)期成效,是高等教育內(nèi)涵式發(fā)展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從已公布的“雙一流”建設(shè)高校和建設(shè)學(xué)科名單來看,“雙一流”建設(shè)高校更傾向于理工類高校和理工實力較強的綜合性高校;從學(xué)科布局來看,“雙一流”建設(shè)學(xué)科傾向于國際化程度更高的理工農(nóng)醫(yī)等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人文學(xué)科處于“無用知識”的尷尬境地;從學(xué)科建設(shè)思維來看,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工程化思維建設(shè)人文學(xué)科,人文學(xué)科面臨被抽象化、算法化、符號化的生存危機;從學(xué)科屬性來看,“雙一流”建設(shè)傾向于國際化通用學(xué)科,中國特色本土學(xué)科嚴重不足;從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實踐來看,這種基于科學(xué)主義的標(biāo)準話語體系、學(xué)術(shù)模型和科學(xué)范式不利于人文學(xué)科的自然生長,破壞了學(xué)科生態(tài)平衡,違背了高等教育內(nèi)涵式發(fā)展理念。
在這個數(shù)據(jù)化的計量主義時代,人文學(xué)科“內(nèi)卷”于“技術(shù)化”“標(biāo)準化”和“程式化”的“科學(xué)管理叢林”,仰賴的是“飽和的自我”與“思想的懸置”,陷入了被估算的風(fēng)險。正如羅薩所言,“如今的科學(xué)領(lǐng)域,不論在人文科學(xué)還是社會科學(xué),目前的學(xué)術(shù)論述很難發(fā)展出更好的論點邏輯,很難檢視哈貝馬斯所謂的有效性宣稱,也幾乎沒辦法進行集體的思量,因為科研人員已經(jīng)都在失控地、狂熱地追求更多的出版、會議、研究經(jīng)費。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成功已經(jīng)不在于或幾乎不在于有沒有提出什么強而有力的論點,而是只去看論文發(fā)表量的多寡而已”[1]。毫無疑問,人文學(xué)科映照著一所大學(xué)的歷史底蘊和人文高度,人文學(xué)科的缺席無異于是對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釜底抽薪。一流大學(xué)不僅要培養(yǎng)“國之大器”的工匠人、科學(xué)家,還要培養(yǎng)“國之命脈”的哲學(xué)家、思想家;不僅要推進科技創(chuàng)新,還要實現(xiàn)知識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思想創(chuàng)新。
一、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人文學(xué)科的生長困局
從教育的歷史來看,人文學(xué)科曾是人類最有價值的知識,直到今天,人文學(xué)科在思想性和創(chuàng)造性方面依然是最有價值的學(xué)科,專注于人類靈魂的“喚醒”。科學(xué)旨在解決事實判斷,通過探究自然規(guī)律來描述和分析客觀世界的原貌,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科學(xué)的原理或定律,提高人類的生活品質(zhì)。人文學(xué)科研究指向的是一種意義結(jié)構(gòu),重在價值判斷,通過解釋和理解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探討生命的價值、行為、目的及其意義。人文學(xué)科表達的是人類社會的價值內(nèi)核,關(guān)注的是人的思維和精神產(chǎn)物,具有較強的地域文化脈絡(luò)性。
(一)人文學(xué)科知識譜系的流變
人類知識論經(jīng)歷了一個譜系性的生產(chǎn)過程,知識最初的分門別類與人類早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guān),知識隨著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遷而呈現(xiàn)不同的知識生產(chǎn)方式與知識分類方式,某些知識之所以被保存并傳承下去,并不是因為這類知識有多么高深,而是與人類的某種需求相契合。從中世紀大學(xué)產(chǎn)生到柏林大學(xué)建立之前,人文學(xué)科構(gòu)成了大學(xué)的靈魂,人文知識一直是最有價值的知識,大學(xué)以古典教學(xué)為主,既不提供實用的科學(xué)研究,也不直接為社會服務(wù),目的在于培養(yǎng)踐行社會品格的德性人。在古希臘以及此后漫長歷史進程中,知識都是有品格的,沒有品格的知識是不可能存續(xù)的。17世紀之后,有品格的知識觀逐漸讓位于以技術(shù)理性為架構(gòu)的科學(xué)主義知識觀,基于常識的價值判斷轉(zhuǎn)向了基于數(shù)學(xué)模型、符號話語的事實判斷。以學(xué)科設(shè)置為例,19世紀之前,西方大學(xué)主要設(shè)置了神學(xué)、哲學(xué)、法學(xué)、醫(yī)學(xué)等學(xué)科,致力于培養(yǎng)遵守道德約束和高潔品格的社會精英以及通曉多學(xué)科知識的思想家、哲學(xué)家。19世紀以后,尤其是德國柏林大學(xué)將科學(xué)研究確立為大學(xué)使命后,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社會學(xué)科取代人文學(xué)科成為大學(xué)課程設(shè)置中的主導(dǎo)力量,物理學(xué)、化學(xué)、生物學(xué)、解剖學(xué)等自然科學(xué)逐漸成為大學(xué)的核心課程,并在國家力量的助推下,受到師生的追捧。于是,知識不再是美德,學(xué)術(shù)開始成為一種職業(yè),專家知識與世俗權(quán)力日漸合流,知識成為權(quán)力的代名詞。自然科學(xué)開始以“科學(xué)”的名義在大學(xué)的課程設(shè)置中迅速蔓延,并完成了學(xué)科制度化,占據(jù)了越來越多的課程席位,導(dǎo)致人文學(xué)科越來越“科學(xué)化”、理性化、機械化,否則就可能因不合乎科學(xué)范式要求而失去生存空間。在系科主義支配下,大學(xué)逐漸知性化,大學(xué)教授從公共知識分子向政府“發(fā)言人”、企業(yè)“合伙人”轉(zhuǎn)型,權(quán)力與金錢開始慢慢滲入大學(xué),人類意義上的普遍關(guān)懷和道德合法性被棄之如敝屣。同時,學(xué)術(shù)成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大學(xué)籠罩在資本的控制下,并不斷地向社會輸送馴化的“資本人”,充滿人文氣息的德性大學(xué)逐漸被功能性的知性大學(xué)所取代,最終,大學(xué)成為了帕森斯所說的“知性復(fù)合體”,“它看不到罪惡,聽不到罪惡,聞不到罪惡,不知道罪惡”[2]。
今天,在技術(shù)革命和資本革命的侵襲下,大學(xué)在走向國際化、全球化的同時,也越來越商業(yè)化、資本化、政治化,大學(xué)里奉行的企業(yè)化管理模式,與人文學(xué)科倡導(dǎo)的學(xué)術(shù)自主格格不入,而人文學(xué)科如果不能回答社會提出的問題,不能用多學(xué)科的觀點來理解當(dāng)下數(shù)字化或人工智能的技術(shù)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化,將逐漸在大學(xué)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人文學(xué)科為了證明自己的功用,部分放棄了為知識而知識的自我論證,開始尋求自然科學(xué)或社會科學(xué)的方法論,向商業(yè)靠攏,向技術(shù)問道,尋求政治的庇護。如今,無論是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還是人文學(xué)科都在極力地向“一流”靠攏,似乎有了“一流”的“符號”王牌,就可以坐擁“學(xué)科巔峰”。雷丁斯認為,所謂“一流大學(xué)是一個大學(xué)理念的幻影”[3],是一個貧乏蒼白的、沒有內(nèi)在品質(zhì)的空洞目標(biāo),最適合技術(shù)官僚根據(jù)計算主義模式來加以管理。在“一流”的驅(qū)動下,衡量一個學(xué)者是否優(yōu)秀的標(biāo)準,主要看他的論文發(fā)表量、課題申請數(shù)、文獻引用率等量化的外顯指標(biāo),而不是某種學(xué)術(shù)的內(nèi)在標(biāo)準。“一流學(xué)科”是科學(xué)主義邏輯下的產(chǎn)物,自它產(chǎn)生以后,就成為衡量所有學(xué)科的通用標(biāo)準,人文學(xué)科作為一種以人的精神性、思想性和價值判斷為指向的意義結(jié)構(gòu)也加入這場“他人場域”的“學(xué)科之爭”,必然陷入科學(xué)主義的“陷阱”。吊詭的是,“我們今天接受的知識體系基本來自西方,尚未形成中國本土化的知識體系,實際上中國的人文學(xué)科從未得到過充分發(fā)展,我們的知識生產(chǎn)者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自己”[4]。今天,中國的不少科技成果已經(jīng)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在人文學(xué)科領(lǐng)域,還是拿不出一套人文學(xué)者自創(chuàng)的理論——我們的人文學(xué)科與西方存在巨大的落差,這既是人文學(xué)科的危機,也是中國文化的危機。
(二)“雙一流”建設(shè)中人文學(xué)科的生存現(xiàn)狀
從“雙一流”建設(shè)高校和建設(shè)學(xué)科名單公布結(jié)果來看,共計42所一流大學(xué)建設(shè)高校和95所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高校,共列出465個一流建設(shè)學(xué)科。以人文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的分類框架來看,各類學(xué)科的分布比例如下,其中人文科學(xué)有52個(哲學(xué)門類5個,教育學(xué)門類6個,文學(xué)門類19個,歷史學(xué)門類9個,藝術(shù)學(xué)門類13個),占比為11.20%;社會學(xué)科有55個(經(jīng)濟學(xué)門類11個,法學(xué)門類23個,管理學(xué)門類21個),占比為11.80%;自然科學(xué)有358個(理學(xué)門類104個,工學(xué)門類188個,農(nóng)學(xué)門類24個,醫(yī)學(xué)門類42個),占比達77%。同時,一流學(xué)科比例之間存在一定的校際差異,如北京大學(xué)有10個人文學(xué)科,8個社會學(xué)科,23個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以文科為主的中國人民大學(xué)有3個人文學(xué)科,10個社會學(xué)科,1個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理工類大學(xué)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7個一流學(xué)科均是理工類學(xué)科;綜合類高校如浙江大學(xué)共18個一流學(xué)科全是理工類學(xué)科,廈門大學(xué)共5個一流學(xué)科也均為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可見,理工類、綜合類高校在選擇申報一流學(xué)科時,都是傾向于優(yōu)先考慮理工類學(xué)科。根據(jù)2018年《學(xué)位授予和人才培養(yǎng)學(xué)科目錄》,去掉10個軍事學(xué)科,我國共有101個一級學(xué)科,其中人文學(xué)科15個(哲學(xué)1個,教育學(xué)3個,文學(xué)3個,歷史學(xué)3個,藝術(shù)類5個),社會學(xué)科13個(經(jīng)濟學(xué)2個,法學(xué)6個,管理學(xué)5個),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73個(理工類14個,工學(xué)類39個,農(nóng)學(xué)類9個,醫(yī)學(xué)類11個),人文學(xué)科占學(xué)科總數(shù)(除軍事學(xué)以外)的14.90%,社會學(xué)科占比12.90%,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占比72.20%。由此可見,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人文學(xué)科和社會學(xué)科占比均低于“學(xué)科目錄”中其相應(yīng)學(xué)科所占的比例,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的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比例較高于其在“學(xué)科目錄”中所占比重;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進一步拉大了人文學(xué)科與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本不平衡的學(xué)科布局,加深了學(xué)科發(fā)展的罅隙,人文學(xué)科的地位進一步被弱化。從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和學(xué)科屬性來看,理工類學(xué)科滿足了決策者對于精確性、標(biāo)準化、計算性的科學(xué)管理范式,容易進行比較、達成共識,并且能夠適應(yīng)我國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戰(zhàn)略,因而被置于更高的學(xué)科地位。
(三)“雙一流”建設(shè)中的工程化思維導(dǎo)向
在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無論是理工類學(xué)科還是人文類學(xué)科,都呈現(xiàn)出鮮明的工程化思維導(dǎo)向,按照一定的計算主義哲學(xué)價值觀,以可量化、可切割、可比較、可評測的思維邏輯來建設(shè)人文學(xué)科,必然使人文學(xué)科陷入技治主義的生存危機。在現(xiàn)實中,學(xué)科評估被納入一定標(biāo)準化的數(shù)據(jù)庫,并以數(shù)字和指標(biāo)的形式輸出排名;排名成為一些大學(xué)和學(xué)科評價結(jié)果的唯一表現(xiàn)形式,甚或是評價結(jié)果的主要目的,呈現(xiàn)出向國際化看齊、向指標(biāo)看齊、向計算主義看齊的價值傾向性,尤為重視諾貝爾獲獎?wù)摺H聲譽、國際期刊論文發(fā)表和引用率、學(xué)術(shù)“頭銜”等硬指標(biāo)。在“以排名論一流”的評價體系下,“雙一流”建設(shè)的績效經(jīng)常被等同于論文發(fā)表或?qū)W科排名,結(jié)果就是“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排名將會替代我們做出決策”[5]。事實上,不同學(xué)科有不同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和引用慣例,“人文學(xué)科領(lǐng)域的參考文獻,幾乎四分之三引自著作,而非期刊論文,長期以來該比例都保持相對穩(wěn)定;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80%以上的參考文獻源自期刊論文,引用著作的頻率較低,好像著作不如論文那么科學(xué)。”[6](P18)一本優(yōu)秀的人文學(xué)術(shù)著作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的積淀,而以可量化的數(shù)據(jù)評測為學(xué)科評估的主要工具,采用“效率至上”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模式,忽視了人文學(xué)科自身的積聚性與內(nèi)隱性。過于功利的工程化思維,只會導(dǎo)致人強烈的資本性。錢理群教授曾指出:“我們的一些大學(xué),包括北京大學(xué),正在培養(yǎng)一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德雷謝維奇在《優(yōu)秀的綿羊》中也提到,“精英高校并沒有興趣培養(yǎng)過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詩人、牧師、律師、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這種類型的人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養(yǎng)利他主義、創(chuàng)造力、知性思維以及理想主義。問題是,大學(xué)作為機構(gòu)本身,并不引導(dǎo)學(xué)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資源去創(chuàng)造更好的社會價值。學(xué)校默認了社會的價值取向:物質(zhì)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嚴和幸福”[7]。無論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還是“優(yōu)秀的綿羊”,本質(zhì)上都是人性物化的“資本人”在不同語境的翻版。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旨趣不應(yīng)該限于技術(shù)和應(yīng)用,而應(yīng)體現(xiàn)在解放旨趣上。人文學(xué)科要做到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需要走出工程化思維的束縛,回歸人的自然性和生命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文學(xué)科是現(xiàn)代“資本人”的防火墻,是遏制人性物化的最后一道關(guān)卡,必須承擔(dān)起人類的學(xué)科使命,做好人類靈魂的“瞭望塔”。
(四)“雙一流”建設(shè)中人文學(xué)科“國際化”的“學(xué)科運動”傾向
“雙一流”建設(shè)中常出現(xiàn)一些盲目推動人文學(xué)科國際化、西方化、英語化的“學(xué)科運動”傾向,過度追捧英文期刊和英文出版物,特別是以數(shù)量化為導(dǎo)向的SCI、SSCI期刊論文的發(fā)表。學(xué)科評估主要參照SCI、SSCI數(shù)據(jù)庫以及參加的國際會議等國際標(biāo)準。在職稱評審中,一篇SSCI論文相當(dāng)于四篇甚至五篇中文CSSCI論文,導(dǎo)致人文學(xué)者也紛紛轉(zhuǎn)向數(shù)量相對較多的SSCI期刊(從收錄的期刊目錄上來說,SSCI期刊有3 500多種,而中文C刊包括擴展版也只有700多種),運用西方的學(xué)術(shù)話語體系并模仿其寫作風(fēng)格和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優(yōu)先考慮西方期刊感興趣的話題和方法論,亦步亦趨緊跟西方學(xué)者的研究偏好,導(dǎo)致我國本土“顛覆性創(chuàng)新”的匱乏以及知識體系的松散。從期刊引文來看,國際期刊存在嚴重的語言偏向性,“《美國社會學(xué)雜志》獲得的引用中有97%的英文文獻,僅有3%為其他語種的文獻。相比之下,法國《社會科學(xué)行為研究》獲得的引用中有64%的為法文文獻,26%的為英文文獻,還有3%的為德文文獻。引文的地理來源也顯示了《美國社會學(xué)雜志》更多地聚焦本土,其中2/3的引文來自美國,而在法國《社會科學(xué)行為研究》中只有40%的引文來自法國。”[6](P47)從世界大學(xué)排行榜來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fā)布的U.S.News世界大學(xué)排名中的國際化比重占到了22.5%(“全球?qū)W術(shù)聲譽”12.5%、“國際協(xié)作”5%、“具有國際合作的出版物總數(shù)的百分比”5%),英國QS世界大學(xué)排名的國際化比重為20%(“全球雇主聲譽”10%、“國際教職工比例”5%、“國際學(xué)生比例”5%)。英國泰晤士報發(fā)布的THE世界大學(xué)排名國際化程度(工作人員、學(xué)生和研究)占比7.5%。上海交通大學(xué)發(fā)布的軟科世界大學(xué)學(xué)術(shù)排名的6大指標(biāo)幾乎全與國際化有關(guān),包括獲得過諾貝爾科學(xué)獎或菲爾茲獎的教師折合數(shù)(20%)、湯森路透公布的各學(xué)科領(lǐng)域被引頻次最高的科學(xué)家數(shù)(20%)、在《自然》(Nature)和《科學(xué)》(Science)上發(fā)表的論文折合數(shù)(20%)、被科學(xué)引文索引(SCI)和社會科學(xué)引文索引(SSCI)收錄的論文數(shù)(20%)、獲得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的校友折合數(shù)(10%)、上述五項指標(biāo)得分的師均值(10%)。可見,從一流大學(xué)排名到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國際化都是一個重要參數(shù),關(guān)涉著大學(xué)定位和學(xué)科建設(shè)方向。然而,不同學(xué)科研究對象或多或少的本土性對其指標(biāo)的有效性還是有影響的,在一些領(lǐng)域如哲學(xué)、歷史,主要是作者獨立發(fā)表論文,國際合作的比例就不能作為評價國際化的有效指標(biāo)。人文學(xué)科具有強烈的地域性、人文性、民族性與本土化等特征,是一個國家的文化符號,僅依靠國外的數(shù)據(jù)庫和外文學(xué)科評估標(biāo)準難以真實客觀反映我國人文學(xué)科的發(fā)展水平,更難以建立適切的中國知識體系。人文學(xué)科是中國學(xué)術(shù)話語體系的“發(fā)言人”,具有較強的地方性和意識形態(tài)屬性,必須扎根于中國“現(xiàn)實生活的情境”,其世界一流的標(biāo)準既要與人類其他文化對話,又要用中國“自己的話”解釋“中國模式”。
二、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中人文學(xué)科生長困局的原因分析
在現(xiàn)有知識生產(chǎn)模式主導(dǎo)的學(xué)科布局下,學(xué)校優(yōu)勢資源集中向短期內(nèi)見效快的理工類學(xué)科聚集,人文學(xué)科由于天然的內(nèi)隱性、長期性、積聚性與不確定性,其發(fā)展空間經(jīng)常受到擠占而面臨生長困局。實際上,學(xué)科建設(shè)應(yīng)該是同類學(xué)科共生共存,異類學(xué)科協(xié)同交叉的良性生態(tài)平衡,知識無貴賤,學(xué)科本無等級之差,所謂的差異皆是人為建構(gòu)的虛假之言。我們正處于流動的現(xiàn)代性(鮑曼語),人文學(xué)科從興盛到衰落再到生長困局,既與科學(xué)主義主宰的大環(huán)境有關(guān),也與“雙一流”建設(shè)的目標(biāo)站位、評估導(dǎo)向、技治主義思維有極大的關(guān)聯(lián)性。
(一)學(xué)科評估的計算主義哲學(xué)導(dǎo)向
近十年來,排名、評價、計量、h指數(shù)、影響因子等詞語在高等教育及其研究領(lǐng)域頗為盛行。政府和科研管理人員希望運用定量指標(biāo)來評價一切,包括對普通教師、教授、科研人員、課程和大學(xué)的評價[6](P1)。“雙一流”建設(shè)可以說是現(xiàn)代高等教育“計算主義”評價的產(chǎn)物,評價的比較性突出了“一流”的非一般性,以數(shù)據(jù)為本的計量式教育評價成為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裝置。在計算主義哲學(xué)的數(shù)據(jù)思維導(dǎo)向下,學(xué)科評估排名化,教育成了“可算度的教育”,學(xué)科成了“可算度的學(xué)科”,人也變成了“可算度的人”。馬爾庫塞表達了他的憂慮:“人和它的目的只是作為計算收益和利潤機會時的變量而進入其中,數(shù)字化達到了對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來進行運算的程度。”[8](P5)這種評價的“數(shù)字本位”,導(dǎo)致量化指標(biāo)成為理性的非理性選擇,實質(zhì)上是一種機械化的評價,試圖以一種類似“評價的泰勒主義”方式減少開展此類評價所需的專業(yè)知識。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在計算主義哲學(xué)的導(dǎo)向下,更傾向于優(yōu)先發(fā)展資助多、見效快、易量化的理工類學(xué)科,現(xiàn)有的世界大學(xué)排名評價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庫尤其是論文的數(shù)據(jù)庫大多也是以自然科學(xué)為主要對象的。例如,美國科技信息所(ISI)推出的基本科學(xué)指標(biāo)數(shù)據(jù)庫(ESI)對世界大學(xué)排名具有很大的影響。該數(shù)據(jù)庫分22個學(xué)科領(lǐng)域,其中20個是自然學(xué)科,只有2個社會學(xué)科,而人文學(xué)科一個也沒有,顯然這樣以ESI學(xué)科排名為參考并不能準確地評估我國的人文學(xué)科水平。有些高校為了迅速提高在大學(xué)排行榜中的位階,甚至直接停辦或裁撤某些人文學(xué)科院系,絲毫不考慮學(xué)科內(nèi)部的生態(tài)平衡。這種過于短視化、功利化、工具化的學(xué)科評估,是對學(xué)科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極大破壞,其數(shù)字景觀的背后是對人性的遮蔽與戕害。
(二)技治主義思維對人文學(xué)科的鉗制
技術(shù)時代以降,技治主義猶如空氣一般裹挾、形塑、規(guī)訓(xùn)著人類的思維、行動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現(xiàn)代性社會無法躲避的事實性存在。在技術(shù)至上的現(xiàn)代社會中,技治主義不僅環(huán)繞于我們周圍的一切,更成為控制人類思考走向的思維方式,技術(shù)理性正與經(jīng)濟理性、工具理性聯(lián)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勁的精神控制力量。技治主義思維遵循的是一種確定性的、單向度的實證主義分析哲學(xué),實證主義分析哲學(xué)本身就是單向度的思考方式、單向度的哲學(xué),因為它把語言的意義同經(jīng)驗事實和具體的操作等同起來,并把既定事實無批判地接受下來,從而把多向度的語言清洗成單向度的語言[8](P3)。在高等教育中,“雙一流”建設(shè)深受技治主義思維的強烈支配,“效率至上”“實用主義”的技術(shù)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使人處于技術(shù)王國中有用之器的工具性職能的地位。由于偏重技術(shù)性治理的目的性導(dǎo)向,大學(xué)里人文學(xué)科遭遇了冷漠與拒絕,“人文學(xué)科成為湖面上快要沉沒的年代已久的孤島,有可能淪落成博物館的文化或表演藝術(shù)的女仆的危險。或者成為點綴專門職業(yè)生活的花朵,供閑暇的消遣”[9]。我們現(xiàn)在面對的精神危機不是上帝已死的后果,而是人之死的結(jié)果;不是上帝需要被銘記,而是人性需要被重新喚醒[10]。在技治主義思維的主導(dǎo)下,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本身遵循著一套科學(xué)理性的實證主義原則,再加上可量化、易標(biāo)準化、操作性強、產(chǎn)出快的優(yōu)勢而成為“雙一流”建設(shè)的寵兒;相反,人文學(xué)科關(guān)涉的是一門與人性、文化、感性有關(guān)的“柔性學(xué)科”,既不易操作也不易控制,更無法迅速看到產(chǎn)出,對于決策者來說,具有一定的風(fēng)險性,超出了技治主義的理性閾限。技治主義遵循著一套“投入-產(chǎn)出”的因果律治理模式,自然科學(xué)學(xué)科符合因果律的控制過程,周期短、數(shù)據(jù)清晰、決策失敗的風(fēng)險較小;人文學(xué)科難以按照因果律的原則直接控制,周期性長、概念模糊、投資風(fēng)險較大。因此在技治主義思維模式控制下,“雙一流”建設(shè)的學(xué)科布局助長了學(xué)術(shù)界“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yīng)。在這種技術(shù)方式下,一個人“丟失的是無價之寶,即能夠毫不間斷地忠于他童年時代的沉思本能,借此達到一種寧靜、統(tǒng)一,一種關(guān)聯(lián)和協(xié)調(diào),這些東西是一個被培養(yǎng)去進行生存斗爭的人未嘗夢見過的”[11]。
(三)資本邏輯對人文學(xué)科的束縛
現(xiàn)代性社會的人類處于一切皆可“資本化”、一切皆化為“資本”的生存場域。這是一個“資本”通行的盛世,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技術(shù)資本、學(xué)術(shù)資本、知識資本等浸染于個體化的生命空間,成為指導(dǎo)人類行為準則最可靠、最直接的理性標(biāo)準。“今天,將全部生活都包容到機器中去的過程再也不能避免,生活已變成一個企業(yè),其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工人和雇員”[12]。諾布爾在1998年一篇題為《數(shù)字文憑作坊:高等教育的自動化》中提到:“最近二十年,大學(xué)里發(fā)生的最主要變化,便是校園成為了資本積累的重要場所。”[13]學(xué)術(shù)成為資本在于學(xué)術(shù)是“有用”和“有價值”的,并且學(xué)術(shù)是一種獨特形態(tài)的、能夠維持自我發(fā)展的內(nèi)在收益和更持久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利潤”的稀缺資源,故學(xué)術(shù)暗含著資本化的潛質(zhì)[14]。馬克思提出了資本的“效用原則”,在一定意義上可說成是資本的“金錢原則”,資本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與金錢聯(lián)系在一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轉(zhuǎn)變成能賺錢的機器。資本的自然屬性就是使一切可獲得之物成為工具,資本追求的是無限的增值。如今,資本的邏輯或價值體系已經(jīng)滲透到人類的時間、空間、肉體與靈魂,是附加于現(xiàn)代人性之上的赤裸裸的價值本色,成為我們時代文化與社會的“關(guān)鍵詞”。后工業(yè)社會全球性的資本擴張對于高等教育哲學(xué)的解構(gòu)、對于學(xué)科結(jié)構(gòu)的威脅、對于“利欲性”人格的放大都加劇了現(xiàn)代性社會中“資本人”的急劇生產(chǎn)性擴張。“雙一流”建設(shè)在學(xué)科布局上也推崇著這種學(xué)科“資本主義”的邏輯,甚至出現(xiàn)了學(xué)科“鄙視鏈”——為了在學(xué)科評估中獲得優(yōu)先排名,裁撤一些社會效益或資本效益一般的弱勢學(xué)科或“軟學(xué)科”,而為迎合市場需要,極力發(fā)展經(jīng)濟效益或職業(yè)效益較好的“硬學(xué)科”。學(xué)科建設(shè)中,人工智能、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工程學(xué)、生物醫(yī)學(xué)等理工類學(xué)科因具有較強的市場潛力和經(jīng)濟價值被置于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位置,成為學(xué)科競爭資源的優(yōu)勝者,受到政府決策者、企業(yè)單位、學(xué)生家長等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青睞,教育學(xué)、文學(xué)、哲學(xué)、歷史、藝術(shù)等人文學(xué)科因其固有的藝術(shù)性、思想性和非功利性而較少有機會爭取到外部支持,甚至淪為學(xué)生的“備選學(xué)科”,處于被遺忘的尷尬境地。為了贏得學(xué)科的發(fā)展契機,人文學(xué)者們“皆企圖模仿科學(xué)的方法與程序,連藝術(shù)都被‘非人化了”[15]。我們?nèi)绻粓猿终J定人文學(xué)科和藝術(shù)的至關(guān)重要性,它們就會離我們而去,因為它們不能賺錢。實際上,它們的作用遠比賺錢寶貴,“它們能造就一個值得人類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們能使人們將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應(yīng)當(dāng)受到尊重與同情;它們能造就這樣一種國家,能戰(zhàn)勝恐懼和懷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講理的辯論。”[16](P160)“雙一流”建設(shè)固然重要,但人文學(xué)科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取值是難以計量求證的,過于追求學(xué)科的資本效益,必將人文學(xué)科推向機械化的生存危機。
(四)國際化偏好對人文學(xué)科的誘導(dǎo)
“國際化”成為21世紀大學(xué)評價與學(xué)科評估的通用規(guī)則,是衡量某一領(lǐng)域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打造“世界一流大學(xué)”和“世界一流學(xué)科”是近幾年高校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戰(zhàn)略,大學(xué)走向國際化無可厚非,但就學(xué)科建設(shè)而言,并非所有學(xué)科都適合國際化。在科研評價中,使用期刊排名和影響因子帶來的另一個重要但不太明顯的負面影響是,它使科研人員遠離本土的、邊緣的或不流行的研究主題。這在人文和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尤其危險,因為它們的研究對象本質(zhì)上比自然科學(xué)更本土化。“由于引用率最高的都是英文期刊(這一特征常常被誤認為是“國際期刊”的同義詞),所以要獲得期刊的認可取決于期刊對研究對象的興趣。因此,想要獲得更高引用率的經(jīng)濟學(xué)家傾向于研究美國的經(jīng)濟,而不是法國或加拿大的,因為引用率最高的美國經(jīng)濟學(xué)期刊對這些研究并不感興趣。”[6](P46) 如果機械地使用引用指標(biāo)而不考慮其“指示性”,那么那些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本土研究對象將被低估甚至最終被忽視。加拿大經(jīng)濟學(xué)家的例子已經(jīng)證實:在過去30年里,為了在其領(lǐng)域內(nèi)所謂的頂級期刊上發(fā)表論文,這些專家對當(dāng)?shù)氐慕?jīng)濟問題逐漸失去了興趣[17]。在解讀學(xué)科評價指標(biāo)時,如果不考慮不同學(xué)科的知識本體性,只會使科研人員放棄對不太主流主題的研究,以免不能在官方評價體系中“A”類或“B”類期刊上發(fā)表論文。奇怪的是,這種分類方案中的“A”類期刊大多是英文期刊,全國性期刊則傾向于被列為“B”類,而所謂的本地性期刊則被增選委員會和組織列入“C”類。事實上,在對人文與社會科學(xué)期刊進行排名的歐洲組織早期提出的許多分類中,不難發(fā)現(xiàn)某種形式的殖民主義[6](P46)。人文學(xué)科走向國際化與世界文化交流的前提是立足于本土化的知識體系與社會實踐,而不是盲目向西方靠攏、借用西方的評價指標(biāo)和理論模型,自身文化立場不堅定,極易陷入學(xué)科“殖民化”風(fēng)險。
三、世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背景下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新思路
“我們正在追求能夠保護我們、使我們愉快、讓我們感到舒適的占有物,泰戈爾將它們稱作我們的物質(zhì)‘外罩。但是,我們似乎忘記了靈魂,以豐富、細膩、復(fù)雜的方式,將個人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我們似乎忘記了應(yīng)將他人看做有靈魂的人,而不應(yīng)僅僅看做有用的工具,不應(yīng)看做實現(xiàn)我們計劃的障礙;我們似乎忘記了應(yīng)將自己看做有靈魂的人,與他人溝通,應(yīng)將他人看做深刻、復(fù)雜的靈魂,與我們自己相同。”[16](P6)人文學(xué)科更重要的學(xué)科使命大概是人類靈魂的喚醒和自由意志的沉思,回歸事物的真實形態(tài),培養(yǎng)我們的“內(nèi)心視點”。
(一)通過學(xué)科交叉實現(xiàn)顛覆式創(chuàng)新,找準人文學(xué)科的“內(nèi)心視點”
“顛覆性創(chuàng)新”是著名經(jīng)濟學(xué)家克里斯坦森在《創(chuàng)新者的窘境》中提出的一個概念。“雙一流”建設(shè)既要重視學(xué)科內(nèi)生性、傳承性與發(fā)展性,也要在制度、組織與知識體系層面通過學(xué)科交叉實現(xiàn)顛覆式創(chuàng)新,以動態(tài)開放的視角審視知識結(jié)構(gòu)的“聯(lián)通性”。在傳統(tǒng)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下,學(xué)科和學(xué)科組織幾乎都是“封閉化的科研場域”,這種“內(nèi)循環(huán)”式的知識生產(chǎn)文化造成了不同學(xué)科邊界上的“文化圍墻”和不同學(xué)科間乃至異質(zhì)學(xué)科間心理上的“文化隔閡”[18]。今天的“江湖”是學(xué)科會聚的命運共同體,從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到工業(yè)經(jīng)濟再到知識經(jīng)濟,社會的形式在變,學(xué)科也要重新定義。新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結(jié)果是學(xué)科邊界的日趨模糊,從單一學(xué)科到學(xué)科交叉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和事實,跨學(xué)科工作成為一種規(guī)則。這就決定了人文學(xué)科必須進行范式創(chuàng)新,打破固有的學(xué)科劃分邏輯,進一步促進人文學(xué)科與自然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交叉融合,真正進行跨界協(xié)同的復(fù)合型研究。從教育部公布的《學(xué)位授予(不含軍事單位)自主設(shè)置交叉學(xué)科名單(截至2020年6月30日)》來看,人文學(xué)科所設(shè)交叉學(xué)科相對較少,如中國人民大學(xué)自主設(shè)置了12個交叉學(xué)科,有3個人文交叉學(xué)科(中國學(xu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國學(xu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設(shè)置了9個交叉學(xué)科,有1個人文交叉學(xué)科(文化傳播與管理),清華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均未設(shè)置人文交叉學(xué)科。面對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的契機,人文學(xué)科必須依靠跨學(xué)科研究的天然優(yōu)勢,利用通識教育的課程平臺,尋找與自然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的共通性知識生長點,聚焦于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審思,開發(fā)新的知識域,找準人文學(xué)科的“內(nèi)心視點”。實質(zhì)上,人文學(xué)科就是啟發(fā)心靈的思想,使之聯(lián)系外界事物,再返回思考心靈本身,以認識事物的真實形態(tài)。人文學(xué)科的“內(nèi)心視點”應(yīng)該是激活人類的思考與想象,超出于學(xué)科的閾限,學(xué)會彼此關(guān)照對方思想感情的內(nèi)心機能,使人際關(guān)系成為豐富的人性關(guān)系,而不是簡單的互相利用和操縱的關(guān)系。
(二)強化學(xué)科主體意識,重建中國特色“國家+”人文學(xué)科知識體系
當(dāng)前,我國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對西方名校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總是遵循“世界標(biāo)準”和“國際慣例”,照搬英美建設(shè)方案,逐步走向西方化、同質(zhì)化、去國家化的“學(xué)科陷阱”。一般而言,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建立在對本國文明的思考之上,西方文明就立足于西方的社會實踐和知識系統(tǒng),而我國尚未建立起獨立、系統(tǒng)、完善的知識體系,需要借助國外的學(xué)科標(biāo)準來衡量自己,導(dǎo)致中國學(xué)者對我國學(xué)科產(chǎn)生“邊緣危機意識”。當(dāng)前人文學(xué)科最大的問題應(yīng)該是缺乏學(xué)科主體意識,找不到學(xué)科文化歸屬,慣用西方的理論模型、概念結(jié)構(gòu)、研究方法、話語范式和引文數(shù)據(jù)庫來解釋中國的本土化實踐。然而,人文學(xué)科的地域性極強,難以區(qū)分先進與落后,其影響因子的關(guān)鍵不是理論模型的創(chuàng)新,而是本國文明的建構(gòu)。人文學(xué)科彰顯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氣質(zhì)與精神風(fēng)貌,是國家文明的“透視鏡”,其學(xué)術(shù)體系必須建構(gòu)在“現(xiàn)實的中國情境”基礎(chǔ)之上,強化人文學(xué)科主體意識,自覺抵制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浸染,努力建設(shè)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顏色、中國底色的一流人文學(xué)科。“中國特色”意味著要走“中國式”的學(xué)科建設(shè)之路,棲息于中國本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和風(fēng)土人情,構(gòu)建具有“國家+”的中國特色人文學(xué)科內(nèi)涵,設(shè)計立足中國話語和中國方案的人文學(xué)科知識體系,用中國概念講好中國故事。所謂“國家+”是要體現(xiàn)國家的文化符號和國家氣質(zhì),是超脫于概念范疇的一種理念或標(biāo)識。一份成功的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方案應(yīng)該包括:立足中國本土的價值理念、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適用性情境;借鑒世界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的共同經(jīng)驗,如制度安排、學(xué)科治理、資源配置、人才培養(yǎng)、學(xué)術(shù)研究、學(xué)術(shù)成果轉(zhuǎn)化等;在國際舞臺上發(fā)聲,表達本土的學(xué)科立場,參與國際學(xué)術(shù)交流,加入國際學(xué)術(shù)組織等。概言之,一流的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必須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不能為了“一流”而損害人文學(xué)科的“國家性”,這是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的基本立場,也是我國建設(shè)世界一流大學(xué)的“根基”。
(三)走出指標(biāo)“陷阱”,構(gòu)建適切的人文學(xué)科評價體系
教育評價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是工業(yè)化或工廠化教育對生產(chǎn)過程、生產(chǎn)結(jié)果及其產(chǎn)品的技術(shù)性描述手段,本意是收集顯性、易量化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減少誤差,降低資源消耗,以滿足利益相關(guān)者的科學(xué)指數(shù)。現(xiàn)實中,這種計量評價可以在短期內(nèi)快速滿足決策者的任務(wù)性指標(biāo),卻往往阻礙原創(chuàng)性、頂尖研究成果的產(chǎn)出和“卡脖子”技術(shù)的突破,是一種超強功利化的短期主義“教育陷阱”。這種計算主義支配下的大學(xué)評價遵循一套標(biāo)準化的數(shù)學(xué)模型,試圖將一切自然現(xiàn)象客觀化、定量化、具體化,與自然科學(xué)的確定性、實證主義、可量化原則相匹配,滿足了自然科學(xué)的計算性要求,而人文學(xué)科的思想性和人文性都需要長期建構(gòu),無法通過簡單的數(shù)字模型進行估算。人文學(xué)科是一門“解釋”人、“透視”人、“理解”人的學(xué)科,致力于教育過程中對人的主體性、生命性和內(nèi)在精神性的喚醒,以培養(yǎng)學(xué)生“正當(dāng)?shù)那楦小⒄_的判斷、自覺的生命體驗”為己任。因此,人文學(xué)科既不能按照理工類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評價標(biāo)準,也不能按照西方主導(dǎo)的評價指標(biāo)來評判。建設(shè)一流人文學(xué)科應(yīng)兼顧國際視野和民族特性,取消對國際論文發(fā)表的盲目追求,極力遏制“唯論文”的“一刀切”評價方式,減少對量化指標(biāo)和國際化評估標(biāo)準的依附性,開發(fā)形式多樣的人文學(xué)科評價標(biāo)準,注重人文學(xué)科的“默會成分”。人文學(xué)科評價指向的應(yīng)該是人類的終極善,必須超越計算主義的技術(shù)性手段和短期主義的功利性指標(biāo),維護指標(biāo)設(shè)計的國際通用性和地域差異性的平衡,克服評價的趨同導(dǎo)向以優(yōu)化學(xué)科的生態(tài)位次,實現(xiàn)從數(shù)據(jù)導(dǎo)向到人的主體性導(dǎo)向的位移。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把人的終極實踐看作是追求最高的善的行動,最高的善是人的福祉和人的德性完善,即靈魂的完善,這也是人的幸福的內(nèi)涵,因此,教育最高的實踐是完善人的德性、完善人的靈魂的行動,即是為了人的發(fā)展的[19]。
(四)超越數(shù)字人文,找準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xué)科的主體性優(yōu)勢
這是一個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云計算、虛擬技術(shù)裹挾的數(shù)字時代,數(shù)據(jù)范式正在引起人類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巨大革命,人文學(xué)科也難逃數(shù)字的“殖民”。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xué)科陷入了實用主義、科學(xué)主義、專業(yè)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圍困中,處于“四面楚歌”的生存困境。為突破傳統(tǒng)人文學(xué)科的外展性不足,數(shù)字人文成為當(dāng)下人文學(xué)科研究的學(xué)術(shù)熱點和趨勢。數(shù)字人文是通過一定的數(shù)字處理軟件,搭建文本數(shù)據(jù)庫,使用編碼化的符號語言,按照一定的“算法”邏輯,遵循標(biāo)準化的計算指令,對人文知識進行分析和解構(gòu)的數(shù)據(jù)化處理技術(shù),以呈現(xiàn)可視化、可量化的數(shù)字知識圖譜。近十年來,世界各國相繼成立了數(shù)字人文中心、數(shù)字人文研究機構(gòu)、數(shù)據(jù)庫平臺,組建了數(shù)字人文研究團隊,主要依托于計算機、數(shù)學(xué)、地理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歷史等學(xué)科,實現(xiàn)了人文學(xué)科的數(shù)據(jù)化。目前,歐美國家與中國文化有關(guān)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項目主要有:中國歷代人物傳記數(shù)據(jù)庫、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古籍半自動標(biāo)記平臺。數(shù)字人文在學(xué)界很時髦,但我們真的相信人文學(xué)術(shù)能被量化嗎?換句話說,學(xué)術(shù)真的可以完全量化嗎?如果只能用量化的方法,我們就面臨一切皆可量化的誘惑。很明顯,現(xiàn)實是復(fù)雜多維的,量化僅是一種技術(shù)工具,而不能承包我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我們必須特別謹慎,不要被追求效率的數(shù)字化測量所誘導(dǎo),尤其是在數(shù)字沒有代表重大事實的地方,一切以數(shù)字形式呈現(xiàn)給決策者的東西都是表象,而不是真理。認為表象就是真理,必然導(dǎo)致決策的失誤。在大學(xué)里,這可能是災(zāi)難性的”[20]。人文學(xué)科必須找準人工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優(yōu)勢,立于人性的教化、情感的交互與生命的關(guān)懷,這是人工智能暫時無法替代的領(lǐng)域,也是人文學(xué)科最后的從容。
“雙一流”建設(shè)是我國學(xué)科發(fā)展的重要契機,人文學(xué)科作為國家的“心臟”,要超越“一流”,走向卓越,為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國家建設(shè)指明方向,做好人類文明的“瞭望塔”。人文學(xué)科對于受教的人可以做兩件事:“第一是鍛煉心情,其結(jié)果可以把我們所有的才情發(fā)展出來,從邏輯的分析起到藝術(shù)的欣賞止,真是應(yīng)有盡有。第二是供給一個寬闊的機架,其中的樞軸經(jīng)緯可以是歷史的、邏輯的以至于物理、化學(xué)、生物的現(xiàn)象所交織而成的種種關(guān)系;有了這個機杼,一個人在前途生命史里耳目所接觸的一切事物,心理所經(jīng)歷的一切見解,就各有其附麗的地方,不致茫無頭緒,泛濫無歸。”[21]
參考文獻
[1] [德]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M].鄭作彧,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3.
[2] [美]烏爾里希·貝克.風(fēng)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69.
[3] [加]雷丁斯.廢墟中的大學(xué)[M].郭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51.
[4] 鄭永年.中國的知識重建[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163.
[5] 王建華.對高等教育中問責(zé)與績效評價的反思[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20(07):1-7.
[6] [加]伊夫斯·金格拉斯.大學(xué)的新衣?——對基于文獻計量學(xué)的科研評價的反思[M].劉莉,董彥邦,王琪,譯校.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19.
[7] [美]德雷謝維奇.優(yōu)秀的綿羊[M].林杰,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65.
[8] [美]馬爾庫塞,H.單向度的人:發(fā)達工業(yè)社會意識形態(tài)研究[M].張峰,呂世平,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9] 金生鈜.大學(xué)人文教育與公民理性[J].大學(xué)(研究與評價),2008(05):75-77+93.
[10] 桑海云,馬培培.技術(shù)時代關(guān)于大學(xué)之道的省思[J].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2019(01):17-22+123.
[11]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教育何為?[M].周國平,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社,2019:31.
[12] [德]雅斯貝爾斯.時代的精神狀況[M].王德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202.
[13] [法]達尼·羅伯特·迪富爾.西方的妄想:后資本時代的工作、休閑與愛情[M].趙颯,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114.
[14] 冉隆鋒.大學(xué)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的意義危機及選擇[J].現(xiàn)代大學(xué)教育,2018(03):18.
[15] M.V.C.Jeffreys.Personal Values in the Modern World[M].Baltimore Maryland:Penguin Books,1962:81.
[16] [美]瑪莎·努斯鮑姆.告別功利:人文教育憂思錄[M].肖聿,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17] Wayne Simpson and J.C. Herbert Emery.Canadian Economics in Decline:Implications for Canadas Economics Journals[J].Canadian Public Policy,2012(04):445-470.
[18] 白強.大學(xué)知識生產(chǎn)模式變革與學(xué)科建設(shè)創(chuàng)新[J].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2020(03):31-38.
[19]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20.
[20] [美]羅伯特·波恩鮑姆.高等教育的管理時尚[M].毛亞慶,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156.
[21] [英]赫胥黎.赫胥黎自由教育論[M].潘光旦,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34.
Analysis on the Growth Dilemma of Huma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ANG Qing-ling
Abstract: Humanitie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discipline. From the published list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he proportion of humanities is low, 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is insufficient, and it shows a distinct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and data based thinking orientation. The main courses are as follows: the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rientation of discipline evaluation, the restriction of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inking on humanities, the constraint of capital logic on humanities, and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preference on humaniti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alize subversive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find out the inner view of humanities, strengthen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disciplines, reconstruct national + humanities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et out of the trap of indicators, construct appropriate evaluation system of humanities, and transcend digital humanities to find out the subjectivity advantage of humanit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world-class discipline;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interdisciplinary; digital humanities
(責(zé)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