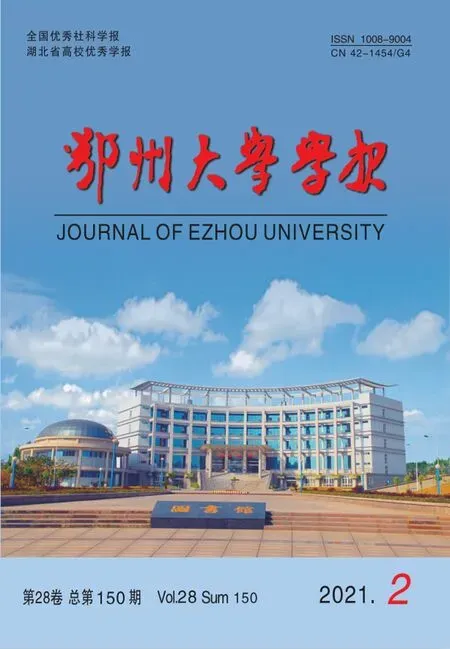陌生化,修辭藝術(shù)反常化的程序
——淺析漢語修辭的陌生化
潘婷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xué)莆田分校,福建莆田351100)
漢語修辭,在西方文獻(xiàn)中,用的是rhetoric,它來源于希臘語詞,本義是河流,后用水的流動(dòng)不息比喻人的話語。在西方古典文獻(xiàn)中成為專門指稱演講術(shù)或論辯術(shù)的詞語,后來范圍擴(kuò)大到指口語和書面語的表達(dá)技巧。在中國文獻(xiàn)中,孔子在《周易》中曾針對“文言”提出“修辭立其誠”的主張,東漢王逸也曾在《楚辭章句》中言:“修,飾也。”就是使簡陋平俗的內(nèi)容更豐富化。古代對于修辭的解讀大概都指向文教這一釋義,是道德層面的“誠實(shí)”。“修辭立其誠”意思是在語言外殼上要注重修理文教,在語言內(nèi)髓上要根立于“誠實(shí)”,是對漢語內(nèi)在外在進(jìn)行改造的修辭藝術(shù)。現(xiàn)代的解讀:“辭”指經(jīng)典文獻(xiàn)中的語言,“誠”就意味著文字要講究順應(yīng)天道天法。“修辭立其誠”的內(nèi)涵解讀就是:通過對文章典著中語言進(jìn)行仔細(xì)斟酌和反復(fù)吟哦后,擷取語言中蘊(yùn)含的深層含義,在人倫性德方面構(gòu)建起一種順應(yīng)天道的德行典范。而在五四以后,引進(jìn)漢語時(shí)候,才被譯成“修辭”。
“陌生化”概念是由俄國美學(xué)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就是使人們非常熟悉的東西原本的面貌煥然一新,將失去的、被固化的、被鈍化的審美意味重新尋找回來,變成具有陌生感的事物,使人產(chǎn)生一種審美新距離。讓這些平常事物變得生疏,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對語言理解的時(shí)間和延伸了事物之間聯(lián)系的距離,有了一種自由的、具有新理解方向的審美感覺。也就是說,陌生化就是對常規(guī)常識(shí)的反常化,造成語言理解與感受上的一種獨(dú)特意味的疏離感。[1]
陌生化其實(shí)本身就是一種藝術(shù)的基本法則,漢語修辭學(xué)中可謂是一種獨(dú)特的語言藝術(shù),他將漢語重新組合,煥發(fā)出新的活力,給人新鮮感。這種讓讀者感覺面貌一新的驚奇感是修辭藝術(shù)追求的普遍現(xiàn)象與基本規(guī)律。[2]
一、漢語修辭陌生化的方法
(一)詞語活用的陌生化修辭
陌生化的前提是語言的“新”,而“新”的生命張力,在“言”與“意”之間。這就必須要在詞語方面進(jìn)行革新,創(chuàng)造新的組合形成“尋常詞語藝術(shù)化”“詞語超常組合”。
1.尋常詞語藝術(shù)化
尋常詞語藝術(shù)化,就是將平常所見的熟悉詞語加以藝術(shù)感的修飾,使之變成新雅雋永的言辭。這種創(chuàng)新思維古已有之,即所謂的“煉字”,可從詞語的內(nèi)容以及形式來進(jìn)行藝術(shù)革新。
尋常詞語藝術(shù)化具體體現(xiàn)為:如《蘇幕遮》詞中:“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fēng)荷舉。”一字“舉”,本是人特有的動(dòng)作,在這里卻用以描述風(fēng)吹荷葉的形態(tài),是非人物詞與人物詞的反常化搭配,故意打破了語言的屏障,讓線性組合規(guī)律變成了立體化的融合,將具體的和抽象的粘合起來,產(chǎn)生新的旨意。
又如“閃閃爍爍的聲音從遠(yuǎn)方飄來,一團(tuán)團(tuán)白丁香朦朦朧朧。”這句充分調(diào)動(dòng)了語言給人的感官體驗(yàn),造成了一定的錯(cuò)覺現(xiàn)象,用“閃閃爍爍”來形容聲音,聲音不單單再是聲音,它還有具體的形象,在客觀的敘述中給主觀體驗(yàn)者一種亦真亦幻的效果和豐富變幻的審美質(zhì)感。這就是所謂的漢語修辭學(xué)中的通感現(xiàn)象,能夠打破感覺的局限,創(chuàng)造性地拓展語言思維,以此來激活讀者已經(jīng)麻木了的感官體驗(yàn),發(fā)生新的聯(lián)想,達(dá)到新的語言修辭審美體驗(yàn)。[3]
所以將尋常詞語重新進(jìn)行編程,會(huì)大大提高原修辭的審美,會(huì)釋放詞語組合已經(jīng)被規(guī)則禁錮了的所蘊(yùn)藏的力量!
2.詞語超常組合
詞語的超常組合就是可以將兩個(gè)完全沒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詞語放在一起組合成新的意義,這有利于漢語修辭藝術(shù)化再創(chuàng)造的形成,具有發(fā)展意義。詞語超常組合會(huì)造成離方遁圓、生生不窮的詞語藝術(shù)效果。
如:“寺院,金黃色的鐘聲,將夕陽擊落,野草叢中。”這里用“金黃色”來修飾“鐘聲”,使得語言內(nèi)涵更豐富,讓讀者自覺地開始聯(lián)想出鐘聲是被夕陽染成了金黃色,并且幽遠(yuǎn)的鐘聲又把夕陽擊落了,雖然這是不真實(shí)的,但卻在語言修辭里變得真實(shí)了。夕陽金黃色的余暉和山中幽遠(yuǎn)的鐘聲就這樣疊加在一起,變得層次豐富、流動(dòng)變化、立體可感。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修辭中的語素組合不可生拉硬拽地胡亂組合,而是應(yīng)該注意長短句相從、平仄相從、位置相從等。只有這樣才能在語言普遍的聯(lián)系與內(nèi)在規(guī)律中進(jìn)行突破,將語言魅力更深邃地呈溢出來。
(二)以丑襯美的陌生化修辭
陌生化就是使得語言反常化,使之標(biāo)新立異,搖身一變,具體方法可以通過語言變形、語言扭曲、語言顛倒、語言拉長或縮短,產(chǎn)生一種延變的“誤現(xiàn)象”,典型的體現(xiàn)之一是利用以丑襯美的修辭手段來表現(xiàn)延誤的漢語語言現(xiàn)象。
如:唐朝詩人李賀的詩句“明星燦燦東方陲,紅霞稍出東南涯”,燦燦的星辰與紅霞,透過煌耀濃郁的顏色側(cè)寫出了迢遙妙曼的旖旎心境。李賀詩作中的意象大多連綿緊湊,他筆下的“病骨”“荒畦”“蟄螢”“鬼燈”“血斑”等等,開啟了另一種視角,讀來也是趣味盎然,值得玩味。
再如:于堅(jiān)的詩歌《一只蝴蝶在雨季死去》有這樣一段語言描述:“一只蝴蝶在雨季死去……那死亡被藍(lán)色的閃電包圍……星星淹死在黑暗的水里/這死亡使夏天憂傷……”這首詩中“蝴蝶的死”和“星辰的隕落”都帶有死亡的灰暗,這種悲慘的死亡方式正是人生絕望境地的呈現(xiàn),美麗的事物和灰暗的事物聯(lián)合在一起,又加之丑與美、生與死的對比,產(chǎn)生了一定的審美距離。其陌生得如此奇特新怪、陌生得如此復(fù)雜深邃、陌生得如此富有深刻哲理。
以丑襯美的反常化漢語修辭讓大眾產(chǎn)生新奇的視角,能夠豐富文本修辭藝術(shù),讓漢語搖曳多姿、五光十色,富有獨(dú)特魅力。[4]
(三)幽默的陌生化修辭
修辭是一種表達(dá)活動(dòng),表達(dá)者在一定的語境中,有意識(shí)地將語言要素進(jìn)行重新選擇、組織、配置,這往往會(huì)通過“幽默”手法來表現(xiàn)。幽默是一種積極性的修辭現(xiàn)象,將平常語言進(jìn)行反常化,偏離原本的語言軌跡重新規(guī)劃語言程序編寫的路線。幽默也是陌生化的表現(xiàn)形式,可以將修辭的語言要素更巧妙地凸顯出來,強(qiáng)化漢語語言魅力。[5]
幽默的修辭,可以采用各種呈現(xiàn)手段來恰如其分地表達(dá)語言中的思想情感。如:在夏目漱石著作的《我是貓》中,作者就多次運(yùn)用偏離尋常邏輯的語言,以此來釋放被禁錮的審美意味。如:“假如春風(fēng)總是吹拂這么一張平滑的臉,料想那春風(fēng)也太清閑了吧!”這句話的藝術(shù)修辭設(shè)置春風(fēng)這一事物來說明苦沙彌無聊平庸的人物形象,借平常事物變成不平常,特點(diǎn)盡顯而出。
幽默這種反常化的藝術(shù)修辭手法可以幽微深邃地反觀平俗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讓枯燥無味的平常語言煥然為耐人尋味的語言,又可以帶給讀者體味語言美麗的愉悅感。有一首饒有趣味的詩:“這兒很少刮風(fēng)/一年只刮兩次/一次刮半年/這兒刮的風(fēng)很小/連一片秋葉也吹不下來/這兒沒有樹。”這種看似直白的句子,深品之,則會(huì)變成曲折跌宕。經(jīng)過如此修辭后,不僅了然到這里一年天天都在刮風(fēng),風(fēng)之所以吹不落樹葉也是因?yàn)檫@里沒有一棵樹,貧瘠如荒漠,為此心靈感到失落。這首詩句中的感情由一種如“陌生化”的新鮮感慢慢渡到一種干燥感,又在這干燥感中感到富有新意。通過語義的褒貶的色彩改變、婉曲地表達(dá)出來。如果詩人說“這里一年都在刮風(fēng),這里沒有樹”在這種陳腔舊調(diào)下還有什么興趣來品味這首寓意深刻的詩呢!
二、漢語修辭陌生化的意義
生活總是平淡單調(diào)、百無聊賴的,陌生化的修辭活動(dòng)是人們繁忙生活中的調(diào)味劑,能夠在貌似簡單輕松的內(nèi)容之中體驗(yàn)和感悟其背后蘊(yùn)涵深刻的道理。陌生化修辭不僅是敘述方式的個(gè)性化,更是以新的視角來對事物產(chǎn)生了一種讓人感到陌生新奇的效果,仿佛重新煥發(fā)出了獨(dú)特的生命活力。然,陌生化的漢語修辭功能并不是單單局限在使人產(chǎn)生另外一番新鮮驚奇的感覺范疇里,這種反常化的程序真正目的在于更加真切實(shí)在地將語言審美藝術(shù)獨(dú)特化、個(gè)性化、豐富化,呈現(xiàn)給讀者時(shí),能夠讓讀者有一種云霧頓散的靈感醒悟,從而讓其內(nèi)心因?yàn)檎Z言散發(fā)的魅力而變得鮮活靚麗起來。[6]語言呈現(xiàn)不再是一種思維麻痹狀態(tài),要注入新的語言力量,使得語言因?yàn)槟吧揶o達(dá)到語言世界光怪陸離的最高境界!
在未來修辭藝術(shù)探究的道路上,陌生化這種反常規(guī)的藝術(shù)程序,可以讓泱泱中華漢語修辭藝術(shù)更加流光溢彩,芳華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