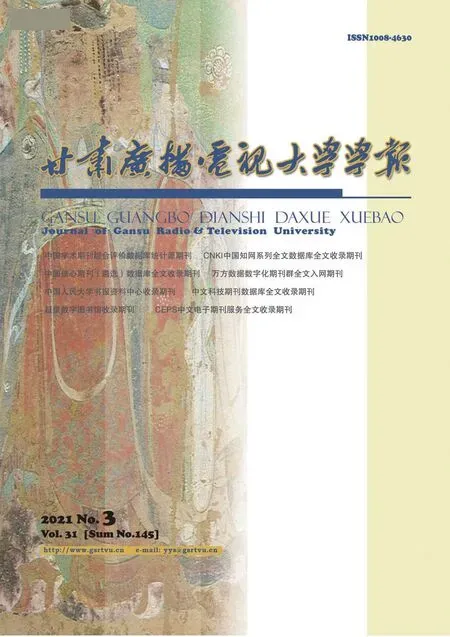劉勰文章潤色觀芻議
徐慶玲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文章的潤色一直以來都是文學家們所關注的重點,從情感到句法、辭采到音律,無不可作為裝點文章的要素。從先秦到魏晉,關于文章的潤色的論述要數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論述最為折中、系統。
一、“澤”的含義與“悅澤”論
從字形上看,金文“澤”字的部首為水,整個字形如羊在飲水。在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古代中國,水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以水為部的字自然也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先秦典籍中,“澤”字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在《詩經》《周易》《莊子》《孟子》中也屢見不鮮。據《廣韻》,“澤”字本義與水有關。
《周易·說卦傳》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1]434由于水是澤之所以存在的因素之一,故后“澤”常與“潤”相結合成為一個詞語。西漢劉向《說苑》云:“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2]即“澤”的作用是滋養萬物,使萬物達于一種“說(悅)”的狀態。后“澤”又常與“悅”連用,如漢代焦延壽的《焦氏易林》:“鳧得水沒,喜笑自啄。毛羽悅澤,利以攻玉。”[3]形容鳥身上羽毛的光鮮亮麗,而其原因正是得益于水的潤色。
“悅澤”一詞由自然界轉而進入文學家的視野,始于晉。陸云《與平原書》:“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4]陸云并未指明“悅澤”具體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內容,只是暗含與“潤色”有相近或相似含義。
自先秦至漢魏六朝,“悅澤”論的發展一直處于一種介于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狀態之間。一方面,作家們都注重文章的潤色,在聲律、采藻、修辭等方面都不遺余力地加工;另一方面,這種自發的行為由于缺乏文學理論的節制,逐漸走向了另一種極端——繁縟。至齊梁,劉勰作《文心雕龍》方重申“悅澤”的含義與使用原則。
二、劉勰“悅澤”論的內涵與原則
劉勰的“悅澤”論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龍》中,其《銘箴》《誄碑》《雜文》《諸子》《定勢》等篇都有對“澤”的論述。尤其在《定勢》篇中,劉勰稱贊陸云“往日論文,先辭而后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5]531。并因此提出“勢實須澤”的主張。
在《文心雕龍·知音》篇中,劉勰提出了鑒賞作品的六要素:“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5]715“置辭”“奇正”“事義”“宮商”都與文章的潤色有關。另外,《镕裁》篇也規定寫文章的三個步驟,即“設情以位體”“酌事以取類”“撮辭以舉要”[5]543,把“舒華布實”作為寫文章的程序之一。在劉勰看來,“悅澤”與否關乎文章的成敗,文章的潤色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聲律的使用一定要謹慎。詩歌文章依聲律而作并非劉勰首倡,早在先秦時期,《詩經》的采集者對韻的使用就已經十分清楚,注重用雅正的聲音去歌唱,這是因為文學在產生之初與音樂、舞蹈的結合十分密切,其表現形式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禮樂,追求的是一種“和”或者說“合”的狀態。此后的很多文學作品,在韻方面有意或無意地追求和諧,而嚴格的聲律論直到齊梁時期才由沈約、謝朓等人提出,即“四聲八病”說。“四聲八病”指“平上去入”四種聲調和“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八種毛病。其原則是“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6]在此基礎上,劉勰在《文心雕龍·聲律》篇提出“聲有飛沈,響有雙疊”[5]552,即聲韻分平仄,又分雙聲與疊韻,作文章時聲與韻要“轆轤交往,逆鱗相比”[5]553,反之,文章的聲律就會不和諧。劉勰的聲律論是文章潤色的要素之一,一篇文章的風貌在于韻律的和諧。在聲律的運用過程中需要變換韻腳聲調,但換韻不能太勤,也不能太少,須秉承節制的原則,反復斟酌,“比音切近”,方能產生調和的音律。
其次,重視比興。“比”與“興”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7]在《毛詩序》中這六項又稱“六義”。劉勰對“比”與“興”的解釋見于《文心雕龍·比興》篇。“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5]601劉勰把比與興推崇為詩人表情達意的兩種方法。然而,縱觀先秦至漢魏六朝的文學,自《詩經》以后,作家大多重視“比”而忽略“興”,尤其是漢賦大力使用鋪陳排比的手法,譬喻多而興義少,這種取向直到西晉仍十分盛行,劉勰對此十分不滿。在《文心雕龍》的“文之樞紐”部分,劉勰表達了對儒家傳統的遵循。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深刻影響了他對文學作品風格的認識,《定勢》篇中云:“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5]531文章的勢不一定要依靠豪言壯語、慷慨意氣,而是要做到“文質彬彬”,情感與文辭協調一致。如此,就算是言辭委婉的文章也可以產生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這就要依靠“比興”手法,尤其是“興”,以達到美刺的目的。在使用比興手法時,劉勰認為追求的效果也應當貼切,要使文章達于“和”的狀態。雖然文學到了魏晉已經進入自覺的階段,但劉勰對于“比興”的認識還在朝著“有益政教”的方向發展。
再次,夸張、對偶、用典等修辭手法的運用。《文心雕龍》的《夸飾》《麗辭》《事類》三篇專論文章的夸張、對偶與用典,《諧隱》等篇在寫作過程中也大量使用《周易》《尚書》《爾雅》《禮記》《左傳》《漢書》等中的典故。可見,劉勰對文章的修飾潤色十分重視,并且在寫作中一直踐行。他所追求的是用技巧卻不著痕跡,達于自然之效。如《夸飾》篇中,劉勰推崇《詩經》《尚書》的夸張技巧,不認同司馬相如、揚雄等漢賦家的辭賦,指出夸張一定要合于情理,不能違背事實,理想的效果是“夸而有節,飾而不誣”[5]609。
在具體的文章潤澤過程之中,劉勰認為要“重熔裁,明隱秀”,不能簡單地將所有的寫作技巧堆砌在一起。《麗辭》篇稱:“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5]589技巧的運用要追求自然的效果,也即“和”的狀態,這與道家的“無為”思想達到了高度的契合。老子云“無為而無所不為”[8],其目的不是要人“不為”,而是要因勢利導,做到“善為”。《文心雕龍》開篇便講“原道”,追求文章寫作的自然狀態,以貼近“道”之本原。這看似是要求作家“無術”,實則要求他們“善術”。《總術》篇云:“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5]656言明不能“棄術”,而要“執術”,注意掌握作文之大體,因時乘機,動不失正。總之是要在創作文章時做到潤澤而有節制。
三、劉勰“悅澤”論的時代背景與淵源
劉勰生活在南北朝的齊梁時期,那時中國文學的創作已經進入自覺狀態,同時文學理論的發展也漸趨成熟。文學思潮方面,齊梁時主要有“新變”與“復古”兩大陣營。以裴子野為首的復古派主張文學要師法儒家經典,而以沈約、蕭綱等為首的新變派則表現出對聲律、辭藻等的關注。在文學理論方面,劉勰之前,曹丕《典論·論文》提出不同體裁的文章應該有各異的風格,“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9]158。陸機在曹丕的基礎上對文體及其風格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劃分,“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9]171。陸機在文章的立意與潤色方面主張巧妙妍麗,“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9]172。在《文心雕龍》中,劉勰對虞、夏、商、周到南朝的文學風貌及其產生的原因均有總結評論。他的這些評論集中見于《時序》《才略》二篇,其他篇目亦有提及。在《宗經》篇中劉勰評楚辭和漢賦的特點是“楚艷漢侈”。在《通變》中說:“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5]520在劉勰看來,正是楚辭漢賦造成的“流弊”被魏晉南朝的作家所吸收,才使他們創作的駢體文對形式美的要求極高。
劉勰生活的時代,“文筆之辨”正當熱潮,《文心雕龍·總術》篇中提出的區分“文”與“筆”的原則是:“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5]655這與蕭統的“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10]在表述上雖有差別,但在內蘊上卻達到了一致,他們都強調文章的加工潤色。可見,劉勰所處的時代,偏好文章辭采的華美,作家們對文章的修飾甚至到了繁縟的程度,即便是劉勰,在寫作《文心雕龍》時也難以避免這種風氣的影響。
雖然劉勰與同時代的作家在文章的是否潤色上持有相同的選擇,但劉勰的潤澤觀卻別有一番清麗的風貌。《文心雕龍·宗經》篇中,劉勰主張作文宗經,以達到“情深不詭”“風清不雜”“事信不誕”“義貞不回”“體約不蕪”“文麗不淫”[5]23的效果,以此來正末歸本。劉勰反對的并非是潤色本身,而是要改革自楚騷、漢賦開始形成的艷麗侈靡的文風,以及晉宋以來文人為追求新奇而使用的顛倒字句的方法。他力圖把文學拉回正軌,達于自然的狀態,其潤色觀的特點是取向中和,強調潤澤而有節制。
《物色》篇是《文心雕龍》雜論中的一篇,兼談寫作的方法。全篇論述的是如何用文學來描述自然景色,文章認為《詩經》、楚辭、漢賦都對自然景色有所描摹,《詩經》的語言如“‘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5]693,十分簡約形象;楚辭的語言如“嵯峨”“葳蕤”等開始鋪陳,到了漢賦,辭句則發展到了繁蕪的程度。辭句繁便不珍,抓不住重點,反失了最初的寫作動機,辜負了作者的情志。劉勰的這一主張深受《周易》的影響,《序卦傳》云:“賁者,飾也。致飾然后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1]450此處“飾”通“飭”,含整頓之意。《說文解字注》說:“凡人物皆得云飭。飭人而筋骸束矣,飭物而器用精良矣。”[11]同理,文章需要整飭、加工,但到達極致之后其效果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轉化。所以劉勰對“澤”的理解是建立在對《節》卦卦義的理解基礎之上的。《節》卦卦象為“澤上有水”,本應處于十分和諧的狀態,但如果水過多,就會溢出,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需要加以節制,“安節”則亨,但節制過頭又可能會走向窮途末路,是以“苦節”不可。
《周易》之后,先秦儒家和墨家都對《周易》的“節制”思想進行了深入闡發。孔子及其門生作《十翼》闡釋《易》理,認為《節》卦的根本在于“當位以節,中正以通”[1]346。孔子把天地的“節”引申到社會秩序中,再將之延伸到詩教中,即“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而墨家對“節”的闡釋則更注重于其“節儉”的含義。劉勰的在文學作品的潤色上所持有的節制原則正是受到了儒家之“節”的影響,既不否認與摒棄藝術形式,同時又對齊梁時期詩文潤澤的“訛勢”進行節制改造,表現出對深郁厚篤的藝術風格的追求。《文心雕龍》中有關文章潤色的論述,始終貫穿節制的思想。《情采》篇:“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5]538辭采是輔助表明情理的手段,是文章之“末”而非“本”,文章的“本”應該是情理,濫用辭藻的結果是舍本逐末,弄巧成拙。如此一來,潤澤的關鍵一步就正在于“知止”,要“斟酌乎質文之間,隱括乎雅俗之際”[5]520,以求“文而不侈”。
四、結語
魏晉時期,關于文學應有之樣貌的爭論十分激烈,諸多文學家在文學理論和寫作實踐中都不遺余力地傳播和踐行自己的文學主張,他們或完全走向復古的極端,或為求新而變,以至訛勢。而劉勰因其深厚的儒學功底使得他能兼眾家之理而中庸,結慮司契,垂帷制勝,故而其潤色理論對同時代的裴子野、蕭綱以及后世文學家、理論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