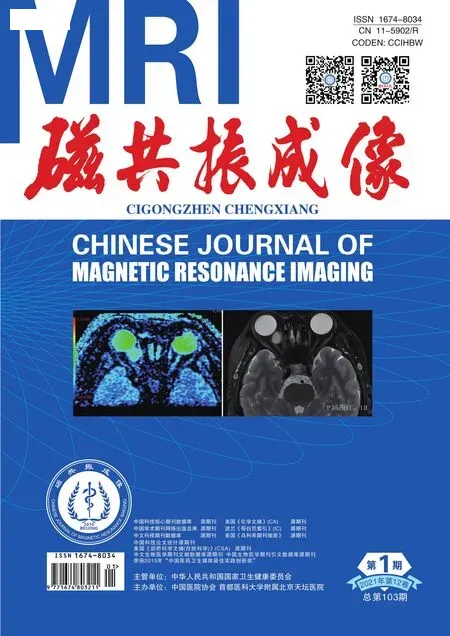DCE-MRI半定量及定量分析在鑒別頸部淋巴結良惡性中的研究現(xiàn)狀
劉宏,張鳳翔,張芳
作者單位:1.內蒙古醫(yī)科大學,呼和浩特010100;2.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中心醫(yī)院影像科,鄂爾多斯017000
淋巴結廣泛分布于全身,其中頸部占比37.5%[1]。炎癥、結核、腫瘤及轉移等因素均可導致頸部淋巴結腫大。在惡性淋巴結中,轉移最為常見,其是否發(fā)生轉移直接影響患者病死率[2],所以早期鑒別淋巴結的良惡性顯得尤為關鍵。目前超聲是淋巴結檢測的首選影像學方法,檢查費用低廉且可以提供淋巴結形態(tài)學信息,但存在一定的假陰性率(15%~26%)[3]。而PET具有最高的準確性,但檢查費用高昂使其難以廣泛應用,而且會導致患者過度治療和治療不足的可能性[4]。動態(tài)對比增強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CE-MRI)可以從微觀層面檢測血流灌注,能夠先于形態(tài)學改變反映組織病理生理狀態(tài)變化。近年來,DCE-MRI在頸部淋巴結性質判定方面的研究逐漸深入,展現(xiàn)出一定的臨床應用潛力。
1 DCE-MRI分析的病理生理基礎
早在20 世紀70 年代,F(xiàn)olkman[5]就提出腫瘤生長和轉移是依賴血管生成的假說。即不論腫瘤遺傳因素如何,新陳代謝需求的增加及組織缺氧決定了腫瘤的生長和轉移都需要新生血管的生成。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由組織缺氧觸發(fā)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過量生產所主導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之間的失衡驅動的。VEGF被認為是病理性血管生成的關鍵介質,其高表達于多種惡性腫瘤中[6]。最新研究表明,半胱氨酰白三烯-2 作為一種獨立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調節(jié)劑,在腫瘤血管中表達明顯增加,以此調節(jié)腫瘤的生長并促進轉移風險[7]。此新生的血管網復雜且發(fā)育不完善,毛細血管粗糙,管腔大小不規(guī)則且走行扭曲,以上因素導致腫瘤微血管通透性顯著增高[8]。高通透性不僅影響腫瘤的生長和轉移,而且影響藥物的遞送。因此,血管通透性代表了癌癥干預治療的新靶點[9]。
惡性淋巴結具有與腫瘤類似的行為,只有具有更多血管生成的淋巴結才能有助于癌細胞在淋巴鏈中擴散進而實現(xiàn)更高的N 分期[10]。惡性淋巴結微血管亦具有高通透性的特點。而良性淋巴結中,由于某種抗原引起的反應性淋巴結增生,增生的濾泡之間的小血管也會增多,但新生血管發(fā)育程度較惡性明顯完善。所以,良性淋巴結在微血管通透性方面即有明顯的差異。而DCE-MRI正通過無創(chuàng)的微血管通透性成像,可以對淋巴結的良惡性做區(qū)分,將陽性預測率提高到89.4~91.2%[3]。
2 DCE-MRI概況
DCE-MRI 屬于MRI 功能成像范疇,是一種以病變微血管系統(tǒng)為生理基礎的成像方法,通過連續(xù)、快速的獲取靜脈內注射低分子釓對比劑前、中、后的T1 加權快速梯度回波圖像,經過計算機軟件的處理,得到一系列分析參數,進而非侵入性地評估病變微循環(huán)和血管通透性情況[11]。與其他MRI 功能序列類似,DCE-MRI 早期研究大多集中于腦部,隨著DCE-MRI 的快速發(fā)展,現(xiàn)已成為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熱點,其應用現(xiàn)已擴展至四肢和體部,在類風濕性關節(jié)炎、前列腺癌、乳腺癌、顱內占位等[12-15]中的應用最為廣泛,包括腫瘤與正常組織鑒別、腫瘤分期、療效評估、腫瘤復發(fā)等方面。現(xiàn)階段,用于DCE-MRI 數據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兩種。
2.1 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根據信號強度-時間曲線得出的多種參數對其強化特點進行描述,半定量分析不涉及藥代動力學模型的應用。常用的半定量參數有對比劑到達時間、達峰時間(time to peck,TTP)、最 大 上 升 斜 率(maximum slope of imcrease,MSI),描述的是時間-強度曲線 (time-intensity curve,TIC)的形狀和構成。半定量分析該種方法開始使用于上個世紀90 年代,因其可以直觀地反映病變的強化特征,所以,在提高腫瘤診斷的敏感度、良惡性腫瘤鑒別、腫瘤分期等方面有較好的應用價值[16-18]。如,Xu 等[16]在利用TIC 曲線鑒別腮腺的良惡性腫瘤中分析到,腮腺惡性腫瘤TIC 曲線在注入對比劑后的第一階段迅速增長,而在下一階段逐漸下降,而良性腫瘤的TIC曲線則呈上升趨勢,其結果表明TIC曲線可以提高區(qū)分腮腺惡性和良性腫瘤的準確性。由此類似地,TIC曲線可應用于淋巴結良惡性的鑒別。半定量分析雖然易于獲得,但易受掃描設備參數、噪聲比等多因素的影響[19]。
2.2 定量分析模型
定量分析可以將血管與細胞間隙之間的對比劑交換做量化分析,評價組織灌注與組織內血管內皮的完整性。定量參數的獲得,依賴于所選擇的藥物代謝模型。為了更準確地分析DCE-MRI 定量數據,現(xiàn)已提出了幾種藥代動力學模型,包括Tofts標準藥代動力學模型,Brix模型和快門速度模型[20]。目前,最常用的是依然是1991年由Tofts等[21]提出的兩室模型,該模型在人類DCE-MRI 數據分析中更準確。兩室模型即血漿為中央室,血管外細胞外體積分數為周邊室,并標準化了三個主要參數[22]。分別為:Ktrans(容積轉運常數)、Kep(速率常數)、Ve(細胞外間隙分數)。Ktrans值代表從血液進入血管外細胞外間隙的對比劑劑量,與微血管生成及血管通透性有關。Ve代表微血管外組織細胞外間隙,提示細胞壞死及細胞化程度,Ve值越大,微血管外組織細胞外間隙容積越大,則細胞化程度低或,細胞壞死程度大。Kep反映單位時間內對比劑回流進入微血管的量,三者的關系為Kep=Ktrans/Ve。為了獲得準確的定量參數,還需測量主要供血血管腔內的動脈輸入函數(arterial input function,AIF),目的是可以減小外在條件對定量參數的影響,使參數更加穩(wěn)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定量參數的獲取比半定量分析相對復雜[23]。近年來,微血管的定量測定越來越多地應用于腫瘤研究。但免疫染色等傳統(tǒng)評價腫瘤血管方法均為有創(chuàng)檢查,且太耗時。DCE-MRI指標與腫瘤低氧有關[24],Wu 等[9]利用DCE-MRI 參數來評估腫瘤通透性,結果顯示,Ktrans與腫瘤血管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有很強的相關性(Pearson R2=0.451,P<0.05)。因此,DCE-MRI 的定量參數Ktrans可以無創(chuàng)地評估血管通透性腫瘤血管微血管密度。而惡性淋巴結具有與腫瘤通透性相似的原理,據此,DCE-MRI定量參數將良惡性淋巴結得以區(qū)分。
3 DCE-MRI在淋巴結良惡性鑒別中的應用
3.1 半定量分析在良惡性淋巴結鑒別中的應用
半定量分析描述的是每個體素或ROI 時間信號強度曲線(time 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的形狀和構成。黎曉萍等[25]在DCE-MRI 結合DWI對頸部淋巴結鑒別的研究中,將TIC曲線分為流入型,流出型,平臺型三型,并以達峰后下降幅度是否≥10%區(qū)分流出型與平臺型,其研究表明,惡性淋巴結以流出型為主(26/44,59.01%),良性淋巴結以流入型為多見(15/26,57.69%);惡性淋巴結MSI 明顯高于良性,良性淋巴結TTP 長于惡性,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滿育平等[26]將TIC曲線按照Yabuuchi 分型分為四型(增加例Ⅳ型,即平坦型),把增強達峰后下降幅度是否大于30%作為界值,其研究表明,良惡性淋巴結TIC-平臺型分別占7.5% (9/120)、53.3% (96/180),以TIC-平臺型為鑒別,兩者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χ2=22.596,P=0.000)。以上表明,惡性淋巴結的TIC曲線多表現(xiàn)為流出型,良性淋巴結曲線更易見于流入型。但Yan等[3]研究中,TIC-流出型在轉移性和良性淋巴結中分別占93.7%和90.3%,兩組之間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527)。最新研究指出,良性LN最常見的是TIC 型IIc(快速流入流出型,54%)。惡性LN 中Ia 型(緩慢流入型,28%)多于Ⅱc 型(24%),二者無明顯的差異[27],與Yan 等[3]的結論一致,即TIC曲線類型不能準確地區(qū)分轉移性淋巴結和良性淋巴結,可能與分型及劃分界定不統(tǒng)一有關。
3.2 定量分析在良惡性淋巴結鑒別中的應用
別克木拉提·馬合木提等[1]探討了DCE-MRI在頭頸部淋巴結良惡性鑒別診斷中的臨床價值,研究結果表明,惡性淋巴結與良性淋巴結兩組間的Ktrans、Ve及Kep數值的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t 值分別為2.897、2.919、2.327;P 值均<0.05)。ROC 曲線的Ktrans、Ve及Kep敏感度分別為100%、88.2%和70.6%;特異度分別為83.3%、50%和83.3%。由此得出結論:DCE-MRI的常用參數Ktrans、Ve及Kep值對頸部淋巴結的良惡性判定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這與Chen 等[28]、Yan 等[3]的結果一致。但Wu 等[29]在多模態(tài)MRI 分析評估宮頸癌的病理特征研究中指出,DCE參數在宮頸癌分期和區(qū)分淋巴結是否轉移中顯示出不一致的結果。Kim等[30]最新研究顯示,對于IB3和ⅡA2子宮頸癌,當僅使用常規(guī)MRI 對淋巴結的短徑難以確定淋巴結狀態(tài)時,Ktrans似乎是檢測轉移性淋巴結的有用參數。但轉移性淋巴結與非轉移性淋巴結之間的Ve值無顯著差異。并認為,Ve值與淋巴結的不同轉移階段有關,在早期,癌細胞的增殖超過壞死。癌細胞增殖逐漸擴大,由于血流量減少,淋巴結內部發(fā)生了微壞死,增加了間隙。由此,轉移性和非轉移性淋巴結之間的Ve值發(fā)生變化。Vidiri等[31]利用直方圖分析口咽癌的DCE-MRI 參數和18F-FDG PET 值的相關性來評估原發(fā)腫瘤和轉移性淋巴結。文章指出,在轉移性淋巴結中,所有Ktrans百分位數均與SUV(標準攝取量)值密切相關,KtransP90也與TLG(糖酵解總量)相關。
4 DCE-MRI在淋巴結轉移與分期中的應用
癌細胞可以通過淋巴途徑轉移,一旦侵入受累淋巴結,就可以通過血源途徑增殖并獲得向遠處擴散的能力,這依賴于淋巴管與血管系統(tǒng)的高內皮靜脈分子交換[32]。腫瘤N 分期反映淋巴結轉移的程度和范圍。Chawla 等[2]在利用DWI 與DCE-MRI聯(lián)合的方式,來評價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患者遠處轉移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低分化的HNSCC比中分化的HNSCC高Ktrans的趨勢,即分化較差的HNSCC 中的血管通透性較高,故提出DCE-MRI可能有助于預測HNSCC的遠處轉移。Huang等[10]等利用DCE-MRI 分析了鼻咽癌患者淋巴結轉移與分期的相關性,其研究共納入26例患者,結果顯示,N期患者的Ktrans差異顯著(N1,n=3;N2,n=17;N3,n=6),P=0.015。N1,N2 和N3 的中值(范圍)為0.24 min-1(0.17~0.26 min-1),0.29 min-1(0.17~0.46 min-1)和0.46 min-1(0.29~0.70 min-1)。文章指出,轉移性淋巴結中Ktrans反映的血管通透性增加與N 期呈正相關。Bontempi 等[33]在利用DCE-MRI 異質增強模式探討健康小鼠體內正常淋巴結形態(tài)的實驗研究中指出,正常淋巴結中DCE-MRI顯示出特征性的異質性模式,可以區(qū)分淋巴結的周邊和中央部分。并提出此種模式可以作為淋巴結分期的診斷標志物進行研究。
5 總結與展望
DCE-MRI 作為一種新的MRI 功能成像技術,能早于形態(tài)學改變之前,從微觀上反映病變的本質。但仍存在一些問題:(1) 缺乏獨立驗證以及存在掃描序列之間的技術差異,限制了DCE-MRI的臨床適用性[34];(2) DCE-MRI一個重要限制是缺乏標準化,如對比劑注入及后處理算法,導致研究結果在各中心之間的可比性有限[27]。隨著DCE-MRI的不斷發(fā)展,及多中心、多模式的聯(lián)合應用,以期為臨床診療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