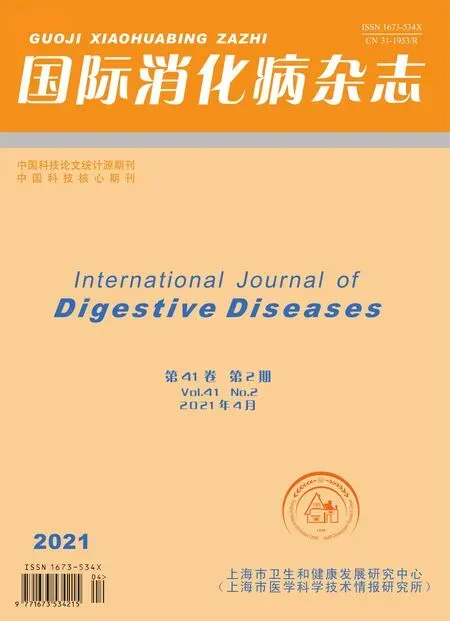鼠李糖乳桿菌GG防治消化系統疾病的研究進展
劉靜華 李 靜 周國瓊 曹海龍 王邦茂
鼠李糖乳桿菌GG(LGG)是一種常見的益生菌,最早由Goldin和Gorbach在20多年前從1位健康成年人的糞便樣本中分離出來,具有耐胃酸、耐膽汁鹽、耐多種抗生素等生物學特點,體內研究表明LGG在人類胃腸道中具有良好的黏附及定植能力。目前LGG已成為研究較廣泛的益生菌之一,其對于胃腸道的保護作用可能涉及的機制包括增強腸道屏障功能,提高對腸黏膜的附著力,抑制病原體的黏附,競爭性排斥病原微生物,產生抗菌素樣物質,調節機體免疫系統等,可用于預防和治療各種胃腸道微生態失調相關疾病[1]。本文就LGG防治消化系統疾病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幽門螺桿菌感染
幽門螺桿菌(Hp)感染是慢性胃炎及胃癌的危險因素,據調查顯示中國不同人群中Hp感染率為42%~84%[2],根除Hp對于多種消化系統疾病的治療極為重要,在根除Hp治療中,腹脹、腹瀉和味覺障礙是抗生素治療期間常見的不良反應。一項針對成人的研究結果顯示,LGG能顯著降低上述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提高治療耐受度[3]。在另一項包括25項隨機對照試驗共3 769名參與者的薈萃分析中,同時對接受根除Hp治療的成人和兒童進行比較分析,結果表明LGG可降低Hp根除治療中抗生素應用引起的腹瀉發生率[4]。
2 急性感染性腹瀉
引起急性感染性腹瀉(AID)的病原體包括病毒(如輪狀病毒和腺病毒)、細菌(如沙門氏菌屬、大腸桿菌致病菌株、小腸結腸炎耶爾森氏菌和艱難梭菌)、寄生蟲(如藍氏賈第鞭毛蟲和小隱孢子蟲)和真菌等。
腸道微生態失衡不僅可能是成人AID的誘因,也可能是其結果。由腸道益生菌組成的活性微生物制劑不僅對人體健康有益,還可以治療腹瀉,其機制可能包括:(1)對黏膜的黏附作用及腸道通透性正常化LGG編碼的基因組能夠合成一種特殊的菌毛,這種菌毛在黏附腸上皮細胞和促進生物膜形成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5];(2)抗菌作用LGG能產生相對分子質量<1 000的細菌素,具有蛋白酶抗性和熱穩定性,從LGG條件培養基中可以分離得到7個肽段,具有抗革蘭陰性菌和革蘭陽性菌的殺菌活性,LGG的菌毛與黏液結合可阻止潛在病原體與宿主結合,從而預防和治療耐萬古霉素腸球菌(VRE)感染;LGG含有凝集素樣蛋白-1和凝集素樣蛋白-2,可抑制沙門氏菌、大腸桿菌等病原體[6];(3)產生有益的蛋白活性物質,以減少腸道上皮細胞凋亡,保持細胞骨架的完整性;(4)免疫調節作用LGG具有積極的免疫調節作用,能升高抗輪狀病毒抗體免疫球蛋白G的表達[7]。
服用益生菌不僅能縮短兒童急性腸胃炎(AGE)的持續時間,還可降低疾病嚴重程度,且LGG對于AID的作用可隨著服用劑量的增加而增強[8]。Szajewska等[8]對15項隨機對照試驗共2 963名參與者進行Meta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一般支持治療,LGG能較快緩解受試者的腹瀉癥狀,且大劑量LGG(>1×1010CFU)比小劑量的效果更顯著,平均可縮短腹瀉時間1.1 d。此外,該研究還發現LGG對輪狀病毒引起的腹瀉的治療效果尤佳。
3 旅行者腹瀉
導致旅行者腹瀉(TD)的病原體以細菌多見,常見的是大腸桿菌腸毒性ETEC株,其他包括彎曲桿菌、志賀氏菌和沙門氏菌,此外,輪狀病毒也是常見病原體。有報道指出,在出發前2 d給予受試者LGG膠囊并持續整個旅行,對于47%的受試者可起到預防腹瀉的作用[9]。
4 抗生素相關腹瀉
抗生素相關腹瀉(AAD)的發病率與使用的抗生素、流行病學環境和宿主有關,成年人AAD的發病率為5%~39%。誘發AAD的常見抗生素包括氨芐青霉素、阿莫西林、頭孢菌素和克林霉素等。這些藥物可打破腸道微生態平衡,導致對上述制劑耐藥的細菌增殖,如艱難梭菌、A型產氣莢膜梭菌、金黃色葡萄球菌、沙門氏菌和念珠菌。益生菌可以通過調節腸道中的微生物群平衡來預防和治療AAD。McFarland[10]的薈萃分析指出,布拉氏酵母菌、LGG及益生菌混合物均可顯著降低AAD的發生率。一項納入了12項隨機對照試驗共1 499名參與者的薈萃分析表明,LGG在預防成人AAD方面有效[11]。Blaabjerg等[12]的薈萃分析包括了17項隨機對照試驗共3 631名參與者,結果發現使用益生菌,尤其是LGG和布拉氏酵母菌,有利于門診患者AAD的預防。以上研究提示,LGG與抗生素聯合使用可降低AAD的發病風險。
艱難梭菌是AAD常見的病原菌,艱難梭菌相關腹瀉(CDAD)多見于接受廣譜抗生素治療的老年患者或住院患者,頭孢菌素、氟喹諾酮類、青霉素和克林霉素等藥物與CDAD的高發病率有關[13]。其他引起CDAD的危險因素包括使用質子泵抑制劑、H2拮抗劑、甲氨蝶呤,以及胃腸道基礎疾病。有研究表明應用益生菌可使CDAD的發病率降低60%左右[14-15]。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益生菌在CDAD的一級預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CDAD的發病率呈快速增長趨勢[16],目前單獨應用LGG治療CDAD的研究較少,今后需進一步探究LGG預防CDAD的效果及相關機制。
5 功能性胃腸病
微生物群、腸道和大腦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作用。腸內細菌可能通過神經、內分泌或免疫活動調節內臟疼痛反應。益生菌在調節腸易激綜合征(IBS)和中樞介導的腹痛綜合征的內臟痛覺方面可能發揮重要作用[17]。一項包括3項隨機對照試驗共290例患兒的薈萃分析指出,LGG能夠改善腹痛程度,有助于治療與腹痛相關的功能性胃腸病(FGID)患兒,尤其是IBS患兒[18]。
5.1 IBS
IBS的發病機制較復雜,可能與遺傳、性別、腸道動力因素、腸道炎性反應、腸道菌群失調、飲食習慣、應激、內臟敏感性、腦-腸軸和腦腸肽等有關。
Han等[19]的研究表明應用LGG預處理可以阻止IBS患者糞便上清液引起的細胞通透性變化,對腸上皮屏障功能起保護作用。但有關益生菌治療IBS的研究常呈現矛盾的結果,且不同菌株的治療效果不同,這可能是由于宿主特異性的差異造成的,宿主特異性可能是益生菌的選擇標準之一。Pedersen等[20]研究了低發酵、低聚糖、雙糖、單糖、多元醇飲食(LFD)和益生菌LGG對IBS的影響,對符合羅馬Ⅲ診斷標準的123例IBS患者進行為期6周的治療,結果顯示LFD和LGG對IBS均有較好的療效。Capurso[1]總結了近年來LGG在IBS臨床試驗中的應用情況,包括LGG的單獨應用及其與其他益生菌的聯合應用,結果顯示雖然LGG被認為適用于治療IBS,但LGG單獨應用不能顯著改善IBS癥狀;對于腹瀉型IBS患者,應用LGG能夠改善糞便性狀。目前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較少,且由于IBS患者的異質性和多變的自然病程,限制了臨床試驗的設計及觀察,未來亟需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證據。
5.2 便秘
益生菌對成人便秘有效,但多數研究均未發現其可改善兒童便秘。Banna等[21]和Korterink等[22]研究了益生菌對排便相關FGID的治療效果,結果表明LGG、LactobacilluscaseiDN114 001和BifidobacteriumlactisDN173 010對排便相關FGID均無顯著影響。目前研究顯示某些特定益生菌對成人便秘有效而對兒童無效,其具體機制尚未闡明,可能與成人和兒童的便秘病因不同有關。
6 炎癥性腸病
炎癥性腸病(IBD)患者腸道存在菌群失調,其特征為某些優勢共棲成員(如梭狀芽孢桿菌)的多樣性和豐富度下降,而有害病原菌增高。IBD患者腸道菌群組成改變主要包括厚壁菌門減少和變形桿菌增多,這種菌群失調可能通過增強宿主的炎性免疫反應而參與IBD的發病機制。益生菌治療IBD患者的機制可能與競爭性抑制病原體、刺激免疫反應、增強腸道屏障活性和誘導T細胞凋亡有關[1]。
一項雙盲研究將187例靜止期UC患者隨機分為3組,其中65例接受LGG18×109CFU/d,60例接受美沙拉嗪2 400 mg/d,62例接受LGG聯合美沙拉嗪治療。結果顯示,3組患者在治療第6個月、第12個月時的復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在延長復發時間方面,LGG治療組似乎比美沙拉嗪標準治療組更有效[23]。另一項臨床試驗給予CD患者口服LGG10 d,結果顯示特定抗體分泌細胞β-乳球蛋白表達顯著升高,提示口服LGG具有增強腸道IgA免疫功能的潛力,從而可增強腸道免疫屏障[24]。
7 消化系統腫瘤
LGG(ATCC53103)是早期被研究用于腫瘤治療及預防的益生菌之一。一項薈萃分析總結了近年來LGG在腫瘤相關胃腸道疾病中的報道,結果指出LGG能夠逆轉腸道失調和中度腹瀉,可減輕與腫瘤發展相關的慢性炎性反應[21]。
Linsalata等[25]將胃癌細胞(HGC-27)置于LGG勻漿中,觀察到隨著時間延長,細胞酶活性及多胺聚合物含量逐漸降低,提示LGG可以抑制胃癌細胞增殖。另有研究指出,LGG可以有效降低Hp誘導的白細胞介素-8(IL-8)的產生及其對胃腺癌細胞(AGS)的附著力[26]。
Orlando等[27]將維生素K1和LGG聯合應用于3種結腸癌細胞(Caco-2、HT-29和SW480),結果顯示其促凋亡作用顯著,尤其是對于Caco-2細胞。Lopez等[28]發現鞭毛蛋白可以使結腸癌Caco-2細胞中的IL-8表達升高17倍,而應用活的LGG和紫外線滅活的LGG處理可以抑制IκB的降解,從而阻止轉錄因子移位,抑制IL-8的表達。Escamilla等[29]應用LGG處理轉移性結腸癌HCT-116細胞,發現可使ZO-1表達升高,并降低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表達,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浸潤。上述研究提示,LGG可通過降低MMP-9的表達、抑制IκB的降解、升高IL-8和ZO-1的表達水平,從而降低腫瘤細胞的浸潤和侵襲轉移能力。
在1996年已有研究表明LGG可以減弱致癌物質的致突變作用[30]。Gamallat等[31]的研究發現,LGG能促使1, 2-二甲基肼(DMH)誘導的結腸癌大鼠細胞凋亡,提示LGG可能通過抑制血管生成及炎性蛋白表達,在腫瘤預防中發揮作用。
8 慢性肝病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發病率呈升高趨勢,該病可進展為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NAFLD的發生可能與腸道菌群的異常生長、腸道通透性的增加、腸道滲漏、小腸細菌過度生長(SIBO)有關,SIBO通過腸源性脂多糖(LPS)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誘導肝損傷。益生菌不僅能夠減少細菌移位,減輕病原菌對上皮細胞的侵襲,還可阻止細菌附著于黏膜上,促進抗菌肽產生,并可以減輕炎性反應,刺激宿主免疫,提示益生菌可用于慢性肝損傷的防治。動物實驗表明,LGG可通過升高益生菌含量、保護腸道屏障功能、降低腸道通透性,抑制NAFLD模型小鼠和酒精性肝病(ALD)模型小鼠的肝損傷[32-33]。
NAFLD是一種與肥胖相關的疾病,目前對于NAFLD的治療重點集中于運動和減肥方面。部分藥物如二甲雙胍、他汀類藥物、吡格列酮、熊去氧膽酸等也被用于治療NAFLD,但上述方法均存在局限性,不能被廣泛使用。益生菌相對容易獲得,且成本較低,目前尚未發現嚴重的不良反應,是一種具有廣泛應用前景的慢性肝病治療方法。
9 展望
LGG被認為是一種經典、安全、有效的益生菌菌株,其在預防和緩解各種類型的腹瀉、慢性肝病、消化系統腫瘤、Hp感染、部分FGID中發揮一定的作用,而其在IBD等其他消化疾病中的廣泛應用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量,細化對細菌劑量、劑型、菌株及實驗持續時間等變量的選擇,從而指導臨床的合理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