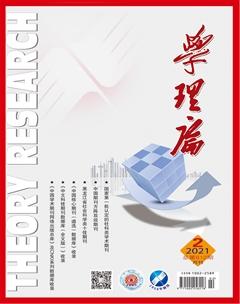唯物史觀視域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闡釋
朱怡初
摘 要:自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備受關(guān)注。它是一種政治哲學(xué),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和馬克思唯物史觀緊密相連,從舊唯物主義到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和經(jīng)濟(jì)全球化以及文化全球化伴隨世界歷史的進(jìn)程而發(fā)展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之間的關(guān)系,對于更進(jìn)一步順應(yīng)全球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更好地推動經(jīng)濟(jì)全球化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關(guān)鍵詞:唯物史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經(jīng)濟(jì)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02-0042-03
馬克思出生在富裕的律師家庭,但他對德國人民所遭遇的苦難現(xiàn)實感同身受,并致力于解決德國現(xiàn)實問題,積極求索,在馬克思恩格斯不斷的研究和學(xué)習(xí)中,創(chuàng)立了唯物史觀。站在唯物史觀的視角審視社會歷史和社會運動,全球化理論和唯物史觀給社會變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dǎo)。
結(jié)合中國社會發(fā)展情況和當(dāng)代世界發(fā)展形勢,2012年,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2015年,在聯(lián)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習(xí)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系統(tǒng)論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提出以來就備受各國廣泛關(guān)注。
將馬克思的全球化理論以及唯物史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結(jié)合,以唯物史觀的視角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yīng)全球化發(fā)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源源不斷的鮮活血液。
一、從舊唯物主義到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xué)立場的確立
馬克思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條中提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1]54-57它以“立腳點”為視角指出新舊唯物主義之間的概念差異。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是對“對象、現(xiàn)實、感性”以感性直觀理解,是形而上學(xué)的,不立足實踐活動發(fā)生能動作用。而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從主體方面去理解,把它們都當(dāng)作“現(xiàn)實世界”中的感性活動來理解,從實踐的角度能動地發(fā)展人的感性活動,從社會關(guān)系的角度理解人的實踐活動,展現(xiàn)出其以“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為立腳點的理論特質(zhì)。“市民社會”和“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是新舊唯物主義劃分依據(jù),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政治哲學(xué),是為全人類提出的理念,是超越以往的、能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和諧相處的共同體。與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對單個人的感性直觀抽象的發(fā)展相背離,與“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從實踐和社會的關(guān)系發(fā)展人的感性活動思想主線一致。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哲學(xué)立場基于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
二、世界歷史演進(jìn)與社會形態(tài)更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理解深化
(一)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新航路的開辟,使殖民者看到了一個新世界,這標(biāo)志著殖民時期的到來。資本主義的殖民擴(kuò)張時期,資本邏輯以強(qiáng)盜的方式打破了各國間的貿(mào)易壁壘,社會的巨大變革使殖民地的人們過上了長達(dá)幾個世紀(jì)被侵略者像豬羊一樣宰割的殖民奴隸生活,殖民地土著的無知和不開化、半開化招致目的性極強(qiáng)的殖民者為所欲為。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瘋狂掠奪使殖民者本國經(jīng)濟(jì)和殖民地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呈對立面拉開差距,經(jīng)濟(jì)發(fā)生了變化,政治也隨之發(fā)生了相應(yīng)變化,直到民族解放運動興起,殖民主義才退出歷史舞臺。隨之而來的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全球化,資產(chǎn)階級不斷滋長的利益迫使他們競相追逐,不顧一切野蠻侵占,無原則地擴(kuò)張,掠奪全球一切資源,他們用到處掠奪的資源進(jìn)行生產(chǎn),又到處傾銷產(chǎn)品,正如馬克思寫到的,“不斷擴(kuò)大產(chǎn)品銷路的需要,驅(qū)使資產(chǎn)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fā),到處建立聯(lián)系。”[2]404資產(chǎn)階級以擴(kuò)張的方式打破了各民族之間的隔閡,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世界處于一個“共同體”內(nèi)。在資本主導(dǎo)下,這種“共同體”以金錢和利益至上為主流,是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對多數(shù)勞動者的壓榨,人與人之間呈剝削和被剝削的關(guān)系,階級分化明顯。
資本的異化進(jìn)一步加劇資產(chǎn)階級和勞動者之間的矛盾,社會分化為兩個階級,以不勞而獲為主的資產(chǎn)階級和以大多數(shù)工人為代表的無產(chǎn)階級。實踐活動中的不對等不公平和“市民社會”中的“私人利益的體系”性質(zhì)一樣。世界市場形成下資本逐利的“共同體”社會形態(tài)和市民社會中流于形式的普遍“共同體”社會形態(tài)互為表里,正如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指明的,作為精神特殊性的客觀法“在市民社會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從精神中產(chǎn)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財富上、甚至在理智教養(yǎng)和道德教養(yǎng)上的不平等。”[3]所以市民社會具有階級性,隨著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擴(kuò)展和深入,市民社會的等級性結(jié)構(gòu)也隨之嵌入到“世界市場”的范圍內(nèi)。隨同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起來的“真正的市民社會”內(nèi)在地要求殖民擴(kuò)張,現(xiàn)代世界的市民社會不可能只是一國之內(nèi)的自由市場社會,伴隨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打破地理隔閡,超越以往一切局限的市民社會走向世界。資產(chǎn)階級的市民社會理論為其加大對工人的剝削這一狡黠“吃相”推脫了罪責(zé),裹上了一層“合理”的外衣,經(jīng)濟(jì)壓榨和政治剝削使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愈演愈烈,資本家的貪婪,利益“蛋糕”分配的極大不公平加速了無產(chǎn)階級反抗資產(chǎn)階級的進(jìn)程,壯大了無產(chǎn)階級隊伍的力量,催生了社會變革新生政權(quán)的產(chǎn)生,國家形態(tài)、世界大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資本主導(dǎo)下的強(qiáng)盜邏輯激化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的矛盾,無產(chǎn)階級進(jìn)行革命活動奪取政權(quán)建立新生政權(quán),實現(xiàn)全人類解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是包容整體思維和維系天下情懷的多元文化觀念,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和經(jīng)濟(jì)剝削,也不是市民社會維護(hù)私利和分出階級為統(tǒng)治者服務(wù)的理論,主張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和無產(chǎn)階級實現(xiàn)全人類解放的思想相一致。
隨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資本主義裹挾著資本邏輯進(jìn)入現(xiàn)代文明,社會結(jié)構(gòu)以資本為運行中介,在資本邏輯主導(dǎo)下,霸權(quán)主義和強(qiáng)權(quán)政治應(yīng)運而生,企圖操縱世界經(jīng)濟(jì),妄圖整個世界發(fā)展都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并極力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所謂的“普世價值”就是指西方價值。西方社會所倡導(dǎo)的“普世價值”其實并不“普世”,而是基于資本邏輯的、反映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包藏西方國家利益的地域性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僅不是以人類社會為觀照主體,反而置民族國家利益或地域性利益于國際社會的公共性需求之上,本質(zhì)上與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產(chǎn)生沖突和對立關(guān)系。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構(gòu)建與人類社會、社會化人類相適應(yīng)的新型價值觀為目的。這種新型價值觀徹底擺脫資本邏輯,體現(xiàn)出對全人類整體命運的關(guān)注,具有深厚的人類情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共善”的共同體,不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為了生存不一定需要超越和對立,可以是和諧共生、天下大同的大局觀。縱觀現(xiàn)今,經(jīng)濟(jì)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世界呈多極化發(fā)展趨勢,世界各國經(jīng)濟(jì)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也伴隨很多國際沖突,機(jī)遇和挑戰(zhàn)并存。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為了解決世界發(fā)展進(jìn)程中國際形勢的突出問題、世界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突出問題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會推動世界歷史前進(jìn)的向好態(tài)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也凸顯其價值地位和美好生活理念。
(二)文化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馬克思認(rèn)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xué)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xué)。”[2]404文學(xué)是一定民族和地域范圍的人們經(jīng)過長期社會實踐形成的,民族和地理界線被打破,就會擴(kuò)大人與人的交往圈層,在人與人相互往來中促進(jìn)其文化層面的交流,那么文學(xué)也就不再是什么隱晦的了。文學(xué)資源更多,跨越了地理和時空界限,各民族的文學(xué)也就相應(yīng)成了公共的資源。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下文化也全球化,產(chǎn)生了文化總的交集融合,文化打破孤立狀態(tài),各國相互借鑒學(xué)習(xí),一種“世界文學(xué)”就這樣出現(xiàn)了。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將目光放眼全世界,隨著世界歷史的逐步形成,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公開化、透明化、共享化的特點,成為全球化共享的資源。總體全球化的推動力首先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上,其次是在文化上。文化全球化相當(dāng)于是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附加品,經(jīng)濟(jì)和文化的總體過程形成總體全球化,是唯物史觀的時代特征,開拓人類的世界視野,增強(qiáng)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類共識。
西方學(xué)者S.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jīng)濟(jì)來劃分的集團(tuán)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tǒng)一的力量。”[4]7他認(rèn)為當(dāng)代全球化完全是文化全球化,這種觀點摒棄了生產(chǎn)力是推動社會發(fā)展的決定力量,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精神層面置于當(dāng)代全球化發(fā)展的主體地位。在人類歷史演進(jìn)中,社會發(fā)展永遠(yuǎn)立足生產(chǎn)實踐,經(jīng)濟(jì)全球化仍然是重要的推動力之一,文化全球化永遠(yuǎn)居于次要地位。享廷頓指出當(dāng)代全球化的重要一維即文化之維,這是總體全球化的重要維度。總體全球化中的文化全球化是一個中性概念,中性概念在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含義,導(dǎo)致不同的態(tài)度和結(jié)果。當(dāng)前,文化全球化被理解為西方文化的全球普及,賦予西方的文化“殖民”特色。人們自然不接受這個說法,拒斥文化全球化,歪曲文化全球化的原意。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的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價值乃至意識形態(tài)的大眾滲透,它是指在總體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逐漸形成的普遍的、整體的、共同的文化理念、文化觀念、文化價值和文化認(rèn)同,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代全球化應(yīng)當(dāng)被理解為包括經(jīng)濟(jì)和文化雙重維度的更加完整的總體性全球化,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要充滿文化自信,摒棄質(zhì)疑和懷疑的眼光,任何文化都不能獨大、取代、占有,不搞文化霸權(quán)、文化兼并、文化融合,任何文化都有話語權(quán)。也就是說,在文化的交流與互動中,我們應(yīng)當(dāng)持開放的態(tài)度,應(yīng)當(dāng)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豪感。
如果不囿于社會主義的種種具體規(guī)定,我們看到,從《共產(chǎn)黨宣言》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這種共同體精神均始終貫穿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歷史階段。換言之,在當(dāng)代全球化背景下,蘊含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中的人類共同價值已經(jīng)具備了形成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基礎(chǔ)上,隨著人類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打破各民族文化隔絕性的“世界文學(xué)”逐漸形成,深刻理解文化全球化的指向就能深刻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理念和價值,綜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人類共同價值就具備了形成的條件。
三、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意義
(一)對馬克思?xì)v史唯物主義的繼承與發(fā)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表述契合馬克思創(chuàng)作《共產(chǎn)黨宣言》的初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和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和全球化下的時代體現(xiàn),是理論和現(xiàn)實的交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開辟,意味著消解各國互相防范、互相競爭的利益隔閡,打破為生存而筑起的高高聳立的心理壁壘,澆滅一切矛盾的引燃點。這一原則縮小了全球化初期的矛盾斗爭對立格局,同時也為全球化進(jìn)入一種正面的軌道開辟了良性道路,為人類的生存、發(fā)展、幸福開創(chuàng)了美好前景。
(二)推進(jìn)馬克思共同體演進(jìn)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fā)展理念和全球化的不斷上升發(fā)展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化發(fā)展,全球化發(fā)展增強(qiáng)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性。解決唯物史觀全球化問題初期即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消極發(fā)展,在全球化發(fā)展中深入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nèi)涵精髓和時代妙用,又以實踐方案之力推動全球化發(fā)展的同時,自身也在積極構(gòu)建發(fā)展,它不是制度發(fā)展模式,也不是全球性的理念擴(kuò)張,更不是搞“新殖民主義”擴(kuò)張,也不是在主導(dǎo)國際領(lǐng)導(dǎo)話語權(quán),只是同人類追求和平發(fā)展的時代以及和諧美好生活的愿望一樣一同促進(jìn)時代發(fā)展,促進(jìn)自身理念發(fā)展。它起源于馬克思唯物史觀,植根于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實踐于現(xiàn)今全球化發(fā)展,并且對未來的理論給出預(yù)示,是未來理論創(chuàng)新的參照概念。《共產(chǎn)黨宣言》鄭重宣告:“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chǎn)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5]66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是天下大同的世界觀,是沒有階級、國家消亡的共同體,是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未來命運的思想和方法論基礎(ch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也是當(dāng)今世界的實踐理論,更是通向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的價值旨?xì)w。
(三)全球化發(fā)展的更高生存智慧
現(xiàn)今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區(qū)別引發(fā)的變化表現(xiàn)為發(fā)達(dá)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也表現(xiàn)為平等和不平等,經(jīng)濟(jì)和政治上的強(qiáng)行不公的做法被話語權(quán)表述得合情合理。在貿(mào)易、技術(shù)、金融等領(lǐng)域,反映了世界體系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矛盾的深刻性和尖銳的利害沖突。發(fā)達(dá)國家是種種不合理做法的主動發(fā)起者,發(fā)展中國家是種種不合理做法的被動承接者。發(fā)達(dá)國家以近代歷史發(fā)展為借口,提出種種不合理、混淆是非的特殊要求,既想本國超強(qiáng)發(fā)展又想干涉別國發(fā)展,還想在國際中有很多優(yōu)待權(quán)。但是發(fā)展中國家也意識到危機(jī),一直努力發(fā)展自身。當(dāng)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gòu)建,正是打破不平等壁壘,消除經(jīng)濟(jì)和政治方面的隔閡,促進(jìn)人類社會的共同發(fā)展和進(jìn)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觀旨在解決國際政治大變革、大動蕩,維護(hù)國際、國家、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以國際主義精神規(guī)范的道德解決全球性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大變革中出現(xiàn)的危機(jī)。貿(mào)易戰(zhàn)、局部沖突、排外主義、霸權(quán)主義、強(qiáng)權(quán)政治等等是近年來的國際沖突,究其原因也是經(jīng)濟(jì)全球化帶來的國與國、地區(qū)與地區(qū)的利益沖突,各國應(yīng)該互相尊重,每個國家都享有選擇道路、制度、發(fā)展方式的權(quán)利,也有決定權(quán),不能抱有偏見,恃強(qiáng)凌弱。每個國家都要遵守人道主義國際精神,自身發(fā)展道路有自己特色,大國強(qiáng)國不能強(qiáng)行要求他國制度選擇和發(fā)展模式和自己一樣,不然就會帶來不利沖突,危害他國發(fā)展。在相互依賴的全球化時代,發(fā)達(dá)國家的發(fā)展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是互相映襯互相依托的,各國在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外貿(mào)、技術(shù)方面都要和諧相處,發(fā)展本國的同時兼顧他國利益。“要建設(sh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意義”[6]。消解各種國際沖突,用更高的生存智慧共建人類美好明天。
(四)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
《共產(chǎn)黨宣言》闡釋了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無產(chǎn)階級解放學(xué)說和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階級最終消亡,人類最終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站在人的立場上實現(xiàn)人的發(fā)展,經(jīng)濟(jì)全球化是人與人、人與社會在歷史演進(jìn)中交叉碰撞出的產(chǎn)物,經(jīng)濟(jì)全球化勢不可擋,它不是制度模式和方法論,但卻從資本主義擴(kuò)張那一刻就推動世界變革,是歷史發(fā)展的客觀必然性,社會主義只有在世界歷史進(jìn)程中,才能不斷發(fā)展并獲得勝利,才能建設(shè)人人共享的美好生活。以人為對象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吻合。
四、結(jié)語
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創(chuàng)立的全球化理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論前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和時代化運用。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其理論生命的延續(xù)和深化。
參考文獻(xiàn):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劉同舫.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8(7):4-21,204.
[4]S.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張雷聲.唯物史觀視野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12):29-37,161.
(責(zé)任編輯:姚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