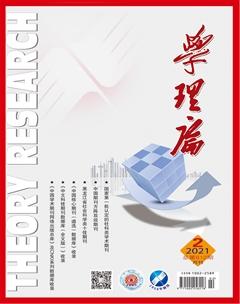霍克海默社會批判理論研究
張新朋
摘 要:霍克海默的社會批判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補充,是實踐批判原則在意識形態(tài)批判中的運用。霍克海默基于辯證哲學方法,由反對形而上學的體系出發(fā),一方面批判唯心主義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而抽象地談論理性,另一方面批判唯物主義機械地把理性看作是某種物質(zhì)本原的附屬品。這種內(nèi)容與形式看似沖突的批判,恰恰是其“開放的辯證法”的體現(xiàn)。既可以克服唯心主義的理性批判的脫離實際的弊病,又能避免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批判的僵化。霍克海默在否定和批判意義上的“社會批判理論”,用以清除意識形態(tài)遮蔽,并試圖突破和超越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的感性意識。而理性究竟如何恢復其獨立自主性,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霍克海默;社會批判理論;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意識形態(tài)批判;實踐批判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02-0045-03
法蘭克福學派是1923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內(nèi)成立的一個由左派知識分子組成的,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多學科綜合性研究與批判為主要任務的哲學社會學學派。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主要代表,霍克海默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簡單回歸,即從自我意識立場出發(fā)的理性批判,而主要是遵循實踐批判原則的指向,即揭示生活世界自身的批判維度。霍克海默對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狀況本身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zhì)進行批判,目的是消除生活世界中的意識形態(tài)遮蔽,以此來探索新的感性意識出現(xiàn)的可能性。
一、霍克海默社會批判理論體系的脈絡
霍克海默對理性的批判開始于1934年他所寫的《關于現(xiàn)代哲學中的理性主義爭論》。霍克海默站在唯物主義立場,批判現(xiàn)代哲學史上自笛卡爾以來的理性主義的唯心主義實質(zhì)。霍克海默批判地指出:“在實際上,認識的每一步都依據(jù)純邏輯以外的許多前提條件。”[1]130除此之外,還包括社會階級斗爭和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關于社會的活生生過程的理論是一種最廣泛的思想建設過程,這個理論必須考慮到處處決定著社會階級的特征及由此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的全部物質(zhì)和精神的條件。”[1]146但是,他同時也強調(diào)他的唯物主義原則的反形而上學的特點:“辯證唯物主義并不把主體再次理解成諸如人的本質(zhì)那樣的一種抽象物,而是時時把它理解成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中的人。”[1]145這種唯物主義理論反對尋求一種不變的、作為“實體”的世界本原。
1937年在《傳統(tǒng)理論與批判理論》中,霍克海默第一次正式使用“批判理論”這個概念,并強調(diào)其批判理論是一種“新型的唯物主義”,特點是“把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所提出的任務”作為研究的主題,并為此而“在總體性中考察社會的發(fā)展趨勢”。霍克海默指出,由于人類理性已經(jīng)被統(tǒng)治階級所濫用,作為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工具,因此,他的批判理論以批判理性作為基本任務。這種批判的立足點是為了消除理性所制造的種種意識形態(tài)“幻想”,如科學、文化、理論、技術(shù)等。霍克海默繼承了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并用黑格爾關于異化的觀點,進一步加以綜述。到1947年發(fā)表《理性的消蝕》和《啟蒙辯證法》時,批判理論采用“批判的理想主義”的形式,集中地批判作為現(xiàn)存不合理社會的支柱的“不合理的理性”。
依據(jù)馬克思的“實踐批判”原則,物質(zhì)生活領域是最基礎的領域,是歷史運動和變化的根源所在。而作為基礎領域的觀念表達的意識形態(tài)并不具有革命性,真正的革命動力在物質(zhì)生活關系這一感性基礎領域之中。“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zhì)力量只能用物質(zhì)力量來摧毀”[2]。所謂“武器的批判”就是實踐批判,只有實踐批判才具有現(xiàn)實的力量,才能摧毀舊世界建立新世界。霍克海默講到批判理論的主體是處在現(xiàn)實歷史運動和真實生活實踐中的主體,批判理論對于批判的需要也要求批判應當植根生活本身。真正的批判力量是在生活世界本身之中,在廣大群眾的感性意識中,批判理論只不過是“從世界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fā)新原理”,是對生活世界的自我批判向度的一種自覺表達[3]186。
二、霍克海默社會批判理論的起點與基干
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現(xiàn)代工業(yè)技術(shù)與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資本與商品交換的邏輯滲透到生產(chǎn)生活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了新變化。
從廣度來看,意識形態(tài)不僅在上層建筑,更滲透到生活世界本身之中。馬克思所描述的沒有被意識形態(tài)沾染過的源初性物質(zhì)生活世界不復存在,而是如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所描述的那樣“把思想意識吸收到現(xiàn)實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識的終結(jié)。相反,在特定意義上,發(fā)達工業(yè)社會較之它的前身是更為意識形態(tài)性的,因為今天的意識形態(tài)就已經(jīng)包含在生產(chǎn)過程本身之中。”[4]12
從深度來看,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滲透到無產(chǎn)階級的感性意識層面。無產(chǎn)階級的感性意識已經(jīng)被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所包圍,霍克海默指出:“在今天,每個社會階層的意識都有可能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和侵蝕,不管它在自身所處的環(huán)境里可能多么地專注于真理。”[3]210正是由于生活世界被打上了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無產(chǎn)階級的新的感性意識受到遮蔽。同樣,無產(chǎn)階級感性意識被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所侵蝕,才使得基礎領域的生活世界被意識形態(tài)“殖民化”。基于此新變化,法蘭克福學派在繼承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基礎上,更對意識形態(tài)進一步批判。而且,批判的觸角更廣,不僅對理論形態(tài)或宗教形態(tài)等意識形態(tài)本身進行批判,更對滲透進生活世界中讓人們失去了實踐變革力量的意識形態(tài)加以批判。
1.社會批判理論的起點: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
霍克海默對社會的總批判包括從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到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一切方面,但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的總批判的出發(fā)點,也是法蘭克福學派與以往一切唯心主義批判相區(qū)別的根本點。
在《傳統(tǒng)理論和批判理論》中,霍克海默認為,傳統(tǒng)理論的基本要求就是“排除一切矛盾,并以充分論據(jù)把各個部分聯(lián)結(jié)在一個完美無缺的形式中”。這種通過純粹理性的思維活動而尋求理論各部分的和諧的企圖,乃是非批判態(tài)度的一種典型表現(xiàn)。“只要理論的概念是自滿自足地建造起來,這些概念就會轉(zhuǎn)化為一種異化的意識形態(tài)范疇。”[5]250就是說,以往的一切非批判的傳統(tǒng)理論,由于其唯心主義性質(zhì)而變成“異化的意識形態(tài)范疇”,變成統(tǒng)治階級的理性工具[6]627。
由此,在霍克海默看來,“同現(xiàn)代的專門化了的經(jīng)濟學相反,社會批判理論保持哲學的形態(tài),即使它采取了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的形式。”可見,社會批判理論同傳統(tǒng)理論的區(qū)別,不僅在于它具有唯物主義性質(zhì)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更在于其是在哲學辯證法指導下的全面批判,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特點。
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是“唯心主義的理性概念的唯物主義內(nèi)容”[5]292。霍克海默這句看似矛盾的話,說明了批判理論的要義所在。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唯心主義的批判精神,是對康德以來德國古典哲學理性批判的延續(xù)。另一方面,它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為基礎。內(nèi)容與形式看似沖突的批判,恰恰是其“開放的辯證法”的體現(xiàn)。既可以克服唯心主義的理性批判的脫離實際的弊病,又能避免機械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批判的僵化。
霍克海默說:“近代的辯證哲學堅持這樣的觀點,即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取決于社會的合理制度。在分析現(xiàn)代社會條件的基礎的過程中,這種哲學轉(zhuǎn)變?yōu)閷τ诮?jīng)濟的批判”[6]626。霍克海默認為,只有著手進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才能促使社會由不合理向合理進行轉(zhuǎn)化,這個世界“已經(jīng)不是人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5]262因此,對理性的唯物主義的批判很自然地變成為爭取合理化的革命斗爭。
2.社會批判理論的基干:意識形態(tài)批判
霍克海默把批判的鋒芒延伸到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人的理性,深植于現(xiàn)實生活的土壤,但在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理性所起的作用遠遠復雜得多。由此,他把批判的重點轉(zhuǎn)向了文化的批判和一般社會意識形態(tài)批判。
一方面,人類社會區(qū)別于自然界在于人類精神文明的獨創(chuàng)性。人類精神文明創(chuàng)造了科技;同時,也從理論上為高度發(fā)達的物質(zhì)文明進行美化和辯護。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越是高度發(fā)達,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越需要訴諸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
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文化和科技的發(fā)展,在為社會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zhì)財富的同時,似乎給人一種資本主義社會無限發(fā)展的生命力的假象,如同是人類理性本身的“合理產(chǎn)物”。科技的發(fā)展不僅掩蓋了現(xiàn)代社會的不合理性,而且好似直接論證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在文化和科技上的欺騙性,產(chǎn)生了比軍事力量等其他手段更為有效的作用。
三、霍克海默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內(nèi)容
霍克海默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便發(fā)現(xiàn)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魔術(shù)式”威力的奧秘。因此,從那時起便逐步把對于社會批判的重點轉(zhuǎn)向?qū)τ谖幕呐校M而實現(xiàn)對現(xiàn)代社會的總批判。
1.發(fā)端:對西方社會心理的批判
1931年,霍克海默就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時,便把對社會心理的調(diào)查作為社會研究所的重要任務。他在就職演說中這樣說,社會研究所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揭示經(jīng)濟基礎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心理聯(lián)系”。接著,在《歷史與心理學》一文中,霍克海默又強調(diào)說:“只要理論還沒有認識到經(jīng)濟生活的結(jié)構(gòu)變化是怎樣通過一個特定時期內(nèi)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心理組成因素的變遷,而在他們整體生活中表現(xiàn)出來的話,那么,關于社會意識依賴于社會經(jīng)濟基礎的理論便仍然包含著獨斷的因素——這些獨斷的因素將嚴格地使這個理論停留在其現(xiàn)有的解釋的那種假設價值的形式上。”[7]
在霍克海默看來,社會心理研究不只具有理論價值,而且也具有現(xiàn)實的實踐意義。它不僅能使歷史唯物主義從一個假設性的理論變?yōu)檎嬲膶嶋H理論,也能揭示出壟斷資本主義與法西斯制度的興起與發(fā)展根源。
2.發(fā)展:對于家庭和權(quán)威的批判
1936年,在《權(quán)威與家庭》中,霍克海默指出:“生產(chǎn)過程對于人的影響不僅是通過間接的和現(xiàn)存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中,他們自己在他們的勞動中與這個生產(chǎn)過程相遇,而且還通過生產(chǎn)過程顯示為相對穩(wěn)定和緩慢變化的制度中,諸如家庭、學校、教會和藝術(shù)。”[8]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的權(quán)威性是資本,而經(jīng)濟條件本身就是資本權(quán)威性的表現(xiàn)。在資本主義表面的“自由交易”現(xiàn)象的掩蓋下,工人不知不覺在家庭教育中向其后代灌輸看不見的、無形的資本的權(quán)威統(tǒng)治。他由此得出革命性的結(jié)論:解決對于權(quán)威服從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個人解放”的問題,而是革命的問題——而這是資本走向它的“反面”,就像貨幣被翻過來的背面那樣。
3.頂峰:對于文化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國高度發(fā)展的壟斷資本主義文明,同樣也對廣大人民群眾形成了高度嚴密的控制作用。不僅在物質(zhì)上,而且在精神上使老百姓遭受殘酷的剝削,處于被奴役的地位。
隨著現(xiàn)代工業(yè)技術(shù)與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資本與商品交換的邏輯滲透到文化領域。受資本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動,文化的生產(chǎn)日益成為商品的生產(chǎn),文化的欣賞逐步成為商品的消費。文化的商品化,使得文化創(chuàng)造打上了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原有的家庭不再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而存在和發(fā)生作用,而“文化工業(yè)的技術(shù),通過祛除社會勞動和社會系統(tǒng)這兩種邏輯之間的區(qū)別,實現(xiàn)了標準化和大眾生產(chǎn)”[9]。
由于文化被徹底技術(shù)化,以最先進的科技所裝備。在“文化工業(yè)”系統(tǒng)中,工業(yè)技術(shù)這個由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機械怪物,反過來成為操縱人類本身的工具。這樣,原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知不覺地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說:“攝取暗含著內(nèi)心維度的存在,這種內(nèi)心維度區(qū)別于、甚至敵對于外在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個人的意識和一種個人的無意識從公眾的意見和公眾的行為中分割開來。現(xiàn)在,這個私人的領域已被技術(shù)現(xiàn)實所侵入和所削減。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和大規(guī)模分配要求整個的個人,而工業(yè)心理學早已不再局限于企業(yè)本身。攝入的多種過程,看來已被固定在絕大部分的機械反應中。”[4]25馬爾庫塞接著指出,家庭作為社會化的一個單位,已被“外面的集體和傳播系統(tǒng)”所取代。
霍克海默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是以“真理是全面的”作為基本指導思想的。阿多諾說:“文化批判的一個基本動機,最中心和貫徹得最持久的觀點,是揭露文化如何杜撰出人的有價值社會的虛幻觀念……這就是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的作用。”[10]對于文化的批判,對于一般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是對于社會的全面批判的基點,因為所有一切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的統(tǒng)治的精神支柱。它一方面腐蝕了被統(tǒng)治的人民的思想意識,為他們提供了種種足以描繪資本主義“合理性”的幻象;另一方面,又麻痹和誘導廣大人民群眾安于現(xiàn)狀,放棄“革命”,以使得資本主義統(tǒng)治延續(xù)下去。
四、總結(jié)
霍克海默認為,意識形態(tài)不單純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意識形態(tài)作為理性的表現(xiàn),固然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但并不是如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是以物質(zhì)的生產(chǎn)活動為基礎的、有規(guī)律的、朝著共產(chǎn)主義最高目的發(fā)展的過程,而是在主體與客體、社會與自然永無止境的相互矛盾中發(fā)展的。這個相互矛盾的各方所組成的關系,乃是一個總體。而人類理性,就其處于現(xiàn)階段為統(tǒng)治階級所控制的范圍內(nèi),往往為人類制造種種有關現(xiàn)實合理的幻象——人們自己在制造這些幻象,卻又自我陶醉和自我迷惑,使這個幻象披上了越來越精致的、虛假的“合理”外衣。正如法國學者高宣揚所說:“批判理論所堅持的對于理性的批判,就是要不斷揭穿理性本身同歷史上某一特定的統(tǒng)治階級的神秘關系,使理性真正地脫離開某一階級或某一集團的操縱,由理性來自我判斷和自我確定。果能如此,理性便能恢復其本來的面目和原有的功能。”[11]
在霍克海默看來,理性能否重新成為人類的真正尊嚴,成為評判真理的標準,這要看它能否重新獲得自我批評的能力,能否擺脫資產(chǎn)階級的控制,批判理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保證理性的純粹性。這雖然揭示了當代社會不合理的原因,但是也充分暴露了法蘭克福學派本身的批判理論的局限性。批判理性反對對于“工具的理性”的崇拜,但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理性的標準”究竟是什么?又有誰去執(zhí)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亙古不變的抽象的真理標準從未有過,有的是隨著歷史發(fā)展而變化的具體標準,而這些具體標準還和現(xiàn)實社會的客觀情境和統(tǒng)治階級利益緊密相連。
霍克海默最終并未解決理性究竟如何恢復其獨立自主性的問題。既然統(tǒng)治階級要控制理性,而現(xiàn)有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或者心甘情愿地按照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濫用理性的功能和權(quán)威,那么,如果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那樣去進行無產(chǎn)階級革命來摧毀不合理的統(tǒng)治秩序的話,又該怎樣切斷現(xiàn)有理性與資產(chǎn)階級的聯(lián)系呢?霍克海默對理性的批判不尋求對某一階級有利的方案,而只能停留在理性本身的王國里,聽任理性自己來做主。這才是理性獨立自主的真正表現(xiàn),這是其思想的局限所在。
參考文獻:
[1]Max Horkheimer. Kritische Theorie[M]. Auflage der Studienausgabe, Fischer Verlag,197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
[3]霍克海默集[M]. 曹衛(wèi)東,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4]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89.
[5]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J].zeits-
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1937.
[6]Max Horkheimer.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J].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1937.
[7]Max Horkheimer.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J]. 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 1932:134.
[8]Max Horkheimer.Autoritat and familie[J]. Kritische Theoie,
Studienausgabe,S.Fischer.S,1977:284.
[9]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08.
[10]阿多諾.道德的最低限度[M].叢子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44.
[11]高宣揚.新馬克思主義導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174.
(責任編輯:張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