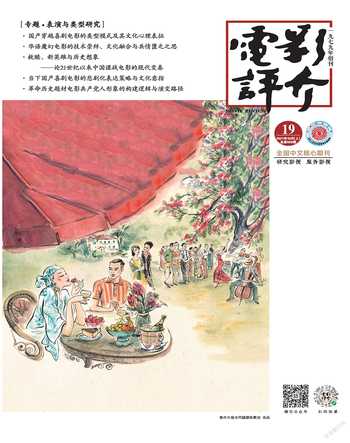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的感官敘事與疾病隱喻
王小靜 吳蕾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在懸疑光影中,梳理出一個關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動人且無奈的故事。曾憑借《沉默的羔羊》(喬納森·戴米,1991)榮獲第64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著名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因在《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爐火純青的表演再次榮獲第93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同時《困在時間里的父親》還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可謂是該年度奧斯卡的最大贏家。對于阿爾茨海默病的關注,很多電影中都有涉及,比如韓國純愛電影《我腦中的橡皮擦》(李宰漢,2004)就講述了女主角患病之后男主角的不離不棄;電影《戀戀筆記本》(尼克·卡薩維蒂,2004)的故事設定也是相伴終生的愛人,即使其中一個人開始遺忘,另一個人總會不厭其煩地講述他們曾經的故事,即使記憶真的抹去了,也要在重復中制造新的回憶。這些電影大多從照顧者的角度展開敘事,主題多與愛情相關。《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以患病的父親為敘事主體,通過他的引導展開情節的建構。也正是因為父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使得他的敘述具有不可靠性,本片因此呈現出“懸疑”的效果,碎片化的記憶拼接宛若迷宮般混亂。但隨著故事接近尾聲,一切又逐步清晰。鏡頭的調度、演員的表現、重復的情節等都在緩緩進行中迸發出巨大的動力,觀者對于親情、自我、生命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一、從舞臺劇到電影的文本深化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是導演弗洛萊恩·澤勒(Florian Zeller)的第一部影視作品,他最初為人熟知的是他作為小說家和劇作家的身份,這部電影就是他根據自己于2012年原創的同名舞臺劇《父親》改編而來的。自古希臘以來,盡管戲劇不斷演變發展,但對于“崇高”的追求幾乎是一以貫之的,這其中當然也少不了劇烈的沖突。近情近理的劇作創作即使打破了傳統的“三一律”,由于戲劇一般在劇場中演出,還是會受到空間的局限。除了演員激情的表演,場次的轉換、道具的改變、旁白等各個環節必須配合默契,才能使劇情高度凝練集中,觀眾才能在有限的觀賞時間中接近事件的真實狀態。即使故事不是一天之中、一個場景、一批人,戲劇也必須遵循規律,在這樣的背景下戲劇呈現的故事是宏大的,缺乏細節的捕捉,形式往往大于內容。戲劇有不同的“幕”,電影文本細化為導演劇本,也就是分鏡頭腳本。內容包括鏡頭號、景別、攝法、畫面內容、臺詞、音樂、音響效果、鏡頭長度等項目,更為精細化。電影給了導演更廣闊的發揮空間,靈活多變的鏡頭語言、不同場面的拼接更為直觀地使觀眾在視覺觀看中達到心理認同。即使電影不像戲劇以追求莊嚴、崇高、典雅、完美為旨趣,但也不缺乏藝術感受力和震撼力。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導演對于劇本文本的打磨。文本創作是戲劇也是電影的基礎,在其他藝術形式還未成型之前,文本必須是形象性與理性、情感性與認知性相互滲透的。《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故事源于弗洛萊恩·澤勒的外祖母,故事背景從最初的法國遷移至英國倫敦,人物與文化背景的改編,使得文本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又以一種全局意識構建社會理性,兼具個人情感又能達到普遍的智性輸出。即使在看似碎片的畫面拼接中也能抓住故事的核心講述者,并在他們的對話和不同的視角呈現中把握故事的脈絡,感悟時間與生命。
影片中最重要的角色莫過于父親安東尼和女兒安妮,他們共同構成電影的兩個敘事角度。托多羅夫(Todorov)說過:“在文學中,我們從來不曾和原始的未經處理的事件或事實打交道,我們所接觸的總是通過某種方式介紹的事件。對同一事件的兩種不同的視角便產生了兩個不同的事實。事實的各個方面都由使之呈現于我們面前的視角所決定。”[1]在故事的前半部分,父親占據著敘事的中心,觀者對于故事的了解來自父親視角,父親對女兒的指責甚至讓觀者誤解安妮可能是個不太孝順、只想繼承財產的自私的人。隨著情節的推進,父親患有阿爾茨海默病這一事實開始顯露,父親的敘事開始變得不可靠,也正是這種不可靠加深了電影對于觀眾的吸引力。觀者半信半疑地跟隨安妮的敘事角度不斷窺探父親患病的細節,卻又對于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一切充滿了好奇。女兒的無奈、父親的敏感在彼此交織中呈現不同的境遇和困惑,不同的事實背后是不可逆的衰老和仍將繼續的生活。在父親患病的這個事件里,不同的情節鋪排打破了時空的界限,不同視角的穿插使故事事實與價值判斷出現矛盾,也就能夠更為客觀地展現故事內核,觀者也可以在質疑中形成與電影的有效互動。尤其是電影中對于相同情節的一次次重播,借助不同的視角對混亂與不合理進行解釋。例如,父親沉睡時,女兒是受不了折磨掐死了父親,還是輕輕撫摸父親的面龐;父親聽見女兒和男朋友在爭執把自己送入養老院時對安東尼臉部的鏡頭聚焦,和從正面記錄的全景聚焦。同一場景換個角度往往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這種鏡頭的調度符合情節的進展,是功能性的結構設置,也是敘事意義的延伸。以“我”這個第一人稱視角展開的故事也更好地凸顯出人物的形象,使觀眾更為接近文本所要傳遞的價值觀念。
二、突破封閉空間的感官敘事
在傳統的文學批評中,故事空間最開始是指背景,強調外部空間可以使人物及其行動具有似真的效果。從最基礎的層面來說,背景的呈現往往能增強觀者或者讀者的視覺化理解,增強代入感,使故事更具有可信性,人物形象更加鮮活。結構主義敘事學家普遍認為,空間對于敘事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結構意義。一方面,空間給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動場所;另一方面,空間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動、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深層意蘊的重要方式。《困在時間里的父親》的敘事空間在三個空間中,包括父親的公寓、女兒的公寓、養老院的房間。這三個空間的布局結構非常相似,尤其是父親的臥室,如果不仔細觀察基本很難區分,甚至可能會以為只有女兒公寓這一個活動空間。為了突破看似封閉且單一的空間,導演不僅注意畫面的色彩轉換,而且借助有限空間里的相似物件設置懸念、給出線索。空間被結構化和整理的地方,就能獲得解答謎題的一個錦囊。父親安東尼游走于公寓中的各個房間,又在不經意中留下痕跡。仔細尋蹤可以知道,安東尼的公寓呈棕色系,安妮的公寓是灰藍色,養老院則是清冷的藍色系。公寓中的燈具、家具、墻面的裝飾畫都有不同。例如,安東尼公寓的壁爐之上掛著小女兒露西的畫作,而安妮公寓的墻面上無裝飾;安東尼的臥室雖然朝向一致,但養老院的床及床頭的裝飾畫、窗外的景色都是不同的。在時空錯亂的迷霧中,揭示的不是恐怖的故事真相,而是安東尼因為患上阿爾茨海默病所陷入的人生困境。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影片中的走廊,安東尼總是在走廊中留下背影,每一次在走廊盡頭,當他打開門,就仿佛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推動故事進展。在有限的空間中,走廊承擔了敘事的橋梁作用,成為敘事空間的轉換樞紐站。當安東尼得知女兒及其男朋友要把他送入養老院,憤怒走向走廊盡頭,打開門,他已身處養老院陰冷的藍色世界,這種視覺的流動性極具詭異感,又能帶給觀眾直接的心靈震撼。記憶術的核心其實就在于視覺聯想,即把記憶內容和難忘的圖像公式編碼以及入位——在一個結構化的空間中的特定地點放入這些圖像。從這種地形學的特點到把建筑物當作記憶的體現只有一步之遙。這也是空間作為記憶術的媒介朝向建筑物作為記憶的象征的一歩[2]。倫敦的公寓是導演精心設計的,各種色彩、道具的存在都是對時空切換的按鈕,看似狹小的空間擁有無限的存量,記錄著安東尼流散的記憶,也共享著每個參與者的感官知覺和生活經驗。
除了視覺的建構,電影的配樂也在極力延溢空間的邊界,依靠聽覺加強感官敘事。最初的電影是沒有音樂的,其實連聲音都沒有,當時還不具備把聲音加入畫面的技術。后來即使有了音樂,音畫也是分離的,音樂是在放映現場配合演奏的,直到有了同步的聲音,現場演奏的音樂才逐漸被淘汰。發展到今天,大部分電影中都有配樂,各大頒獎禮也會有和音樂相關的獎項,音樂成為電影藝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電影配樂和主題曲來自兩種途徑:一種是由音樂家專門為某部電影創作的音樂;一種則是借用已經問世的音樂。這其中既有流行樂,也有古典樂或者爵士等各種類型。好的音樂能助推一部電影的成功,能夠達到相互成全的作用。就如宮崎駿的電影基本都是久石讓創作的鋼琴曲,彼此輝映。音樂能夠告訴觀者某個場景或者時刻所具有的意義,還能推動故事發展,形成強烈共鳴。在《困在時間里的父親》這部電影中,音樂共出現3次,3首來自歌劇的曲子神圣又神秘,每一次的響起都在揭示著安東尼不同的人生軌跡。電影伊始,在安妮穿梭街道回到公寓的過程中,播放的是英國皇室御用作曲家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創作的《冷之曲》,歌聲停止,安東尼出場,戴著耳機的他形容枯槁,就如歌曲所暗示的那樣走入了人生的寒冬,像一座驕傲的孤島。第二次音樂出現在廚房中,伴隨著意大利作曲家貝里尼(Bellini)的詠嘆調《圣潔的女神》,安東尼踉蹌著起舞,輕松且愉悅,這時候的他平和、飽含熱情。只是短暫過后,一個陌生男子保羅的出現馬上又把電影拉回了一種不知所措的驚恐之中,這種反差其實也為后面安東尼真實的狀態埋下了伏筆。從醫院回家的段落采用的配樂來自法國作曲家比才(Bizet)的歌劇《采珠人》中的詠嘆調,無論是坐在車中的落寞還是音樂突然的卡殼,都在昭示著生命的裂痕已經出現。音樂作為感官刺激或刺激感官的一種符號系統,與畫面信息讓人處于從現象到本質的入口或過程中,并在漸入佳境中踏入關于安東尼個體生活的普遍本質和意義探索之中。
三、個體求索指向生命法則的疾病隱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個體意識分為“本我”“自我”“超我”三個維度。“本我”追求快樂,注重現時的享受,受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控制;“自我”則較為現實,受制于“本我”,又起到調節作用,行動力較強;“超我”則受到社會各個方面規則的制約,遵循道德原則。也就是說,主體并沒有恒定的本質,它受到意識和無意識兩方面的影響。作為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意識尚是被分解的,在不同時間、環境呈現的意識狀態會有偏差。作為一個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病人,安東尼顯然試圖掌控自己的意識,即使記憶力在慢慢衰退,生活變得混亂,他也想保持“自我”,甚至完成“超我”。但事實上,安東尼的意志已經不完全受自己控制了,他情緒化、刻薄、多疑、脆弱。當安妮給他找來新的護工時,最初他表現的禮貌、風趣,符合“超我”的規范,但沒一會兒他性情突變,開始數落安妮,甚至詆毀安妮搬進自己的公寓是想要繼承自己的財產,而事實上他是住在安妮的公寓。他的“自我”越是突出,就越接近“本我”的野蠻,也就是人尚未開化的狀態。情緒的狡黠與頑固戰勝了理性和經驗,意識受控于直覺,主體拋棄了社會和歷史,逐漸生物化,無法以原有的樣態繼續存在下去。阿爾茨海默病打破了主體的完整性,像病毒侵入般腐蝕主體的身體機能,摧毀主體的精神系統。個體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博弈,想要對于“自我”存在的確認,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在大量特寫鏡頭下通過不著痕跡的表演展現得淋漓盡致。電影中出現兩次安東尼找手表的情節,其實也是安東尼想要試圖掌控自己與現實的聯系的一種隱喻。“找”其實是安東尼對于“自我”的一種確認,是想對自己活在當下的一種明證;“手表”代表著時間,是世界運行的秩序。阿爾茨海默病打破了時空的運行準則,使得安東尼不知道自己身處一個什么樣的環境,尤其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當他懷疑護工、懷疑保羅拿了自己手表的時候,其實就暗示著他其實已經走入時間的迷宮,被時間控制。安東尼·霍普金斯將內心戲與表演場景重合,契合主人公的慌亂,是電影與生活的真實統一。而時間最終指向的則是死亡。弗洛伊德指出,“開始認為人類正在可怕的死亡驅力的掌握之中憔悴凋萎,而這一死亡驅力就是自我釋放到自己身上的一種原始受虐欲”[3]。雖然電影結局還未提到死亡,但受困于疾病的安東尼已經被死亡驅力所包裹著。最后,安東尼對著護士說自己想要找媽媽,依偎著護士的他回到孩童模樣。本能的需求超越思想的滿足,自我變成一個可憐的實體。對于生命價值的確認回歸有知之前的狀態,最終只是在掙扎中指向死亡的悲劇。
生老病死,沒人可以逃過這一生命的規律,人的一生在健康之外總會伴隨著疾病。比起癌癥,阿爾茨海默病的攻擊性不算強烈,但卻更加考驗一個人的能力,畢竟這是一個耐心和時間的混合體,也就難免要與倫理聯系起來。倫理的范圍由濃厚的關系決定,有親密也有疏遠。與道德不同的是,在倫理語境下的人是一個實體詞,更具有個性。在疾病隱喻的背后,電影更加注意對于道德的解綁、對于個體的尊重。在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困在時間里的不僅只有父親,還有女兒。也許有人不理解安妮最后把父親送到養老院的安排,但這樣的劇情卻更體現出導演的功力。道德是一種必要的善,決定父母要撫養子女,子女要贍養父母。而倫理則是在原則上選擇的善,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可以選擇的關系。當然這種選擇往往是具有轉移性的,有義務但不強制。安妮的第一次離婚其實就與父親有關,包括后來與男朋友的爭論,都可知她從未放棄自己的父親,即使父親心里更在乎死去的女兒露西,安妮也是默默承受并選擇理解。父親進入養老院她會給父親寫信,假期從巴黎回來,與父親散步、交談,安妮其實就是整部電影壓抑氛圍中溫暖的代表,不張揚,平凡卻充滿力量。生活永遠處在不確定的狀態中,倫理的價值不僅在于打通社會里消極情感轉化為關愛和關心的通道,而且在于承認并肯定每一個人獨立的自我價值。個體受制于自然規則,也囿于情感的牽連,個體的理性仍有決定的主動權。在“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傳統理念之外,導演或許也在告訴觀眾每一片葉子都有凋零的時候,人同樣如此受制于生死命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有凋零就會有新生,微不足道卻也獨一無二,個體的價值不會輕易消失,活過即存在。
結語
電影是文本感知的特殊分享,是平凡世界的特別構成。完整的電影文本不僅是一種再現,而且是直接的感官體驗。《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把故事置于純粹而有限的空間,借助多個維度的視角一步步揭開一個家庭的不幸。以個體的感受為出發點,記憶與想象、現實與虛幻沒有清晰的界限,生命在時空混淆中運行。時空的視聽轉換加之飽滿的故事情懷恰如其分地相融為一體,混亂的碎片在故事的推進中才一點點得以拼湊。從當下出發,跟隨電影的視角,使故事在發生于回憶的時刻移位、變形、扭曲、更新,有限空間延溢出無限的可能。在公寓中游走暗喻疾病壓制下個體對于自我的尋找,意志與意識的拉扯,暴露出生命的脆弱,也展現出善良的美好。疾病是人類難逃的劫數,或大或小,或早或晚,如果無法避免,那就勇敢并堅強地直面它。時空輪回,個體的困境總會消解在時間的齒輪之下,倫理的最終追求是對自我的關愛和對別人的成全。所以,不必沮喪,生命之花仍然值得綻放!
參考文獻:
[1]王泰來.敘事美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27.
[2][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M].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59.
[3][英]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