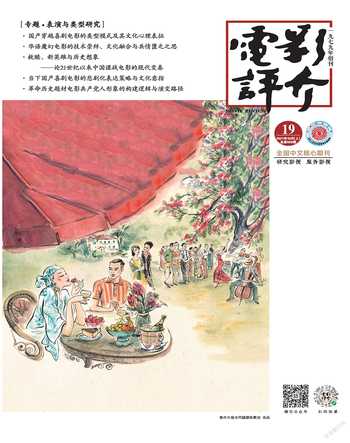由《1917》透析影像本體論中“一鏡到底”敘事
王煜 馮曉媛
一、“一鏡到底”與影像本體論
“‘一鏡到底’,英文名為One-shot,是指用一個攝影機拍攝、在一個鏡頭內表現出整部影片,或者是通過后期剪輯加工讓人感覺整部影片是一個鏡頭的拍攝手法,可分為真正的‘一鏡到底’和加工的‘一鏡到底’兩種。”[1]其中,真正的“一鏡到底”對拍攝技術、場景設置和演員表演都有較高的要求,其畫面的連貫性也遠超由多個鏡頭拼接剪輯后的效果,由此拍攝的影片的美學意義甚而可能超過本文所要表達的核心題旨;加工的“一鏡到底”常被稱作“偽一鏡到底”,即借隱藏剪輯痕跡來使畫面連接顯出平順感、一體感,它對于運動鏡頭的起幅和落幅有著嚴格的條件制約。
“一鏡到底”因鏡頭是連續的(或要體現連續感),需在一個鏡頭內表達全部內容,故其在形塑人物、鋪敘情節、時空轉換等方面與多數由一系列鏡頭蒙太奇連接起來的影片有所不同,由此造成“一鏡到底”文本自身的獨特性,給人以流暢畫面帶來的沉浸式觀影體驗。“一鏡到底”在電影中的出現最早可追溯到阿爾弗萊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1948年拍攝的驚險片《奪魂索》。其可謂最早的一部“一鏡到底”影片,場景集中于一間房子,借演員背景黑幕進行轉場從而給觀眾以連續的視覺影像。事實上,因為當時一卷膠片只能拍10分鐘,所以嚴格地講,《奪魂索》并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一鏡到底”。自《俄羅斯方舟》(亞歷山大·索科洛夫,2002)以真正的“一鏡到底”給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視覺體驗后,越來越多的導演嘗試拍攝“一鏡到底”的影片,如《鳥人》(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2014)、《維多利亞》(塞巴斯蒂安·施普爾,2015)等。
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的“影像本體論”認為,電影的影像是自動生成的,它與被拍攝物同一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攝影與繪畫不同,它的獨特性在于其本質上的客觀性。況且,作為攝影師眼睛的一組透鏡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們的名稱就叫‘objectif’。在原物體與它的再現物之間只有另一個實物發生作用,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嚴格的決定論自動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預,參與創造。攝影師的個性只是在選擇拍攝對象、確定拍攝角度和對現象的解釋中表現出來;這種個性在最終的作品中無論表露得多么明顯,它與畫家表現在繪畫中的個性也不能相提并論。一切藝術都是以人的參與為基礎的,唯獨在攝影中,我們有了不讓人介入的特權。”[2]基于此,安德烈·巴贊對通過大量鏡頭組接來渲染劇情、控制觀眾情緒、引導觀眾思考與導演創作思想趨同的蒙太奇理論提出了批評,認為剪輯所創造的蒙太奇效果會破壞影片的時空統一性,而其對觀眾心理的操縱實是對觀眾觀影自由的束縛。他認為,電影是所有藝術門類中與現實結合得最為緊密的一種藝術形式,它只有通過盡可能地再現“真實”,方能逼近電影藝術的真諦——“段落鏡頭”(俗稱“長鏡頭”)乃是電影再現真實的一種最重要的拍攝手段,這種亦稱作“鏡頭內部蒙太奇”的手法“能保持電影時間與電影空間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表達人物動作和事件發展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因而能更真實地反映現實,符合紀實美學的特征”[3]。在本質層面上,“一鏡到底”就是段落鏡頭的一種極致化表現形式,其目的是追求更為逼真的“真實”,即展現一個與蒙太奇所創造的“真實”大不相同的更為真實、客觀的時空環境,進而給觀眾更多的觀察角度和思考空間。
二、《1917》“一鏡到底”的本事
薩姆·門德斯(Sam Mendes)2020年執導的戰爭電影《1917》,據曾服役于英國國王皇家步槍團一營的導演的祖父阿爾弗雷德·H·門德斯的回憶錄改編而成。故事的發生背景為1917年4月6日(一戰期間)的法國戰場。在德國與英、法兩軍激戰時,兩名年輕的英國士兵(準下士)布雷克和斯科菲爾德接到命令,需在8小時內穿過西部戰線,向指揮官麥肯錫上校傳達“立刻停止進攻”的命令。如命令傳遞不及時,前線的1600余名戰士將會被敵人所設的圈套屠殺。因對前方戰況一無所知,二人只能開啟一場冒險。在布雷克犧牲后,斯科菲爾德繼續前進,終在歷盡千難萬險后趕到前線,并在英軍即將陷入巨大犧牲前停止了進攻。其實,這在某種意義上頗有大衛·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最后一分鐘營救”的意味——矛盾三線(撤退德軍設伏、英軍剛發起追擊、斯科菲爾德剛趕到)并存,只是其解決方式不是用蒙太奇的切換,而是用“一鏡到底”式的段落鏡頭予以呈現。
這部長達1小時58分鐘的“一鏡到底”式影片,由迪恩-查爾斯·查普曼(Dean-Charles Chapman,飾布雷克)和喬治·麥凱(George MacKay,飾斯科菲爾德)飾演主角,由羅杰·狄金斯(Roger Deakins)攝影,李·史密斯(Lee Smith)剪輯。《1917》摒棄了戰爭電影常用的宏觀敘事與人性反思,亦沒突出主人公的“主角光環”及對個人英雄主義的彰顯,而是聚焦軍中的兩個小人物,跟隨他們的足跡,用“偽一鏡到底”的影像實踐來營造沉浸感,讓觀眾與他們所認同的主人公一起完成一段艱難無比的“奧德賽之旅”——在看似線性簡單的敘事結構下蘊含深刻的生存哲思。片中有這樣一句臺詞:“Down to Gehenna or up to the Throne,He travels the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不論是下地獄還是稱王,獨行俠走得是最快的。)這是將軍在給二人下達任務時說的話(這似乎也暗示二人最終會有一人犧牲),盡管這會對兩人的情緒和心態產生影響,但這也為后文故事的發展做了鋪墊。
事實上,《1917》是首部采用“一鏡到底”的手法攝制的戰爭題材影片,但其又是“偽一鏡到底”的,即其乃由多個較長時值的運動鏡頭拼接而成,只是鏡頭間剪輯的痕跡被巧妙隱藏起來,從而營造出一種一氣呵成的視覺流暢感。在某種意義上,“一鏡到底”是呈現該片內核故事并產生感人效果的最佳方法,它讓觀眾在100多分鐘的觀影過程中時刻與兩位肩負大任的小人物同呼吸、共患難,體驗獨一無二的災難性戰爭的現場感。也因如此,該片以數字技術與“偽一鏡到底”的巧妙結合獲得了巨大成功,斬獲第77屆金球獎劇情類最佳影片獎和最佳導演獎,并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上獲得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最佳音響效果三項獎。
三、《1917》“偽一鏡到底”實施策略
實事求是地說,之于一部近兩小時的影片,想“一刀不剪”“一貫到底”是非常困難的。也因如此,《1917》采用“偽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來實現美學上的追求及出乎意料的視覺效果。
(一)“一鏡到底”的空間環境
1.以掠過戰壕的段落鏡頭對比來展現敵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
《1917》開篇不久便再現了不少戰壕的畫面:全景畫面中原本坐在草地上休息的兩名士兵被另一士兵叫走,他們不停地穿梭在英軍修建的戰壕中。從草地到指揮室,從光線明亮的室外到光線暗淡的指揮室內,“一鏡到底”展現了英軍戰壕的環境狀況與士兵的精神面貌。以兩個士兵為前景的畫面引導觀眾的視覺運動方向,主人公逆攝像機的拍攝方向運動(攝像機處于后退反跟拍攝狀態),在流暢的節奏中,后景或背景中依次出現正在吃飯或做飯的士兵、坐在戰壕里休息的士兵、在戰壕中運送物資的人員(此時攝像機與主人公同時停留在畫面中,主人公不動,攝像機也靜態拍攝),見到要帶二人去指揮室的中士后,畫面搖拍繼而由倒退反跟改為正跟拍攝,即由拍攝主人公的正面轉為拍攝主人公的背面。一直追隨主人公連貫性拍攝的攝像機攜著觀眾的“第三只眼”紀實性掠過的英軍整體狀況,為接下來不無“探險”意味的任務奠定了基礎,暗示了一種危機四伏的緊張感及因士兵連日作戰而彌漫的疲憊感、無助感,也凸顯了戰爭的殘酷性及即將執行的任務的艱巨性和執行者作為攸關眾多生命的關鍵信使的重要性。另外,段落鏡頭加景深鏡頭(輔以聲音元素)的環境再現,也讓人更客觀地看到空間的全貌及事物之間的實際聯系:傷亡慘重的英軍、被主人公踩踏過的英軍尸體、寫明毒氣觀察哨的標牌、燒焦變黑的木板、被炸傾塌的防空洞等,都為主人公和移動著的攝影機所親歷——英軍戰壕中的所見所聞頗為直白地展現出戰爭的殘酷與人性貪欲的危險。
同樣,展現主人公穿越德軍所建戰壕時(此時德軍已撤退),《1917》亦采用“一鏡到底”。無疑,主人公置身德軍戰壕即置身險境,命運變得不可預知,觀眾的心理也隨著主人公的艱難前行而劇烈波動。實際上,雖以超長段落鏡頭高度寫實,但為緩解視覺與審美疲勞,影片還是增添了一些戲劇性色彩:在進入德軍第二道戰壕時,布雷克和斯科菲爾德發現了德軍布下的可引爆炸彈的絆線,然就在二人慶幸發現及時之時,一只老鼠拖著一個裝有食物的袋子碰到了絆線,隨即引爆炸彈,二人不得不倉促逃離。顯然,這一充斥幽默與戲劇性成分的段落暫時性改變了敘事節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觀眾的緊張心理,自然也證實德軍的撤離并非被迫,而是預設陷阱的以退為進。掠過英、德兩軍戰壕的段落鏡頭也明示當時的時代背景:畫面中的德軍裝備和戰壕情形遠好于英軍,這恰與主人公所要傳遞的緊急命令相吻合——德軍撤退到興登堡防線之前,已在原防線與新防線間設置了地雷和狙擊手,撤退只是其策略,準備追擊的英軍則面臨慘重的犧牲。穿越戰壕的畫面多采用移鏡頭(多為縱移)、搖鏡頭(上下或左右搖拍)和跟鏡頭(正跟和反跟),保持了對戰壕時空環境的完整呈現,同時交代了德軍作為入侵方(德國為一戰發起國)略強于英軍的軍事實力。
2.以“鏡頭內部蒙太奇”的場面調度來壓縮空間
很顯然,“一鏡到底”難以像蒙太奇那樣可自由打破影片內部的時間線和空間布局,它只能通過“鏡頭內部蒙太奇”即一個段落鏡頭內的場面調度來實現空間轉換。對《1917》被隱藏的剪輯點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其主要實施了動作轉場、遮擋轉場和搖晃鏡頭轉場,在給人“一鏡到底”之感的同時,悄然壓縮空間產生表意,強化中心意旨。在主人公從后方戰壕走到前線戰場時,即影片的10分32秒處,有個巧妙的以空間壓縮來實現內部蒙太奇轉場的處理:接到任務后,布雷克慮及哥哥的安全,便馬不停蹄地往前走,斯科菲爾德緊跟其后;一段時間后,他們遇到一個黑色通道(穿過此通道,他們就可到達前線,然此又是一個很長的通道),于此影片實現了第一次蒙太奇轉換,即以“黑色”隱藏剪輯點的手法實現難以覺察的空間壓縮,將距離很遠的兩個地方連在一起。在25分50秒處,影片運用了同樣手法將戰壕和防空洞連接在一起,實現了空間的轉場。
在某種意義上,電影是夢,或者說是制造幻覺的藝術。影片能借助受眾的視覺幻象,來構建一種時間上的連貫感,既在顯在文本層面保持時空的連貫性,又在實踐層面降低拍攝難度。其實,也只有將段落鏡頭與場面調度有機融合,其語言意義才可能被最大限度地激活,或者說,才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影像風格,更好地發揮寫實表意功能。
(二)“一鏡到底”的人物形象
事實上,《1917》“一鏡到底”所采用的第一人稱視角也使觀眾因認同機制而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繼而對人物形象塑造與接受有所助益。換句話說,因鏡頭語言的創新性鋪敘,主人公布雷克和斯科菲爾德的形象變得更為立體,個性更為鮮明。
究其根本,接受任務且擔心哥哥安危的布雷克奮不顧身地開始穿越冒險,可謂他看重親情的表現;在防空洞里德軍所埋炸彈被引爆后,他徒手扒開廢墟救出斯科菲爾德,應是他重視友情的表現;在德軍飛機墜落在他與斯科菲爾德的面前并燃燒時,他率先沖上并與斯科菲爾德合力將飛行員救出,繼而在斯科菲爾德提議幫助重傷的德軍飛行員脫離痛苦(結束其生命)時,布雷克卻說“他需要水”——這是他善良的表現(盡管最后他被自己所救的人刺死)。對敵軍伸出援手,昭示布雷克的反戰思想。借諸多合情理的寫實細節,影片塑造出立體的布雷克形象——一個善良的忠于親情、友情但因自我“盲目的”善良而犧牲了的沒有主角光環的主角。
較之布雷克,斯科菲爾德的形象更立體、豐滿。從他掏出用布包著的面包分給布雷克一小塊并說“我自有辦法”時,展現了其極為頑強的生命力和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這也符合他參加過索姆河戰役的身份);在進入德軍戰壕時,明知會有敵人觀察哨和狙擊手的他攔住了布雷克,說“Age before beauty(長者優先)”,則體現了雖是在布雷克的申請下自己被迫參加此次任務的他,依舊有著強烈的責任心(盡管在他看來,承載無上榮譽的勛章有時還比不上一桶水,但在任務、危險面前,他也從不退縮)。布雷克死后,斯科菲爾德的人物形象有了升華,從厭戰、被迫參加任務到對將要死去的戰友強調自己一定會找到其哥哥并完成任務。之后,自我意識覺醒和肯定了自我行動價值的他,守著對犧牲戰友的承諾與完成任務的決心繼續前行,最終挽救了很多人(包括布雷克的哥哥)的生命。片尾,完成任務的斯科菲爾德坐在草地上,與片頭他坐在地上的畫面相呼應,無疑預示戰爭還在繼續,犧牲還會存在,需要他完成的艱巨任務依然會有。
概言之,影片通過豐富的細節將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鮮活而充實,給人呈現出忠誠、勇敢、善良的“平凡英雄”形象。不僅如此,在形塑人物的同時,“圣誕節”“休假”“火雞”等令人渴望的物事言語也順帶出現在戰壕中,與現實環境中的戰爭、死傷、蒼蠅等物象形成鮮明對比,并在不無詩意色彩的視聽表達中隱喻創作者的厭戰與反戰情緒;農場中的殘垣斷壁、空中飄落的櫻花、橫陳地上的尸體等也從多個方面展示出戰爭的殘酷和生命的脆弱,令人深思、警醒。
(三)“一鏡到底”的沖突呈現
毋庸置疑,《1917》屬于劇情時間大于敘述時間的影片。它將一個限時八小時的任務濃縮進不足兩小時的畫面中,而且采用“一鏡到底”的敘事手法,足見其展示劇情沖突(特別是主要矛盾沖突)之難,但亦具有不無挑戰性的美學魅力。
片中最強烈的沖突在1小時37分處,垂直于發動進攻的英軍前進方向的斯科菲爾德奔跑著去向指揮官傳達停止進攻的命令。在長達1分鐘的段落鏡頭中,順利找到德文營的斯科菲爾德發現麥肯錫上校已經按原計劃展開對德軍的進攻(第一梯隊已經攻了上去)。這意味著如斯科菲爾德沒有將命令及時傳遞上去,將會有更多的人傷亡。影片在展示這一至關重要的矛盾沖突時,使用了俯瞰大全景,讓人清晰地看到兩個不同方向的奔跑:英軍第一梯隊從畫右往畫左跑(入畫到出畫),斯科菲爾德則從后景向前景跑(攝影機在他的前面正面俯拍)。大景別、小人物,以斯科菲爾德為畫面主體,持槍沖鋒的英軍士兵作為前景和后景,畫左連續的爆炸、紛紛倒下的士兵襯托出斯科菲爾德行動的緊急,整個段落一氣呵成,有著非常緊張甚而令人窒息的節奏。
很明顯,一群自東向西沖鋒的戰士,一個自北向南傳遞關乎沖鋒士兵生命消息的人,不同的動作線(輔以慘烈的爆炸聲響)明示了此刻的尖銳矛盾與復雜場景。一面是視死如歸(為國向死,不得不為),一面是拯救生命(軍務重大,戰友所托),不同方向(甚至是“死”與“生”的相反方向)的交叉奔跑畫面在詩意化呈現的同時頗有意味地完成了深刻的表意——暗示如命令被更快傳達,第二梯隊即可免遭戰火,故斯科菲爾德快速的奔跑也應和了觀眾的心理期待。影片通過段落鏡頭的影像直觀,既立體化了有著強烈沖突的戰場,也凸顯了影片的反戰題旨。
四、“一鏡到底”的利弊得失
一如《1917》的編劇克里斯蒂·威爾遜-凱恩斯(Krysty Wilson-Cairns)所說,影片初衷是讓觀眾在另一個人的生命里活上110分鐘[4]。因鏡頭始終跟隨主人公的行動運動,觀眾便很難從他們之外(即空間距離超出畫幅處)獲得更多的信息,只能被主人公引導著一步步深入劇情,并獲得一種沉浸感。當然,受眾也會不自覺地將自我感受代入劇情,賦予主人公的命運以更多的關注。對主人公行動途中的所見所聞,影片多以布雷克和斯特菲爾德的主觀視角予以展現,包括曲曲折折的戰壕、戰壕外面的死馬及其身上的蒼蠅、大大小小積了水的彈坑、彈坑中的浮尸、坑道中的老鼠、被德軍毀壞的大炮、成堆的炮彈殼、燒焦的樹林、摧折的櫻花樹、無人收養的奶牛、墜落燃燒的飛機、被焚燒的教堂、湍急的河流等,無疑都富有沖擊力,并給人強烈的視覺震撼,亦象喻反戰主題。可以說,“一鏡到底”的戰爭殘酷物語被普通士兵的友情和勇敢精神所包裹,殘酷的現實境遇用唯美構圖的畫面來展現,流溢出不無“對立”意蘊的審美張力。加之流暢合理的敘事節奏,遂使段落鏡頭的美學功能在有限的時間里發掘空間敘事的無限可能性方面得以有效達成。
其實,《1917》“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不能簡單地用紀實美學來概括,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引渡沉浸感的媒介。美國《綜藝》雜志影評人彼得·迪布魯吉(Peter Debruge)這樣評價《1917》:它以電子游戲式的“一鏡到底”審美實現了幾近虛擬現實版本的事件呈現[5]。很明顯,《1917》采用“一鏡到底”完成了視聽語言的游戲化處理(頗像《絕地求生》手游),給人一種在游戲世界中與隊友對壘的感覺,兼以身臨其境的真實感、沉浸感。處于畫面中心位置的人物引領著觀眾的視覺,其命運牽動著觀眾的心,殘酷的環境成為主人公路過時不經意的所見所聞——這種也許是因習慣而熟視無睹所暗示出來的殘酷自然,比刻意的描繪更觸動人心。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也有局限,它無法對比性展示跨地域的更為宏闊的場景和跨度較大的歷時延續,即使前后兩部分的敘事轉變(視點、結構、風格等),有時也難以鋪墊與過渡,繼而使受眾在面對突然的敘事轉換時產生視覺割裂感;為求得更強烈的欣賞沉浸體驗,手持拍攝的鏡頭難免會有需要避免的晃動,遂使觀影效果大打折扣。另外,若是忽視主題呈現的技術為先(如《地球最后的夜晚》),那所謂的“一鏡到底”就更值得商榷。再者,就《1917》而言,觀眾面對僅有兩個主人公的世界且整部影片都被兩人引領時,他們的觀影耐心能否經受住考驗也是一大問題。
當然,因“一鏡到底”操作起來較復雜,對場景設置、演員表演、攝影技術和場面調度有著較高的要求,具體實施時,創作者多會設計出若干剪輯點,利用剪輯特效和觀眾的視覺誤差拼接多個段落鏡頭,最終達成“偽一鏡到底”的視覺效果。鑒于題材和事件的獨特性(《1917》據真人回憶創作,關乎生命與救贖的小兵傳信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須恪守寫實主義風格的《1917》采用“一鏡到底”,既益于題旨彰顯,亦可在鏡頭語言上進行頗有藝術價值的詩意探索。故而,用“一鏡到底”展開敘事較之蒙太奇敘事,無疑會增加更多的客觀性、真實感,主人公的親歷也會讓受眾自覺進行比較而深信畫面呈示的戰爭的殘酷與自我所處現實的美好,進而生出珍惜和平的期許。說到底,技術是為藝術呈現服務的,它所表現在視覺上的效果應具有意味或意義。即是說,對“一鏡到底”的運用,或比之技術美學,契合影片題材、結構、風格、思想的整體敘事建構更為重要。
參考文獻:
[1]吳婷.“一鏡到底”的藝術特色[ J ].藝術科技,2016,29(10):124-125.
[2][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11-12.
[3]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修訂版)[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55.
[4]Thelma Adam.Scripter Krysty Wilson-Cairns Broke Rules with“1917”[ J ].Variety,2020-02-03.
[5]Peter Debruge.“1917”:Film Review[ J ].Variety,201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