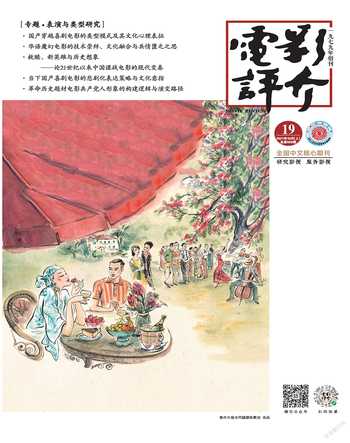現代史詩與異托邦想象:魔幻小說改編電影中的時空建構
周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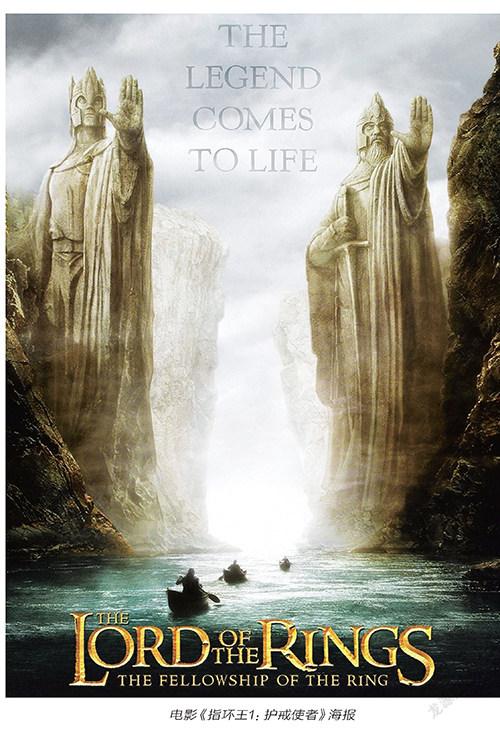
近年來,隨著創作思維和創作技術的不斷革新,我國魔幻題材電影的發展也迎來嶄新的局面。其中,有的故事從中國傳統的神話和傳說中發展變形而來,如《捉妖記》等;有的則是積極從西方魔幻文學和電影中汲取養料,做出有益的嘗試。但站在世界電影的坐標上,考察魔幻電影的質量,以美國、英國為首的電影體系在魔幻電影的創作中依然處在絕對的領先地位——以《哈利·波特》系列、《指環王》系列、《納尼亞傳奇》系列電影為代表的魔幻電影作品,依然是世界魔幻電影體系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就魔幻電影的經典作品而言,其創作背后不僅有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的加持,源于西方的魔幻文學傳統可謂是更為深刻的創作土壤——從《哈利·波特》到《指環王》,再到《納尼亞傳奇》,都是基于小說母本,進而創造出電影魔幻世界的范例。我們看到,從文學到電影,一個個跨緯度的超現實的幻想時空被建構出來,這里或擁有與人類不同的生命種族,或擁有現實世界不存在的奇幻力量,在整體的時空中排除現實世界的存在,在獨立發展中漸漸形成史詩格局,或是在超現實的能力和超現實的景觀集聚中,與現實世界形成時空的雙軌并存,投射出創作者“異托邦”的想象。
一、從文學到電影:魔幻文化的興起和共榮
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從根源上看,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其自身自然帶有“幻想”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剖析,魔幻文化一直在藝術領域的勃興,幾乎是藝術“虛構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將魔幻元素作為虛擬世界建構的核心要素,從而發展出成熟獨立的世界觀和作品體系,可以看作是魔幻作品的創作邏輯。無可否認,魔幻文化發軔于文學領域。一般認為魔幻小說起源于18世紀末的英國,其雛形為英國哥特式小說,以霍勒斯·沃波爾的小說《奧特蘭托城堡》為發端,神秘、恐怖和超自然的性質為魔幻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直到19世紀50年代末,魔幻小說才逐漸成型。這個過程中,作家喬治·麥克唐納的作用至關重要——1958年,喬治的長篇小說《幻境》發表,小說在神話的框架中將魔法、童話的元素融入其中,同時,小說“黃粱一夢”式的成熟故事,蘊含著嚴肅文學的思想表達,成為文學史上第一部寫給成人看的現代奇幻創作。然而,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魔幻小說的發展勢頭卻有所萎靡,魔幻文學直到20世紀,迎來了質的飛躍,從20世紀文學自超現實主義革命到魔幻現實主義繁榮,到英國魔幻小說的進一步發展都印證了這一點。如果說早期的魔幻小說還未從神話和童話中獨立出來,那么20世紀的魔幻小說真正在創作模式和創作主體上實現了突破性的“獨立”。20世紀上半葉,艾蒂絲·尼斯比特,艾狄森和鄧斯尼爵士等作家不斷涌現,將魔幻小說的發展推到“黃金時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當屬艾蒂絲·尼斯比特和她的代表作《魔法城堡》。小說講述了3個孩子在野外探險的途中,誤入魔法城堡,得到魔戒,開始更加神秘危險的魔幻探險的故事。這是魔幻小說創作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人類世界和魔幻世界在同一時空中的并立和融合,可以說,打通了現實世界和魔幻世界的文學壁壘,為魔幻小說注入了現實主義的靈魂。《魔法城堡》也深刻影響了后世的魔幻小說創作,如托爾金的魔幻巨著《指環王》就沿用“魔戒”的經典設定。與尼斯比特不同,艾狄森擅長更為完整的魔幻世界構建,艾狄森在《奧柏倫巨蟲》中塑造了一個完全沒有現實世界參與的獨立世界,并將王國、貴族等元素融入其中,為其賦予中歐世界的風情。發展到鄧斯尼爵士創作時期,魔幻小說又迎來了新的突破——鄧氏的創作真正使魔幻小說從凱爾特神話的基調中獨立出來,進入原創神話的時代。他自創神譜,打造全新的神話世界和神話關系,這對后世的魔幻小說影響頗深。這一時期,更值得關注的是,魔幻現實主義的興起,以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為代表,開啟了震動世界文壇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潮。二戰后,魔幻小說的創作迎來了空前繁榮,在英國,涌現出托爾金、劉易斯、JK·羅琳等一批優秀作家,《指環王》《納尼亞傳奇》《哈利波特》等一系列作品成為一代經典;在美國,克里斯·范·艾爾斯伯格、喬治·R·R·馬丁、羅伯特·喬丹等作家也不斷耕耘,創作了《冰與火之歌》《時光之輪》等魔幻巨著。
正是因為魔幻文化在文學領域的根源性,當我們從電影的角度去審視魔幻文化的博興時,不難發現,魔幻電影和魔幻文學之間的天然聯結性。甚至有觀點認為,魔幻電影本身就隸屬于魔幻文學的范疇。確然,回溯魔幻電影的發展史,這一點也可以得到印證——在電影的早期發展階段,現實和幻想兩大發展趨勢就初現端倪,其中,偉大的電影先驅喬治·梅里埃就是“幻想電影”的奠基者。他的電影《灰姑娘》(喬治·梅里埃,1899)是現今可考電影中第一部具有“魔幻”元素的電影,而其文學母本就是著名的童話故事《灰姑娘》。而當代魔幻小說的電影化改編大體上是從20世紀末開始實踐,《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可以說是近年來具有開創性,也是最成功的魔幻小說改編電影。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數字技術的發展,電影制作水平有了質的提升,創作者在技術的支持下不斷從魔幻文學汲取養料,創作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魔幻電影作品——無論是以《指環王》系列、到《納尼亞傳奇系列》為代表的魔幻史詩類作品,還是以《愛麗絲夢游仙境》《黃金羅盤》等為代表的獨立篇幅魔幻電影,都具有“取自文學,立于電影”的特性。
二、完全時空中的現代史詩演繹
在文學領域,“魔幻史詩”的實踐可以說是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開始的,小說描繪了布恩迪亞家族7代人的傳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鎮馬孔多的百年興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個世紀以來風云變幻的歷史。作品融入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現實與虛幻,展現出一個瑰麗的想象世界,成為20世紀重要的經典文學巨著之一,這部作品也成為魔幻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現實性”成為其魔幻外殼下的內核。在被成功改編成電影的魔幻小說中,率先建構史詩版圖的,當屬托爾金的《指環王》。在《指環王》中,托爾金建構了一個奇麗魔幻的“中洲世界”(又稱中土世界),這里有霍比特人、精靈、巫師、奧克等不同種族,人類也是其中之一。這里的“人類世界”也不具備“現實性”,是基于整個“中州世界”的體系虛構出來的,它在時空特性上,充滿羅馬帝國時代的歷史風貌,如果將讀者生活的真實世界作為“人類世界”的對比考量,就會對這個“中州世界”的時空建構性有很深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的開辟和虛構,更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上的根本性建構,是和現實世界完全沒有關聯的完全體。也就是這種根本的虛構性,使得這類作品無論是小說形式還是電影形式,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都能呈現出完整的虛構體系。以《指環王》為核心,作者托爾金在作品體系中逐步完成對“中洲歷史”的完整書寫——從“第二紀元”:魔王索隆打造魔戒,努門諾爾人類的淪亡,紀元末期討伐索隆的聯盟大戰;到魔戒在霍比特人咕嚕和比爾博之間流轉的中間時期;直到霍比特人弗羅多和眾人一起,將魔戒護送到精靈國瑞文希爾去毀掉。在電影的體系內,這一史詩過程通過《霍比特人》系列電影和《指環王》三部曲得以體現,在托爾金的小說文本基礎之上,《指環王》的電影改編編織了一個龐大的故事體系,使整部影片都呈現出氣勢磅礴的史詩風格。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托爾金的文學體系里,除了小說《指環王》《霍比特人》,托爾金的《精靈寶戒》《胡林的兒女》《努門諾爾與中洲之未完的傳說》《剛果林的陷落》等作品,也參與了這一史詩的建構。這些作品中的某些情節,在電影改編的過程中被巧妙地融入其中,有的則作為留白的故事背景,間接參與了電影的“史詩呈現”,并在讀者和觀眾之間構成需要自行探索的趣味世界。
以《指環王》系列電影作為典型案例,分析魔幻小說電影化過程,不難發現,成功的魔幻電影關于史詩化的呈現,逐漸有跡可循。“史詩化的電影語言”“史詩化的時間歷程”“史詩化的種族譜系”是魔幻史詩電影的幾大關鍵。首先,《指環王》系列小說一再出版,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作者托爾金已經以插畫的形式,對“文字的可視化”打下了一些基礎。在《指環王》系列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彼得·杰克巧妙使用電影的視聽語言再現了托爾金筆下的“中洲世界”:一方面,使用數字技術對“魔幻世界”進行建構,從法貢森林和洛漢王宮,到《霍比特人》中的妖精洞窟和瑟蘭迪爾宮殿,這些美輪美奐的場景都離不開維塔數碼公司的數碼特效。可以說,呈現在銀幕上的這些場景幾乎都是真實拍攝和人工“造假”的結合品[1];甚至還通過數字技術,造出一個純數字化的人物——咕嚕;另一方面,在基礎鏡頭語言的運用上也堪稱精準:大量遠景、全景、俯瞰鏡頭、風景鏡頭的使用,將“中洲世界”的遼闊恢弘展現得淋漓盡致,以打造“視覺奇觀”入手,呈現魔幻史詩電影的外在風貌,特別是幾場史詩大戰的呈現,留名影史。從另一個角度看,電影本身也是“時間的藝術”。它將一個歷時長久的故事濃縮進兩三個小時的電影時間內,可以說是對故事時間的重構,也可以說是對現實時間的“拓展”。從故事的內在時間,《指環王》的故事是由人類、精靈、霍比特人、矮人、巫師(美雅)等共同譜寫的史詩,歷時千萬年,而電影則跟隨文字,以幾個小時的長度再現了這一史詩畫卷。如上文所說,《指環王》中涉及包括人類在內的各大種族,從小說到電影,首先是完成了各種族中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如睿智沉著的團隊主心骨白袍巫師甘道夫、戰斗力強又英俊的精靈王子萊格拉斯、看似平凡卻堅韌有勇氣的霍比特人弗洛多等。其次,電影通過視覺化的幾個場面,也完成了對各大種族的群像刻畫,特別是在幾場大戰中——持弓弩馳援而戰死的精靈們、縱馬搏殺的人類;隊伍中的三個霍比特人,樂觀、堅毅,又團結……在人物譜系構架中兼顧個體形象和群像的呈現,從而為史詩敘事打造人物基礎,是此類魔幻史詩電影的一大亮點。
三、雙重世界中的異托邦想象
福柯曾經對20世紀之前的哲學研究提出質疑,他認為偏重時間研究而忽略空間研究幾乎是當時哲學研究的事實:“自康德之后,哲學家們將觀念的焦點集中到時間上。黑格爾、伯格森和海德格爾都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的是,空間受到了遺棄,因為它處在闡述、解析、內涵、死亡和固定、惰生的一面。”[2]基于這樣的研究格局,福柯和他的空間理論為哲學研究開辟了新的世界,“異空間”理論就是其中重要的存在。福柯認為,“這些場所是外在于所有場所的,盡管它們實際上是局部化的。因為這些場所全然不同于它們所反映,它們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與烏托邦相對立,我稱它們為異托邦。”[3]福柯認為,不同于烏托邦的虛無,異托邦必須擁有實在的空間,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點。但它們又與一般空間不同,是處于主流和非主流文化之間。通過福柯列出的幾個空間示例——監獄、墓地、醫院——可以看出:在整個社會空間的構建中,這些“異空間”發揮著特殊的作用,映射著主流空間中的某一個負面,正因為如此,它們或許居于主流期待之外,卻又實實在在位于整體空間之內,與一般空間保持著微妙的隔絕關系,也發生著實在的聯系。在一部分魔幻小說中,魔幻空間之于現實空間,就是這樣的存在。其中最典型的作品當屬《哈利·波特》。
在小說《哈利·波特》中,以霍格沃茲學院為基地的魔法世界,和“會魔法的人”一起盤踞在離一般世界很遠的地方,需要在隱秘的九又四分之三站臺乘坐火車才能到達。而這看似有著“結界”的兩個世界卻“同在一片天空下”——霍格沃茲的孩子們從不乏從一般世界選拔而來的佼佼者,比如三人組的智力學識擔當赫敏;當孩子們放了暑假,還是要回到一般社會去生活:比如在前幾部里寄人籬下的哈里。電影藝術地再現了這種雙重世界的關系,并著力在視覺上突出魔幻世界的“異托邦”屬性——前期以童趣為主,高聳入云的學校建筑、會移動的樓梯、會動的畫作、帽子分院儀式、金色飛賊等;后期主角團面對的黑暗勢力漸漸浮現出來,陰暗恐怖的氣息彌漫在魔法世界。這種游離于主流空間之外,又滲透于整體空間之中的現象,在《哈利·波特》的衍生作品《神奇動物在哪里》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為了不讓來自異托邦的侵入者影響到主流社會的運作機制,在大戰后,一場大型的“一忘皆空”魔咒化成大雨,洗滌了每個人的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魔幻電影”的概念在我國提出較晚,但從電影史上考證,魔幻電影的實踐卻幾乎貫穿于中國電影發展的始終——從形態上看,中國早期的神怪片可以看作是中國魔幻電影的早期實踐。早在1927年的電影《盤絲洞》(但杜宇,1927)中,就出現了超現實的元素,影片取材自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記》的著名章節,講述了唐僧被盤絲洞的蜘蛛精所困的故事。自此,向中國神話、古典文學、傳統文化求索的中國式魔幻電影創作之路漸漸形成。國產魔幻電影大多以中國文化為本位,雜糅了愛情、武俠、動作、懸疑、娛樂等類型元素,以特有的神怪文化資源完成闡釋現實世界的終極意旨。[4]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技術的加持更是讓國產魔幻電影找到了與動畫、漫畫形式結合的新型路徑。近年來,出現的國產魔幻電影整體彰顯出中國古典文化的強大資源保障:《畫皮》(陳嘉上,2008)、《畫壁》(陳嘉上,2011)、《倩女幽魂》(葉偉信,2011)等均取材于《聊齋志異》;而《西游·降魔篇》(周星馳,2013)、《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田小鵬,2015)、《西游伏妖篇》(徐克,2017)等,均以神話故事《西游記》為題材進行改編,而《哪吒之魔童降世》(餃子,2019)、《白蛇:緣起》(趙霽,2019)等均取材于我國古典神話故事。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中,人、妖、仙、佛各界并存,從“人”的視角來看,其他各界均含有異托邦的特性。
參考文獻:
[1]陳濤.魔幻影像與“感覺現實主義”——彼得·杰克遜電影中的數碼特效[ J ].當代電影,2016(07):58.
[2][法]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M].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2.
[3][法]福柯.不同的空間——激進的美學鋒芒[M].周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22.
[4]李娟.魔幻電影的敘事資源與視覺空間[ J ].中華文化論壇,2019(0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