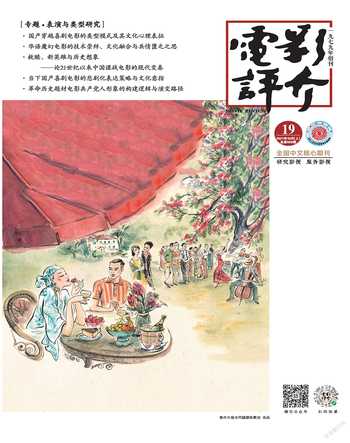結(jié)構(gòu)、觀念與重述: 由《盛夏未來》觀照中國青春片新語態(tài)
徐江濤
自21世紀(jì)一批引起觀眾熱議的青春片上映以來,青春片成為大陸電影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中文化主題的探究,也成為電影研究與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內(nèi)容。2021年7月底上映的《盛夏未來》(陳正道,2021)以兩名高中生為主要人物,在呈現(xiàn)青春故事的同時展現(xiàn)兩名高中生背后的文化結(jié)構(gòu)與社會熱點(diǎn)問題。
一、青春故事后的文化結(jié)構(gòu)
在中國大陸乃至整個華語青春電影譜系中,《盛夏未來》都是其中普通而稍顯特殊的一部。普通之處在于,《盛夏未來》以少男少女的成長成熟故事為基本線索,承襲了青春片中青春有遺憾(戀愛的遺憾、考試的遺憾)但青春無悔(年輕人對于自由不計(jì)代價(jià)的追求、毫無保留地相互幫助等)的情感基調(diào);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一部拍給“90后”乃至“00后”等“數(shù)碼原住民”的青春電影,它并不站在《夏洛特?zé)馈罚ㄩZ非、彭大魔,2015),《乘風(fēng)破浪》(韓寒,2017),《后來的我們》(劉若英,2018)等重返青春、追憶青春的中年人視角感慨青春不再,也不像《送你一朵小紅花》(韓延,2020)和《少年的你》(曾國祥,2019)一樣以身心病痛、校園霸凌事件等先在于故事結(jié)構(gòu)與人物角色之外的矛盾點(diǎn)推動敘事的戲劇性,令電影整體向成熟的類型化方向發(fā)展。在影片的整體故事與風(fēng)格基調(diào)上,《盛夏未來》沿襲了導(dǎo)演在“精神前作”《盛夏光年》(陳正道,2006)的基本風(fēng)格,以平淡樸實(shí)的日常敘事承載了感情與精力充沛的青春故事,雖然幾乎沒有刻意營造的喜劇包袱與催淚點(diǎn),也沒有頗具戲劇性的小概率事件,甚至男女主角在校園中都是平凡的,卻在緩緩流淌的時間與情緒之流中給國產(chǎn)青春片帶來了不一樣的風(fēng)格色彩。《盛夏未來》講述即將高考的女孩陳辰意外發(fā)現(xiàn)媽媽與賣水果的王叔叔的“外遇”而心情低落,她發(fā)現(xiàn)父母早已離婚,只是為了不影響自己高考才繼續(xù)同居。陳辰為了保護(hù)三口之家的存續(xù)在高考時交白卷,并謊稱自己與校園網(wǎng)紅鄭宇星早戀才影響了成績,卻不料在復(fù)讀班中真正對鄭宇星產(chǎn)生了感情。《盛夏未來》中,觀眾不僅能從陳辰與鄭宇星像朋友又像情侶的有趣互動中重新體會青春的樂趣和悲傷,而且能從陳辰父母對待情感關(guān)系的副線中,站在成人的角度對少年情感的追尋進(jìn)行有趣的佐證與補(bǔ)充。這樣一來,影片就在內(nèi)容層面上飽含多重內(nèi)涵:既有對青春少年們真實(shí)情感的關(guān)注,對當(dāng)下性別議題的探索,對應(yīng)試教育得失的微妙辯證關(guān)系,又包含兩個互相辨認(rèn)為“同類”的靈魂是如何在未解的青春里攜手面對成長的種種難題,勇敢地面對真實(shí)的自己,同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見證彼此的成長和蛻變。影片從陳辰與鄭宇星相識相知的感情入手,拿捏得當(dāng)?shù)卣故玖水?dāng)下青少年在家庭中與父母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在學(xué)校中與老師“亦敵亦友”的師生感情,以及對LIVE音樂、搖滾樂隊(duì)、社交網(wǎng)絡(luò)、新媒體等新興事物的關(guān)聯(lián),從而將電影主題從“青春”或“青春期人群”有效輻射到家庭與社會。片尾處電音節(jié)上,鄭宇星和陳辰的臺詞與動作,更是令影片的故事不再拘泥于二人之間的曖昧感情,有效升華了影片的整體立意。
與同題材、同基調(diào)的《盛夏光年》相比,《盛夏未來》同樣是在簡單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反復(fù)渲染角色感情的,每個片段都欲言又止。這樣的寫法令陳正道的兩部青春片將青年人的戀愛故事引向更廣泛的文化結(jié)構(gòu)。《盛夏未來》中,朝夕相處的陳辰與鄭宇星同樣含含混混地享受著以“友情”為名的青春時光,他們在上課時候偷偷聊天,放學(xué)之后一起學(xué)習(xí),分享同一個耳機(jī)中的歌曲,在閑暇時間一起散步、一起吃飯、一起唱歌、一起過生日,一切都是鮮活而簡單青春片“類型”;《盛夏光年》中的慧嘉、正行和守恒也是一樣,在陽光照進(jìn)矮墻,小雨、斑駁的校舍、籃球場的器材屋中,“青春”主題在電影美術(shù)風(fēng)格中的描敘分外凸顯。盡管對青年主體的塑造與對青春想象的呈現(xiàn)在早期電影中已有體現(xiàn),但戰(zhàn)后的西方電影卻首次以青春作為敘事主題與影片美術(shù)基調(diào),使得青春電影成了一個明確的、以青少年為主角、以高度年輕化的觀眾為對象的商業(yè)片類型。“戰(zhàn)后好萊塢電影的‘青春化’連接的是20世紀(jì)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這一階段的青春片所呈現(xiàn)出的反叛、對抗與迷茫為世界電影史意義上的青春片劃定了一個基本坐標(biāo)系,從國別電影的發(fā)展來看,青春片不僅意味著前面所說的演員和觀眾的‘青春(吸引力)’,更體現(xiàn)為創(chuàng)作者的青春(反叛與挑戰(zhàn)),其在題材和電影語言上的突破可能會形成一種電影新浪潮。”[1]《盛夏未來》片尾處,慧嘉、正行和守恒三人之間同樣充滿無法宣諸于口的感情。海邊滾動著躁動不安的雷聲,對峙的三人之間彌漫著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般的沉默,最后守恒宣泄般地喊出“康正行,你永遠(yuǎn)是我最好的朋友”,宣告了這段感情的無疾而終。《盛夏光年》則以高考與表白這兩個“事件”標(biāo)記著“青春”的終結(jié):高考意味著分離,表白意味著少年在性別上成為成熟的青年,陳辰與鄭宇星成為他們讓彼此開始正視自己心意的契機(jī)。隨著故事平緩地推進(jìn),故事中的“年輕人”到了不得不告別青春故事,為了進(jìn)入更廣闊的未來做出選擇的時候。其選擇的結(jié)局,就是從青春故事走向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一如陳辰終于理解了父母的苦衷,同意了母親與王叔叔的戀愛,并重新認(rèn)識了已經(jīng)身為知名DJ的鄭宇星。與《夏洛特?zé)馈贰冻孙L(fēng)破浪》等影片相比,《盛夏光年》與《盛夏未來》的語時與語態(tài)是更為當(dāng)下化的,男女主角在當(dāng)下已經(jīng)體會到長大成人過程中的遺憾與悵惘;與《盛夏光年》相比,《盛夏未來》更加重視當(dāng)下文化語境的影響。短視頻平臺上的網(wǎng)紅在同齡人中格外受到歡迎、靠對音樂的喜好尋找“同類”,都是當(dāng)下“00后”青少年群體中司空見慣的生存習(xí)慣與生存方式。《盛夏未來》將這些元素納入敘事,不僅更為貼近當(dāng)下主流觀眾的現(xiàn)實(shí)生活,而且成功在文化結(jié)構(gòu)的意義上實(shí)現(xiàn)了青春片的有效重寫。
二、青春與“青春片”觀念的倒錯與更新
青春片作為一種具有獨(dú)特文化意義的片種,當(dāng)我們對其加以討論時,不能在空泛的扁平歷史背景下談?wù)撓嚓P(guān)議題,必須圈定一個確定的文化、倫理與歷史范圍,賦予青春片以具體的年代背景。從宣揚(yáng)將青春投入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的《青春之歌》(崔嵬,1959)開始,無論是具有“傷痕文學(xué)”特性與建設(shè)新時代熱情的《青春祭》(張暖忻,1985),還是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影響、在時代劇變中顯示出困惑與迷茫的《頑主》(米家山,1989)與《十七歲的單車》(王小帥,2001),中國的青春電影始終勇敢地觸及與表達(dá)著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歷程。它們不僅從獨(dú)特的批判與反思角度發(fā)掘了一代代中國人多年來對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而且提供了一種很優(yōu)美而獨(dú)特的形式來表現(xiàn)這些獨(dú)特的內(nèi)容。不同的時代思想與青春經(jīng)驗(yàn)具有不同的特性,每一部青春片都有其獨(dú)特的意識形態(tài)范圍與思想觀念,因此,“青春片”這一語詞的所指也是非常具體的。中國當(dāng)下的青春片首先是有著商業(yè)特性的類型片,有著特定的敘事成規(guī)與對特定市場的吸引。以《盛夏未來》為例,這部影片采用了一種淡淡的憂傷情感基調(diào),在當(dāng)下時空中顯示出從揮灑青春激情到思念與懷舊的轉(zhuǎn)變;敘事空間從校園空間向外輻射,涉及主人公的家庭、與主人公愛好相關(guān)的場所如音樂節(jié)等。從2013年開始,《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夏洛特?zé)馈贰冻孙L(fēng)破浪》《后來的我們》等影片在院線相繼亮相,“青春片”成為新的文化議題與閱讀癥候。“青春”這一話題似乎總是指向令人向往的赤子之心、年輕人不計(jì)回報(bào)的付出以及對光明前途的美好向往。反過來看,這一意象也作為一種空洞的能指被不同時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反復(fù)構(gòu)成和填充,在看似相近的大光圈攝影、近距離面部特寫、對光線與環(huán)境的考究攝影下,是“青春”概念本身的反復(fù)倒錯。這些同義反復(fù)的敘述圓圈構(gòu)成一系列關(guān)于“生命”“愛”“幸福”“唯美”“浪漫”“時代”“新”“未來”等所指的、空洞的能指符號,“因其空洞而激動人心,因其空洞而獲得強(qiáng)大的解釋力量,并最終成就一個完滿的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神話”[2]。那么,關(guān)于“青春”的話題在何種意義上在這些超高票房的商業(yè)片中發(fā)揮作用,這些被稱為“青春片”的電影又具有怎樣的電影形式、敘述方法和電影觀念?
學(xué)理上的“青春期”與“少年”“兒童”等概念一樣,都是近代以來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變形產(chǎn)生出的、關(guān)于“人”的話語。“青春期”這一概念在美國發(fā)展心理學(xué)中最早被提出時,描繪的是13~17歲之間人的心理發(fā)生迅速成長變化的時期。20世紀(jì)60年代,全球范圍內(nèi)的青年反文化運(yùn)動與青年主導(dǎo)的民權(quán)運(yùn)動,在肯尼迪政府的推動下被全面賦予了叛逆、左翼、激進(jìn)等意味,“青春期”“代溝”等概念也真正借由大眾文化等渠道在全球社會中流行起來[3]。可以說,所有青春電影都遙遠(yuǎn)地呼應(yīng)著“青春”最早產(chǎn)生的文化語境,這些青春電影在大眾文化的回收與融合中不斷促使觀念的叛逆、更改、倒錯與更新,一邊以電影商業(yè)市場所定義的“青春吸引力”與“青春反叛性”生出諸多可能存在脫離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景觀,一邊保持著憤怒、反叛與反思的色彩。即使是看似平緩發(fā)展的《盛夏未來》,在情緒色彩上也依然抱有反叛與憤怒的情緒。無論是陳辰離經(jīng)叛道、以交白卷對抗家庭分裂的舉動,還是頗具自由色彩的、在同學(xué)們起哄和圍觀下的奔跑、上課時一人一只耳機(jī)偷偷捂著耳朵聽歌“開小差”、在高考前說走就走到海南聽電音節(jié)的旅行,都充滿了青少年亞文化中儀式抵抗的色彩;陳辰與鄭宇星通過抖音平臺“秀恩愛”、鄭宇星將兩人喜歡的歌做成Remix版本,在DJ臺上作為定制的生日禮物送給陳辰,都在高考將近的背景前顯得離經(jīng)叛道、隨心所欲。而電影中父母和班主任的存在,仿佛作為一切現(xiàn)實(shí)主義、擊垮理想的反面力量站在主人公一切行動的對面。“美國青春片從不是孤立的電影類型,而是在生產(chǎn)、制作、流通、發(fā)行及接受各方面都依托其他類型片及其電影史的書寫發(fā)展而成的混雜集合”“是關(guān)于類型的類型,同時也是一種具有高度連續(xù)性的‘再類型’。其不但不拒絕各種類型傳統(tǒng)中的模式化敘事結(jié)構(gòu)、人物類別、臉譜化造型,甚至充分利用這些‘刻板印象’來創(chuàng)建沖突、強(qiáng)化效果”[4]。看似循規(guī)蹈矩的青年對父輩與集體的反叛與挑戰(zhàn),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tǒng)功利觀念與追逐激情之間的對抗成為貫穿《盛夏光年》的重要旋律。如果將20世紀(jì)60年代的社會現(xiàn)實(shí)視作最初孕育現(xiàn)代意義上青春觀念以及青春電影的土壤,那么在遠(yuǎn)離全球民權(quán)運(yùn)動風(fēng)起云涌的社會現(xiàn)實(shí)之后,青春片必然面臨在何處落地的問題。
三、青春角度的觀察視角與現(xiàn)實(shí)重述
當(dāng)青春與青春片離開其原生的文化與社會土壤之后,就會逐漸成為一種價(jià)值表現(xiàn)與現(xiàn)實(shí)敘述上越來越趨于多元化的亞類型和混類型。在中國青春電影譜系中,《盛夏光年》以一種不同于之前青春片的姿態(tài)呈現(xiàn)了青春敘述背后的社會結(jié)構(gòu)問題,從而對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了從獨(dú)特“青春”位置出發(fā)的有效重述。對于一般觀眾而言,《盛夏未來》在觀感上首先是一部十分新鮮和新潮的電影:抖音、音樂網(wǎng)紅、Live與DJ、電子音樂、酒吧、音樂節(jié)都能成功喚起新一代觀眾的共鳴,“我一首特別喜歡的電子樂下面只有兩個人評論,特別好奇這兩位是誰”“去電音節(jié)可以遇到自己的同類”“我們要拒絕虛偽拒絕撒謊,直面自己的內(nèi)心不好嗎”,這些臺詞都是當(dāng)下新一代高中生生活的寫照。陳辰和鄭宇星之所以會成為朋友,而且彼此引為同聽一首歌的知己,不僅因?yàn)樗麄兏鶕?jù)音樂尋找同類,而且因?yàn)橐魳烦蔀樗麄儗宫F(xiàn)實(shí)壓力的重要資源。對于當(dāng)前的青少年人群來說,追求棱角分明的鮮明個性、特立獨(dú)行且對世界有強(qiáng)烈好奇心非常重要,他們以流行文化與網(wǎng)絡(luò)媒介上的虛擬偶像為理想形象,希望活成自己夢想中的樣子。導(dǎo)演陳正道雖然出身中國臺灣,卻對大陸青年學(xué)生的生活相當(dāng)了解,在影片中對陳辰與鄭宇星生活的諸多細(xì)節(jié)進(jìn)行了充滿趣味的展現(xiàn),像是集體跑步時同學(xué)們的起哄、考試后會根據(jù)排名調(diào)整座位、下課后復(fù)讀生還在堅(jiān)持做題、老師將學(xué)生的手機(jī)收集起來、男女間用社交平臺的互動來揣測對方的心意、孤獨(dú)時只能和Siri對話等情景,都是當(dāng)下年輕人生活中觸手可得卻容易被忽略的細(xì)節(jié)。這些細(xì)節(jié)讓整部電影的現(xiàn)實(shí)敘述具有了落地的真實(shí)。在影像上,《盛夏未來》也十分考究:鄭宇星和陳辰偷聽音樂時,當(dāng)歌詞唱到“in this moment I lose focus”時,鏡頭做了變焦處理,“focus”即“焦點(diǎn)”,在電影語言與自然語言層面同時映射出兩人的情感變化。在鄭宇星崩潰的一場戲中,他在音樂節(jié)上給暗戀已久的明打電話,音樂節(jié)的彩色燈光投影了點(diǎn)點(diǎn)光斑,打在他悲傷的臉上,像眼淚一般在迷幻的氛圍中渲染出悲傷的氛圍;在結(jié)尾閃回的泳池戲份中,把陳辰從水中拉出來的另一雙手實(shí)際上是水面上陳辰自己的倒影,倒影中實(shí)像與虛像的對照關(guān)聯(lián),呈現(xiàn)了陳辰從逃避現(xiàn)實(shí)到直面內(nèi)心的轉(zhuǎn)變,也揭示了陳辰的情感沒有得到回應(yīng)的孤獨(dú)狀態(tài),以及只有她自己能將自己從悲傷中解救出來的心靈景況。導(dǎo)演僅用了這樣一個鏡頭就呈現(xiàn)了她與自我的和解,可見對鏡頭語言的把握與操控力度之強(qiáng)。《盛夏未來》在看似精致的畫面與浪漫的情緒之流之外,有力地袒露出青春的不同面向。作為一部青春電影,它暴露出了年輕人似乎不那么“溫順”和循規(guī)蹈矩的一面,而觀眾也應(yīng)該通過對電影的反思勇敢地向真實(shí)的生活袒露自身,感受青春最真切的現(xiàn)在時態(tài)。
在現(xiàn)實(shí)生活的面向上,鄭宇星和陳辰的家庭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具有相近的位置。在兩人撞見陳辰母親和海南水果王見面的那場戲中,原本只有兩個人的對話中,第3和第4個人的加入制造了有趣的節(jié)奏點(diǎn);陳辰和鄭宇星試圖為上一輩人的對話“配音”也顯示出現(xiàn)實(shí)中年輕一代與長輩之間的關(guān)系。在當(dāng)前的文化語境中,孩子天然具有言說父母的立場與能力。這部電影不只試圖言說傳統(tǒng)核心家庭中的新一代,或是某一特定社會文化中成長的新一代的成長,而是試圖以當(dāng)代年輕人的情感為路徑,探討與觸摸當(dāng)代中國的某一段現(xiàn)實(shí),它在青春故事的敘述之下提出和解決的是一個典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其中多元化的青春與青春片內(nèi)涵,正在作為一種“動態(tài)的文化調(diào)解機(jī)制”發(fā)揮出調(diào)節(jié)個人、家庭與社會,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問題的作用。
結(jié)語
作為二戰(zhàn)后伴隨青年亞文化興起的產(chǎn)物,青春片經(jīng)歷了文化結(jié)構(gòu)、故事主題、思想觀念等多層面的變化后,終于在當(dāng)下的中國被固定為一種具有穩(wěn)定意義生產(chǎn)功能的敘事系統(tǒng)。《盛夏未來》在對青春片的電影表述和電影時態(tài)進(jìn)行了富有意義的探索,參與了大眾文化對社會的觀察與反饋。
參考文獻(xiàn):
[1]陳琰嬌.《過春天》重新定義青春片了嗎?——兼談國產(chǎn)青春片的命名焦慮[ J ].戲劇與影視評論,2019(03):78.
[2]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145.
[3]陳犀禾,吳小麗.影視批評[M].上海: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03:71.
[4]白惠元.“后青春期”與“暮氣青春”:中國青春片的情動視野及其性別政治[ J ].文藝研究,2019(3):15.
[5][德]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