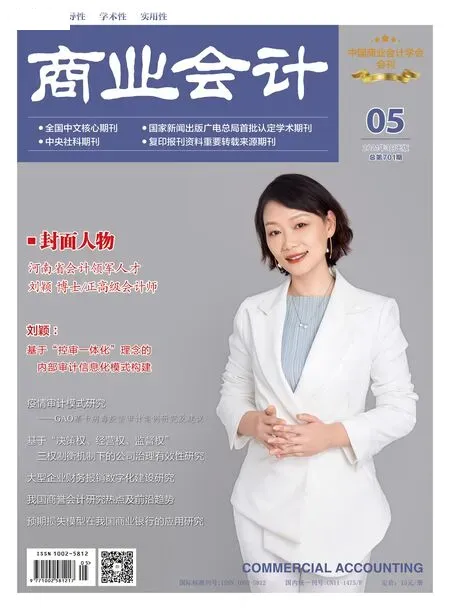基于政府監管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
王索南吉 秦嘉龍(教授/高級會計師)
(青海大學 青海西寧 810000)
一、引言
過去以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三五規劃強調生態文明建設,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企業、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越來越重視環境問題,努力實現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雙贏”。關于政府監管、環境績效和財務績效的關系,以Wally和White head(1994)為代表的傳統學派認為,環境績效提高會伴隨著企業環境成本的增加,進而增加企業的總成本,勢必會降低企業的財務績效。修正學派代表人物Porter(1998)則認為,企業采取積極的環境保護措施,將提升企業的社會和公眾形象,從而促進企業的銷售量和財務業績。我國學者賈春香、王婉瑩(2018)認為,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之間不存在明顯線性關系。在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道路中,充分把握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至關重要。汪長英(2019)認為,為使企業價值有進一步的提升,上市公司在加強治理環境污染的同時,對影響資本市場的因素也應考慮在內。由于環境污染問題外部性的存在,采取政府干預的手段可以使外部性得以內部化,在治理環境績效過程中政府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運用多種干預手段去解決問題,Niu XueJiao等(2020)研究發現政府監管對環境治理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政府監管是調整環境問題的宏觀調控工具之一,但政府監管對環境績效和財務績效的效果究竟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選擇企業的財務績效受外部環境影響相對較大的化工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化工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一)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的關系
企業環境投資在倡導環境保護的法制社會中,可以提升企業價值,企業的環境管理措施、技術創新等投入都會增加企業的成本,但在某種程度上還能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Latan(2018)、Duanmu等(2018)、白世秀等(2019)、王文寅等(2020)研究認為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劉輝(2016)進一步研究得到,企業要加大環境環境保護,控制污染物質排放,從中獲取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朱清香等(2020)研究認為,企業通過主動承擔環境責任來提高環境績效,使企業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綠色需求,從而提高企業財務績效。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采取環保措施后擁有的聲譽會轉變為企業的競爭資源,促使企業在發展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由于化工業企業對于資源與環境的依賴性較強,因此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外部環境質量的提升長期下去會提高化工企業財務效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化工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二)政府監管、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
張兆國等(2019)、王建秀等(2020)研究發現政府監管能夠督促企業投資環境成本,提升環境績效;陳超凡等(2018)發現政府監管可以推動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潘紅波、饒曉瓊等(2019)在比較《環境保護法》實施前后的情況后發現,政府的相關政策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環境績效。蔣倩(2017)研究認為,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企業價值之間的正相關性隨政府監管強度的加強而加強;從長遠來看,嚴格的政府監管將實現公司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的“雙贏”。
外部性理論提出,政府嚴格的制度可以使將企業環境問題中存在的負外部性得以內部化,有效干預能使企業競爭環境更加公平有序,并提高市場經濟的有效性。政府監管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工具,在嚴格的政府監管背景下會給企業形成良性競爭環境,環境績效的增加能帶來收益的增加,政府監管政策的努力改善能有效促進環境績效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說明政府監管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能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政府監管在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以化工行業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環保稅于2018年初開始實施,為了保證數據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截取2018—201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本文所需有關數據來自東方財富網銳、思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網(IPE)等。同時對原始數據進行了以下篩選:(1)剔除*ST以及ST等無法滿足可持續發展的上市公司,避免離群值的影響。(2)再以2018年樣本量為基準,剔除尚未披露環保稅數據的公司。(3)剔除2018—2019年化工業上市公司的相關指標數據不完整、缺失的樣本。經過以上篩選最終獲得174個研究樣本。并考慮到部分數據出現極端值的情況,本文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都在1%水平上進行Winsorize處理。本文采用Excel、SPSS 22.0對數據進行了處理與分析。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企業財務績效指標分為兩大類:會計類指標和市場類指標。會計類指標反映的是年度內企業的盈利情況,并且能夠更好地反映企業整體業務狀況,市場類指標可以從資本市場投資者預期的角度反映企業發展情況與企業價值,該指標需要更加有效的資本市場,但我國資本市場薄弱,因此本文借鑒許慧(2020)、王佳等(2020)的方法,選擇總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財務績效(ROE)的指標。
2.解釋變量。在國外,CEP指數或TRI數據庫數據主要用于衡量企業的環境績效,而在我國,對環境績效研究相對較晚,現有研究對環境績效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不同學者嘗試從不同角度對環境績效進行測量,大致可以分為變量替代法和綜合打分法兩大類。由于綜合打分法中的數據來源不系統,作業的主觀性很大,影響了研究結論的參考價值與穩定性。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在胡曲應(2012)、尹建華等(2020)的研究基礎上進行調整后,將營業收入與環保稅比值作為環境績效(EP)的替代變量,該比值的倒數為EPi。
3.調節變量。我國對政府監管的實證研究時間較短,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衡量指標體系,本文借鑒鄭思齊(2013)、李力(2015)的方法,以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指數)衡量政府監管,反映政府監管環境情況的力度。PITI指數根據企業注冊地所在城市得到政府監管指數,沒有具體評分的城市以企業所在省省會的得分代替反映該城市環境信息的透明度,該指數能對政府執行環境政策的情況做出客觀、全面的評價。
4.控制變量。根據吳昊洲等(2018)的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以下變量:研發能力(Rd)、償債能力(Debtp)、企業規模(Size)、營運能力(Oper)、成長能力(Grow)、市場化程度(Market)等數值變量和年度(Year)這個分類變量。
(三)模型設計
首先,以財務績效為被解釋變量,環境績效作為解釋變量,加入相關控制變量,為檢驗假設1構建了模型(1):

其次,本文以財務績效為被解釋變量,環境績效為解釋變量,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政府監管變量以及政府監管和環境績效的交互變量,為檢驗假設2構建了模型(2):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為了更加清晰地認識數據的分布和變化,本文主要采用SPSS軟件對選取的174家符合篩選條件的重污染上市公司1 740個觀測值作為總樣本,對其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N=174)
從以上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樣本間的財務績效沒有太大的懸殊,ROA的標準差在0.1以下。單位營業收入排污費——EP數值較小且該指標為逆向指標,將EP取倒數后為EPi,EPi的均值為3 410,極小值和極大值分別為688、5 500 000,兩個極值之間的差距大,并且標準差超過3 000,表明化工業各企業之間的環境績效水平相差很大。調節變量PITI的極小值、極大值分別為24.600、80.800,平均值61與極大值更加接近,說明各級政府對其所屬管轄地區的化工業企業的環境進行了嚴格的監管。對于控制變量,企業的償債能力采用資產負債率,資產負債率均值為0.376,說明化工業企業的償債風險處于較低風險;企業的增長能力取決于其營業收入的同比增長率,從營業收入同比增長率的均值來看,僅為0.122,說明在2018年、2019年企業的增長能力較弱,處于瓶頸期;企業的營運能力以流動資產周轉率來表示,流動資產周轉率均值為1.998;同時,由于企業規模和研發能力采用的是總資產和研發費用的自然對數,相對而言差距并不特別大,說明所選樣本整體的規模和研發能力比較均勻;而且所選企業2018年和2019年的數據均完整。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運用SPSS軟件對經篩選數據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檢驗,確定了兩個變量相互之間的相關性,且沒有其他變量的影響,表2是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的統計結果。

表2 各變量相關性分析
從表2可以看出,由于EPi指標為環境績效EP的逆指標,在1%的水平上顯著,環境績效EP對財務績效ROA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償債能力、市場化程度等控制變量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初步驗證了假設1,不過這只是兩個變量之間是對其他變量沒有進行控制情況下的相關,因此還要看回歸結果。政府監管與環境績效這兩個變量在1%的水平上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與財務績效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政府監管無法直接影響財務績效,由于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政府監管可以通過影響環境績效來間接影響財務績效。
(三)回歸分析
本部分在描述性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展開分層回歸分析,檢驗設定的模型(1),分析解釋回歸數據,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層回歸分析
表3中,加入自變量的前后兩個模型的VIF均值在1.1左右,皆小于10,因此說明回歸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均為0.3左右,說明公司財務績效有30%的變差可以由企業環境績效和控制變量來解釋,該解釋比例雖不高,但是擬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模型中的F值大約為12,在1%的置信度上顯著,表明總體上回歸驗證模型有效。并且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因為模型的VIF均值小于1.2,其DW值大于2,不存在自相關。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企業償債能力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關系。因為債務和權益是企業重要的資金來源,負債有期限且面臨一定的償還利息的壓力,可能會存在企業的財務績效下降。企業財務績效與研發費用呈正相關關系,因為企業投資于新的研發,會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促進企業財務績效提升。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對財務績效有正向影響。財務績效與市場化程度之間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企業環境績效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環境績效越好,那么企業的財務績效越好,二者呈正相關關系,說明化工企業在提升環境績效時造成的成本低于環境績效所帶來的收益,促使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向相同的方向變化。基于以上分析,支持了假設1。
(四)調節效應分析
本部分在模型(1)中加入調節變量政府監管以及政府監管與環境績效的交乘項,對假設2政府監管對企業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的調節效應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調節效應檢驗
本文首先對交乘項進行去中心化處理以消除共線性。在只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加入環境績效和政府監管指標以及去中心化后的二者的乘積項,R2進一步提高,模型(2)整體擬合R2為0.24左右,擬合程度較好;F值是8.87,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模型(2)總體有效。此外,各變量間的方差膨脹因子VIF計算所得均值為1.17,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通過對總體數據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單位營收排污費的系數是-0.219,環境績效和財務績效呈顯著正相關,假設1可得相應驗證。在5%的顯著水平上,EPI與PITI的交乘項系數是-0.155,而環境績效與政府監管的交乘項為正,說明政府監管起到了調節作用。更為嚴格的政府監管,對于化工業企業環境績效和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調節作用更為明顯,因此假設2成立。說明政府監管強度越大,越能為企業進行環境治理提供良好的環境,促使企業提高自身的環境績效,最后達到環境與經濟雙贏的狀態。
(五)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可能存在環境績效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具有滯后性以及內生性問題,本文首先從數據出發,將解釋變量環境績效的衡量指標滯后一期以后,對回歸分析結果進行檢驗。將環境績效數據滯后一期后,保證其他變量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再次驗證了在1%的水平上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為正相關,以上結果與假設1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其次從分析方法出發,把調節變量調整為二分類變量,使用分組回歸分析方法檢驗調節效應的結果,將調節變量政府監管由原來的連續變量轉化為分類變量,保證其他變量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重新進行調節檢驗,整體費雪Z絕對值大于1.96,且達到5%顯著性水平,表明調節效應顯著。
五、結論和建議
本文以2018—2019年我國化工行業的174家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將政府監管作為研究對象所處的背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化工企業的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二是政府監管在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根據上文研究結果,為達到財務績效與環境績效的協調發展,本文提出下列建議:第一,化工業企業環境績效水平層次不一,盡管實行了環保稅,說明每個企業的環保意識水平差距還是很大,可以在企業內部組織針對環境績效的培訓教育,企業內部管理者應加強交流,提高管理層環保意識。第二,通常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如果提升環境績效的成本較高,再加上政府對違反環境政策監管不夠嚴格,那么有些企業就會冒險去鉆法律漏洞。因此,政府部門應該利用行政手段,加強對企業污染行為的監管,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企業是否按照相關環境績效評價體系的要求進行環境保護或污染防治。
本文的相關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環境績效指標選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及片面性,相較于國外,國內對于環境績效研究的歷程較短,目前還未形成較為全面及規范的環境績效評價體系,對環境績效用環保稅與營業收入的比值來代替還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二是實證研究的樣本較少。由于環保稅從2018年剛開始實施,所選用的數據為2018和2019兩年的數據進行分析,進行剔除后只有174個有效的樣本數據,可能因為樣本規模較少,不能普遍代表整個化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