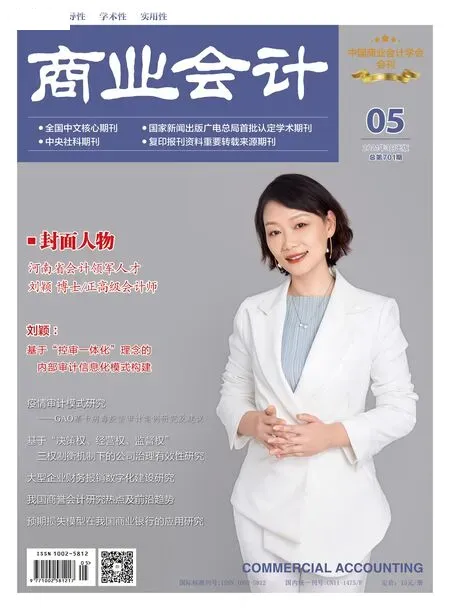風險投資參與對我國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的影響
楊園園
(廣東財經大學 廣東廣州 510320)
一、引言
風險投資(Venture Captical)通過股權投資的方式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創新性企業)提供融資幫助,并采用首次公開上市(IPO)、管理層收購、公司合并等方式退出以獲取投資回報。風險投資的參與不僅為參股企業提供了發展資金,而且通過后續的監督和管理為其提供增值服務,對推動企業發展、助力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風險投資的概念引入我國,經歷了探索、興起與發展,風投機構數量從1994年的17家發展到2018年的22 887家,風險投資機構管理金額也從1994年的22億元增長至2018年的89 969.55億元,呈現出持續增長的態勢。
風險投資通過退出方式獲取投資回報,其中首次公開發行的方式退出能為風投機構帶來豐厚的投資回報,因此也被視為最重要的退出方式(曹麒麟等,2012)。2009年10月30日我國設立創業板,為創新性中小企業提供了更為多元的融資渠道,也為風險投資提供了更佳的退出渠道。截至2018年年底有48.04%的創業板上市公司在上市前接受了風險投資。創業板有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創新型國家的建立;但創業板新股普遍表現出二級市場抑價現象(郭海星,2011),即IPO抑價。IPO抑價指首次公開發行新股的發行價明顯低于首日上市的收盤價,其主要根源來自信息不對稱。風險投資作為創業板企業IPO過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有關風險投資對IPO抑價的研究也得到了廣泛關注,但結果不盡一致。
本文將從兩方面研究風險投資參與對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的影響,一方面探討風險投資參與對創業板企業IPO抑價度的影響,進一步論證風險投資在我國是否發揮了其認證作用;另一方面從風險投資機構特征出發,探討風險投資機構特征對IPO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對風險投資的完善提出建議。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分析
IPO定價效率體現了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有效的市場能夠充分利用信息,發現資產價值。在IPO定價效率測度方面,主要有三種方式:(1)采用IPO抑價,通過計算股票發行價與首日收盤價之間的差異,差異越小表明IPO定價效率越好。(2)采用配比公司的價格乘數模型。(3)測算新股發行價和內在價值偏離程度,使用隨機邊界、內在折價率(李曜、王秀軍,2015)。因此對于IPO抑價的研究有助于進一步了解我國資本市場IPO定價效率。
關于風險投資參與對企業IPO抑價影響存在多種不同的理論支持(紀玲瓏,2020;李家敏、徐惠珍,2019)。認證假說(Megginson and Weiss,1991)認為,風險投資作為專業機構投資者,擁有更為專業的篩選能力,能夠發掘有價值的創新型企業,因此風險投資參與能夠發揮第三方認證的作用。監督假說(Barry et al,1990)認為,風險投資通過股權形式參與到公司管理當中,對企業進行監督,并為企業提供針對性的增值服務,能夠進一步發揮和提升企業價值。此外,市場力量假說認為風險投資機構能為所投企業在IPO過程中帶來更權威和知名度的承銷商、保薦機構、審計師等,從而為企業帶來更高的市場估值,進而風投機構的參與使所投企業IPO抑價下降。
另一方面,IPO上市也是風險投資機構擴大知名度的重要途徑,在“逐利動機”下風險投資機構會以IPO折價為代價推動企業較早上市。在我國IPO資源稀缺,風險投資機構一旦獲得IPO退出機會,其收益將會獲得成倍增長,在機會主義動機下也將推動企業盡早IPO。并且,蘇巍(2015)以創業板公司為數據表明,風險投資并未發揮價值增值作用,對公司的創新作用并不顯著,也進一步表明了風險投資在我國的“逐利動機”。
同時基于實證研究的結果也存在不一致的結果。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風險投資的參與提高了企業IPO抑價程度(王月溪、王萍,2011;張凌宇,2006),并且有風險投資參與公司在IPO后業績即大幅下降。朱元甲、李陽(2012)等認為風險投資對企業IPO抑價率沒有顯著影響。馮慧群(2016)認為風險投資參與可以抑制IPO抑價。此外,王澍雨(2017)認為風險投資對創業板IPO抑價率有顯著影響但是影響趨小。同時,陳工孟等(2011)發現在不同市場上風險投資對于中資企業IPO抑價率的影響具有差異。寇祥河等(2009)也發現風險投資在美國市場上存在認證功能,而在我國中小板市場不存在該種功能。劉林戈(2016)研究表明IPO退出已經成為了我國風險投資的主要退出通道,IPO退出能夠給予風險投資更為豐厚的投資回報,并更能激發風險投資機構對初創期創新性企業的投資。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基于認證和監督假說,風險投資參與具有篩選作用和監督作用,通過認證和后續監督管理,能夠更好地推動優質企業價值增長,并發揮向市場傳遞信息的作用,降低信息不對稱現象。同時,隨著我國資本市場多層次且市場化的發展,風險投資的規模和經驗得到快速的積累與發展;更多的創新性企業尋求風險投資的參與,也為風險投資篩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有助于更好地發掘有價值的企業。創業板市場作為創新性企業融資的重要市場,將進一步體現風險投資參與對創新性企業的認證監督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風險投資參與能夠有效抑制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現象。
在以上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風險投資成立年限、參股比重和機構數量特征對抑制IPO抑價效果上是否存在差異,進而探討何種風險投資特征有助于抑制IPO抑價現象。風險投資機構后續管理和資金規模擴展都需要建立在聲譽、經驗的基礎上;同時,根據逐利動機,相對于成立時間較短的風險投資機構,成立時間較長的機構逐利動機也會減弱,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風險投資機構成立年限越久對抑制創業板企業IPO抑價越具有顯著效果。
參股比重代表了持股人在企業的話語權,掌握較大的所有權能夠幫助持股人更好地管理企業。針對風險投資而言,較大的參股比重能更好地發揮其后續監督管理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風險投資機構參股比例越大對抑制創業板企業IPO抑價越具有顯著效果。
發展前景好的企業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對于風險投資也如此。部分企業會同時受到多家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風險投資對企業的認可,也能發揮其認證作用,因此,提出假設4:
假設4:風險投資機構數量越多對抑制創業板企業IPO抑價越具有顯著效果。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18年創業板IPO上市的所有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按照IPO抑價率對樣本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終樣本總體包括723家創業板IPO上市企業,其中348家企業上市前有風險投資參與,占比達到48.1%。本文所使用的風險投資數據來自清科集團私募通數據庫、投資界數據庫和上市招股說明書,公司數據和大盤指數來自同花順交易軟件、巨潮網和CCER數據庫。
關于風險投資參與企業采用手動收集方式確定,首先通過企業上市招股說明書確定上市前企業前十大股東;然后參照孫建華(2013)等方法對其中的法人投資者進行風險投資性質判斷:(1)通過私募通數據庫、投資界數據庫查詢法人投資者是否為風險投資機構。(2)對于數據庫查詢不到的法人投資者,通過查詢上市招股說明書判定其主營業務,如果主營業務為“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即確定為風險投資參與。(3)對于招股說明書未披露或主營業務不詳細的法人投資者,通過百度信用搜索其主營業務,對主營業務是“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即確定為風險投資性質的股東。
(三)變量定義與模型設計
1.被解釋變量。根據張豐(2009)研究成果,加入市場因素,用IPO調整抑價率來表示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程度。通過采用市場指數來表示市場因素,由于創業板指數推出時間較晚,所以選用深證成指來代替。

其中,UP表示IPO調整抑價率,P1表示企業股票首日上市的收盤價,P0表示企業股票的發行價,M1表示該企業股票首日上市當天所對應的深證成指的收盤指數,M0表示該企業股票發行日對應的深證成指的收盤指數。
2.解釋變量。VC作為虛擬變量,用來表示企業IPO前是否接受到風險投資,如果企業在IPO前接受到風險投資取1,反之取0。old表示風險投資機構的成立年限,用風險投資機構從成立到企業上市當年的年限計算;weight表示風險投資在上市前所占企業股本比重,通過企業上市招股說明書前十大股東明細,計算上市前前十大股東中風險投資機構參股總比重;number表示企業上市前十大股東中風險投資機構所占的數量。
3.控制變量。參考相關文獻選擇發行規模(sales),公司年齡(age),中簽率(lot),首日換手率(turnover),上市前一年凈資產收益率(roe),上市前一年的資產負債率(lev)和主承銷商聲譽(rep)作為控制變量,并對企業所屬行業(industry)和上市年份(year)進行控制,統稱為X。
其中,發行規模用發行股數做對數處理表示;主承銷商聲譽作為虛擬變量,根據歷年證券業協會公布的證券公司排名,排名前十的,表示具有較高聲譽,取值為1,反之取0。
4.模型假設。為了驗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模型(1)用來檢驗假設1,模型(2)—(4)用來檢驗假設2、假設3、假設4。其中,X表示各類控制變量;模型(5)加入全部風險投資特征變量,對風險投資年限、持股比重和機構數量進行統一研究。
(四)描述性統計
首先,對樣本區間內的數據進行描述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總體IPO調整抑價率均值達到38.1%,體現出創業板存在較高IPO抑價現象;同時,總樣本企業平均年限為12.36,IPO發行規模對數為16.91,中簽率均值為0.7%,首日換手率均值為33.8%,凈資產收益率均值29.2%,資產負債率均值37.6%;此外,總樣本中有38%的企業上市選擇聲譽較好主承銷商。

表1 總樣本的描述統計
然后,以是否有風險投資參與劃分總樣本進行描述統計。無風險投資參與企業IPO調整抑價率均值為37.9%,有風險投資參與企業IPO調整抑價率均值為38.3%,反而相對無風險投資企業有所高出,與假設1相違背。同時,相對于無風險投資參與而言,有風險投資參與企業的發行規模、年限、資產負債率和主承銷商聲譽均值都略高。
最后,對風險投資參與企業中風險投資特征進行描述統計。結果表明,355家風險投資參與企業中風險投資機構年齡平均為7年;參股比重平均為12.3%,參股比重較小;平均每家風險投資參股企業中有1.8家風險投資參與。
四、實證分析
由于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發現模型存在異方差現象,采用FWLS對其進行修正,結果如表2。模型(1)列示了風險投資參與對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的影響,vc的系數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假設1不成立,說明我國風險投資參與并沒有降低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現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IPO抑價率,并未真正發揮風險投資的認證和監督作用。模型(2)(3)和(4)分別解釋了風險投資的年限、持股比例和機構數量特征對IPO抑價率的影響。首先,old的系數顯著為正,表示風險投資機構成立年限越高反而會增加IPO抑價率,假設2不成立。其次,weight的系數為負,與假設3認為風險投資參股比重越大越有助于抑制IPO抑價一致,但是該系數并不顯著。最后,number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假設4不成立。模型(5)統一用風險投資的特征對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率進行研究,發現持股比例和機構數量的系數為負,說明兩者能起到降低抑制IPO抑價的作用,但是兩者系數不顯著,導致該作用效果有限。

表2 風險投資參與及風險投資特征對IPO抑價影響
通過模型(1)—(5)可以看出,中簽率(lot)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中簽率能夠起到降低IPO抑價的效果;首日換手率(turnover)的系數顯著為正,符合現實意義,二級市場的情緒會帶動股價從而影響IPO抑價率。由此發現我國創業板市場中,風險投資并未發揮其認證和監督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IPO抑價現象。導致出現以上回歸結果的原因:一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資本市場并不健全,市場當中散戶居多,由于缺乏相應的投資知識積累使得其市場投機動機顯著;同時由于缺乏廣泛的機構投資者參與或協助散戶投資者進行市場動態及信息的正確解讀,導致風險投資參與信息被散戶投資者過度解讀,導致我國證券市場股價的不合理。二是相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我國風險投資市場起步較晚,在投資過程中我國本土的風險投資機構所具備的篩選和服務能力存在不足,并且導致投資出現向中后期偏移的現象,使得逐利意愿更強。
五、穩健性檢驗
由于本文采用FWLS的多元回歸方式,有效地消除了回歸當中的異方差現象,又由于IPO抑價率是IPO定價效率的測量方式之一,為此本文將采用被解釋變量替代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PEG法測算新股內在價值,通過內在價值與新股發行價之間的偏離程度,進而代替IPO抑價率進行穩健性檢驗,保持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不變。結果表明:風險投資的年齡(即成立年限)系數是0.0923,為正且顯著,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風險投資年限越久越會降低創業板IPO的定價效率,與原結果一致;風險投資持股比重系數為0.00785,表明風險投資持股比重對創業板企業IPO定價效率與原回歸結果一致,為不顯著;風險投資機構數量特征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聯合投資能夠顯著提高創業板IPO定價效率,與原結果不一致。通過對被解釋變量的替代依舊表明,在我國風險投資并未能真正地發揮認證和監督作用。
六、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9—2018年在創業板上市的723家企業為樣本,研究風險投資參與對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1)風險投資參與并未降低創業板企業IPO抑價現象,反而提高了企業IPO抑價程度,說明在我國創業板市場,風險投資參與并未真正起到認證和監督作用。(2)進一步對風險投資機構特征進行研究,發現風險投資機構的年限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IPO抑價率,而風險投資機構的持股比例和機構數量在抑制IPO抑價方面作用有限。
研究結果表明,我國風險投資參與并未發揮其認證和監督作用。可能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資本市場本身并不完善,市場存在大量非理性散戶炒新股、投機現象顯著,同時由于缺乏發達市場上廣泛的機構投資者,使得市場信息缺乏正確解讀,導致風險投資參與信息被散戶投資者過度解讀,進一步助推股價。二是我國風險投資市場起步較晚,風險投資機構成立年限較短,在投資企業篩選和服務方面存在經驗不足,并且投資出現向中后期偏移的現象,偏重短期利益。因此,在未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方面,要進一步注重發展質量,鼓勵和發展機構投資者,助推風險投資,積極提倡對早期創新性企業投資;風險投資機構也要進一步積累經驗,全面助力創新性企業,才能發揮其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