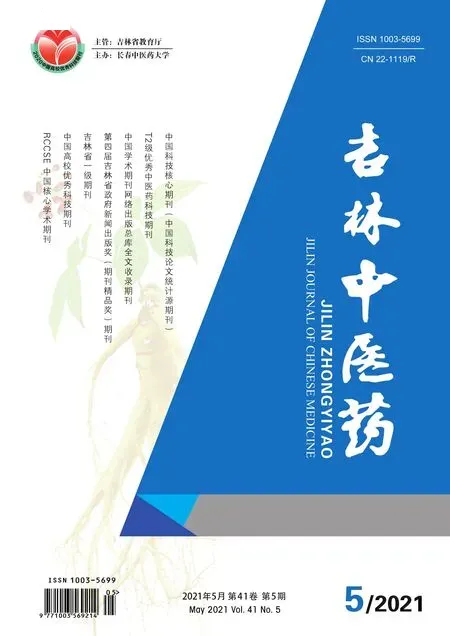仝小林運用黃芪、當歸、益母草氣血水同調經驗
唐 程,王 涵
(1.長春中醫藥大學,長春 130117;2.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絕經后女性多出現乏力、怕冷、情志異常、睡眠障礙、骨節疼痛、顏面肢體浮腫緊脹等不適癥狀,現代醫學多認為與絕經后雌激素水平變化有關[1-2]。中醫認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腎中精氣的衰減會導致氣血不足,并伴有血瘀、水停等諸多病理產物出現,故疾病的發生多以虛實夾雜、正虛邪實為核心,正虛以腎虛、肝虛、脾虛為主,氣血陰陽皆可不足;邪實以氣滯、血瘀、痰濕為主[3]。仝小林院士提出態靶辨證理論體系,認為這類人群多以虛態、瘀態、水壅態為主,以此為立足點調整偏態,在診治疾病過程中強調精準治療,從辨病、辨證到用藥劑量,抓住核心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針對中老年女性的主要病態,以黃芪、當歸、益母草為調態打靶基礎方,補虛的同時兼顧調氣、活血、利水,氣血水同調,虛實兼顧,標本結合,共奏良效。
1 年老多虛,氣血水失調為病機
中老年女性因天癸乏源,氣道、血道、水道、谷道四道虛損[4],可出現一系列非器質性病理表現。《內經》曰:“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可見年近七七,女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其中以虛態最為顯著。仝小林認為,中老年女性氣血虧虛,由衰老導致的虛是此病態的中心環節,這其中氣又是影響血瘀和水停的關鍵因素。氣的鼓動無力、生化乏源會導致血液瘀滯,水液壅停,二者均可視為由虛所導致的病理產物。反之,血液、水液運行不暢又會進一步加重氣機的郁滯。氣具有生血、行血、攝血功能,氣旺則血充,氣虛則血少,在血少的同時,氣對于血液的推動力也有所減弱。脾主運化水液,脾氣虛,運化能力下降;肺主通調水道,肺失宣肅,通調失職,累及于腎,均可造成水液代謝失于常度。
2 意在周流,同調氣血水為治則
仝小林指出,中老年女性所特有的一系列癥狀以虛態為起始,多以虛、瘀、壅停并見。氣虛則乏力倦怠、汗出異常;肝失疏泄、肝血不足,又合氣虛鼓動無力,出現氣虛血瘀,患者表現為心煩易怒、失眠、胸悶等;中老年女性腎氣漸衰,溫煦氣化能力下降,肝脾不調,微循環受阻,導致水液壅停在組織間隙,出現顏面、手指有緊脹感,下肢輕度浮腫且時與情志相關。由于病態復雜且多變,單純以虛為著力點,盲目施以大補,難免造成氣機進一步壅滯,因此在治療上應協調補氣、調(活)血、利水三方力量,以此為基本治則,以求氣血周流。
黃芪性甘味微溫,歸脾、肺經,具有補氣升陽、固表止汗、托毒排膿、斂瘡生肌等功效,常用于治療內傷勞倦、脾虛、氣虛、血虛等諸多氣虛血虧之證,另對于癰疽等諸多“毒癥”亦有顯著療效。歷代醫家常以黃芪為主藥,取其補氣之功行血熄風,用以治療正氣虧虛、氣血陰陽不足且升降逆亂所發之中風[5]。仝小林在臨證應用中取黃芪的補虛作用以調虛態,同時借用其補氣所產生的推動之力產生活血、行水之效。現代藥理學研究證實,黃芪中的主要成分黃芪甲苷具有免疫調節作用,還可起到抗氧化、抗炎、調節糖脂代謝等功效[6]。
當歸味甘、辛,性溫,歸心、肝、脾經,具有補血調經、活血止痛、潤腸通便之功,其中最善補血活血,有血中之圣藥的美稱,可用于治療月經不調、血虛受寒、虛寒腹痛、跌撲損傷、腸燥便秘等。《名醫別錄》對當歸有如下記載:“溫中止痛,除客血內塞,中風痙,汗不出,濕痹,中惡客氣,虛冷,補五臟,生肌肉”[7]。仝小林常取當歸活血、散寒、和血之功為靶藥治療血管疾病中血虛寒厥、脈絡郁滯之證[8]。藥理學家已從當歸中分離出揮發油、多糖類、有機酸等多種化學成分,其中揮發油中的苯酞類具有改善心血管系統、鎮痛、保護神經等作用[9]。
益母草味苦、辛,性微寒,歸肝、心包、膀胱經,可活血調經、利尿消腫、清熱解毒,臨床上多用于治療月經不調、水腫、癰瘍腫毒等。《本草綱目》中記載,益母草對于“胎漏難產,胎衣不下,血暈,血風,血痛,崩中漏下,尿血”有治療作用。仝小林認為益母草可治經期水腫、水鈉潴留型高血壓、肝硬化腹水等[10]。目前已從益母草中分離出包括二萜類、生物堿、揮發油、黃酮類在內的百余種化合物,其中鹽酸益母草堿具有利尿、抗血小板聚集、抗氧化等作用。研究[11]表明,益母草水提取物能明顯降低急性腎功能衰竭模型大鼠的肌酐、尿素氮水平,改善腎功能。
3 用量精準顯良效
《中國藥典》記載,黃芪臨床應用劑量為9~30 g,當歸為6~12 g,益母草為9~30 g。中醫治病用藥,應因證施量、隨癥施量,掌握好劑量進而精準打靶是制勝關鍵。在以氣血水同調為核心的三味小方中,仝小林運用黃芪的常用劑量為15~30 g,當歸為9~15 g,益母草為15~30 g,療效明確,未見毒副作用及不良反應。益母草小于30 g 以活血為主,30 g以上破血之力顯著,如在尚未絕經女性中使用,經期應關注經量,以防崩漏。根據患者實際情況,若氣滯明顯,胸脅脹痛較甚者,可配伍香附調氣;食欲較差,大便不調者,可配伍人參、白術調脾胃;腎陽不足,怕冷明顯者,可配伍淫羊藿補腎溫陽;若合并高血壓,可配伍茺蔚子、車前子利水降壓。
4 病案舉例
陳某,女,52 歲,2020 年11 月9 日初診,身高:155 cm,體質量:57 kg,BMI:23.73 kg/m2。主訴:全身怕冷16 年余,雙下肢及膝關節為甚,加重1 年余。現病史:患者訴16 年前生產后出現全身怕冷癥狀,2020 年春節前后加重,受涼后出現四肢關節游走性疼痛。2020 年2 月至當地中醫院就診,查“抗O”:430.0 IU/mL,生化檢查未見異常,血常規PLT:103×109/L,血沉26 mm/h。后四肢及腹部出現大量圓形紅斑,膝關節疼痛,下蹲不能,遂再次至當地中醫院就診,診斷為“風濕熱”,予中藥方劑“祛風除濕,溫經通絡止痛”,并予長效青霉素1 支/月治療,后感疼痛時作,紅斑改善不明顯,2020 年6 月予青霉素靜點,阿莫西林口服,后紅斑消失,反復就診于該院門診,間斷口服中藥湯劑。2020 年10 月5 日復查“抗O”:35 IU/mL,血常規PLT:95×109/L。刻下:全身怕冷,雙下肢及膝關節明顯,四肢關節游走性疼痛,乏力,易疲倦,四肢麻木緊脹,記憶力減退,脫發、白發,耳鳴,眼睛干澀,眼疲勞,偶有口苦。舌細顫,有齒痕,舌底瘀,苔淡黃微膩,脈細弦澀,尺弱。既往史:先天性膽管狹窄,2007 年行膽囊全切術,常年患婦科炎癥,小囊腫多發,夏季濕疹。12 歲時有傷寒病史。2007 年輸血史,無過敏。末次月經時間:2014年10 月16 日,月經提前5~7 d,量少色黑。中醫診斷:痹病(行痹),方藥組成:黃芪30 g,當歸15 g,益母草15 g,淫羊藿15 g,香附15 g,茯苓15 g,麩炒椿皮30 g,杜仲15 g,敗醬草30 g,鹿銜草15 g,露蜂房9 g,桂枝15 g,豨薟草15 g,生姜3 片。服上方2.5 個月,怕冷、四肢關節游走性疼痛減輕40%,乏力減輕30%,受風后易出現上腹部紅斑,頻次較前減少,眼睛干澀、目脹,雙下肢微有浮腫,自覺上身熱,后背怕風、發涼,耳鳴,納差,無饑餓感,大便稀,每日1 次,夜尿1 次,胃不適,易嘔,反酸,心悸。尿急,量少,眠差,多夢。上方加羌活、獨活各15 g,五味子15 g,桂枝改為30 g,茯苓改為30 g,豨薟草改為30 g,鹿銜草改為30 g。繼服1 個月,關節疼痛、怕風消失,乏力、疲倦明顯好轉,耳鳴、目脹、雙下肢浮腫消失。
按:患者早年生產后或因產后體虛、復感風寒進而出現全身怕冷。正氣不足復加邪氣留存于血脈、經絡、筋骨導致病勢纏綿,伴隨年齡增長、天癸衰耗,以氣虛、血瘀、水液代謝失常等諸多原因導致的復雜癥狀尤其困擾。氣的不足不僅無法發揮氣化、固攝、防御、榮養等功能,也使血液、水液無以溫煦和推動,發生血的瘀滯、水的壅停,患者出現以怕冷、乏力、記憶力減退、關節疼痛、顏面肢體緊脹為主的癥狀,舌細顫,有齒痕,舌底瘀,苔淡黃微膩,脈細弦澀,尺弱均為氣血虧虛、氣血瘀滯、水液失調之象。以黃芪、當歸、益母草為基礎方同調氣血水,助氣血周流,輔以淫羊藿補腎溫陽、祛風除濕,露蜂房、鹿銜草、豨薟草止痛利關節,香附疏肝解郁助調氣,桂枝溫通經脈,杜仲補肝腎,強筋骨,茯苓健脾利水,寧心安神。全方主要針對氣血水的不足與失調,調病態,糾癥靶,臨證應用,療效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