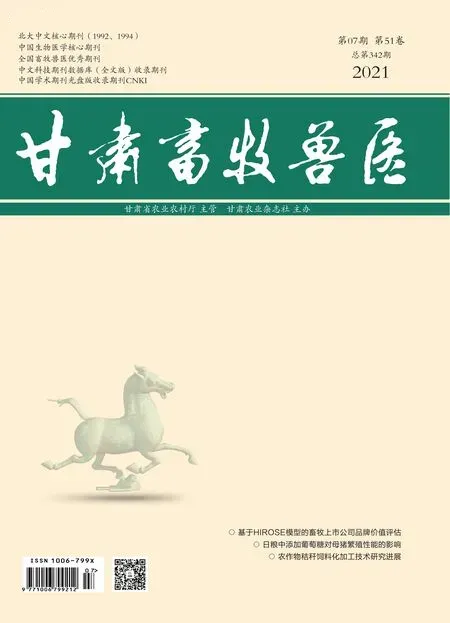鴨疫里默氏桿菌的研究進展
黃 寧
(西南大學 動物醫學院,重慶 402460)
鴨疫里默氏桿菌(Riemerella anatipestifer,RA),原名鴨疫巴氏桿菌,屬于黃桿菌科里氏桿菌屬,是引起1~8周齡,尤其是2~3周齡雛鴨傳染性漿膜炎的病原菌[1],已成為嚴重危害養鴨業的細菌性傳染病之一。自1982年郭玉璞等[2]于北京郊區鴨場中分離出鴨疫里默氏桿菌后,我國各養鴨地區出現RA感染的報道層出不窮。RA感染后雛鴨主要表現生長發育受阻、肝周炎、纖維素性心包炎和氣囊炎,嚴重者甚至死亡。此外,RA還可以侵害雛鵝、野雞、火雞等動物。目前國際認可的RA血清型有21個[3-5],由于其血清型多樣,且不同血清型菌株缺乏交叉免疫保護力,導致免疫預防效果不佳、極易產生耐藥性。由此可見,RA給養鴨及其他養禽業帶來了極大挑戰。
鴨疫里默氏桿菌的防控對養鴨業的穩定持續發展尤為重要,本文對鴨疫里默氏桿菌的血清型、耐藥機制、檢測方法與治療措施進行了綜述,以期為進一步防控鴨疫里默氏桿菌疾病奠定理論基礎。
1 鴨疫里默氏桿菌的流行情況
鴨疫里默氏桿菌病的傳染源主要是被鴨疫里默氏桿菌感染而發病的鴨、鵝等動物。RA可以通過空氣、被污染的飼料和飲水等途徑傳播,其主要傳播方式包括消化道傳播、呼吸道傳播,其次是由于皮膚破損而感染[6]。該病屬于接觸性、細菌性傳染病,在我國呈流行性分布,無明顯季節性。
鴨疫里默氏桿菌病的最早報道是在美國紐約州長島的養鴨場,在當地稱作“新鴨病(New duck syndrome)”,后也被稱作“鴨敗血癥(Duck septicemia)”。由于其典型病理表現為全身的漿膜面均可見纖維素性滲出物,且大多伴有炎性細胞浸潤,Dougherty針對其典型的病理變化將該病命名為“傳染性漿膜炎”[1]。
我國首次在北京發生鴨疫里默氏桿菌病,此后該病在全國各地,尤其是養鴨密集地區均有發生。如2017年雍燕等[7]于廣東3個地區疑似患鴨疫里默氏桿菌病鴨中分離出16株對部分抗生素耐藥的鴨疫里默氏桿菌;2020年陳國權等[8]于貴州省三穗縣暴發大規模雛鴨死亡的養鴨場中分離出11型血清型的鴨疫里默氏桿菌,首次證明貴州省存在11型RA,并通過耐藥基因檢測出分離菌為5重耐藥菌株;2021年董洪燕等[9]于江蘇從鵝源分離出2型血清型的鴨疫里默氏桿菌,通過藥敏試驗結果顯示所分離的RA多重耐藥性嚴重。從各地區相關報道來看,我國RA的耐藥現象不斷出現,多重耐藥性逐漸成為基本態勢。
2 鴨疫里默氏桿菌的血清型
目前國際公認的RA血清型有21個[3-5],該菌血清型多樣復雜,且各血清型之間免疫交叉保護性差。1969年,Harry等[10]通過平板凝集試驗將分離得到的鴨疫里默氏桿菌鑒定為16個血清型,并命名為A-P型。此后,隨著其他血清型的相繼發現,RA被重新用阿拉伯數字分為21個血清型[11]。2003年,程安春等[12]通過玻片凝集試驗和瓊脂擴散沉淀試驗,對我國29個省分離到的1 842株RA進行血清學鑒定,發現了4株血清型,分別命名為22、23、24和25型血清型。2005年,張大丙[13]采用瓊脂擴散沉淀試驗,從只與血清10型的抗血清發生凝集反應的分離株中分離出4個亞型,分別是C2、C449、C459和C598。隨后,張大丙等[14]又用凝集試驗和瓊脂擴散沉淀試驗鑒定出從河北鴨場分離的13個RA株可能屬于一種獨立的血清型。這些發現刷新了我國及國際的鴨疫里默氏桿菌血清型數據,為進一步有效防控鴨疫里默示桿菌病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年來,我國流行菌株主要以1型血清型和2型血清型為主,其次是血清6型、10型。山東、廣東、廣西、湖北等地區的優勢血清型為1型,浙江、貴州等地區的優勢血清型為2型,江蘇、安徽的優勢血清型包括1型、2型[15]。部分地區的RA流行菌株暫不確定。
3 檢測方法與防治措施
3.1 檢測方法
目前,可根據患病動物的臨床癥狀、病理剖檢變化進行初步診斷,確診需要進行實驗室診斷。
3.1.1 臨床癥狀 該病可根據病程長短分為最急性型、急性型、亞急性型和慢性型。急性型發病急,較少見。慢性型主要見于日齡大的雛鴨[16]。患鴨主要表現為精神沉郁,食欲減退,消瘦,生長遲滯,喜臥惡動,縮頸垂翅;呼吸道癥狀主要見于咳嗽、打噴嚏,鼻、眼等天然孔可見大量黏液性、漿液性、膿性分泌物;神經癥狀表現為角弓反張,步態不穩,頭頸歪斜,呈劈叉姿勢,抽搐痙攣,最終死亡。患病鵝等其他易感禽類癥狀與患鴨相似。
3.1.2 病理剖檢變化 該病的病理變化主要以纖維素性物質滲出為主,常見典型癥狀有心包炎、肝周炎、氣囊炎等[1]。此外,可見肝、脾腫大,被膜顯著增厚,表面被覆灰白色或灰黃色、易剝離的纖維素膜。大多數急性型病例可見心臟腫大,表面被覆灰白色絨毛狀的纖維素性滲出物,且伴有大量炎性細胞浸潤;大多數病鴨氣囊也可見灰白色纖維素性滲出物,且炎性細胞浸潤;少數病鴨生殖系統可見病變,如輸卵管膨大,橫切可見內含大量豆腐渣樣的白色干酪樣物質;關節液明顯增多,關節(尤其是跗關節)腫大;大腦為纖維素性腦膜炎,也可見大量纖維素性滲出物和炎性細胞浸潤;極少數病例肺臟出現充血、出血和實變等明顯病變[17]。
3.1.3 鑒別診斷 由于鴨疫里默氏桿菌病、大腸桿菌性敗血癥和鴨沙門氏菌病理變化均可見漿膜炎病理變化,故三者容易混淆,需要通過細菌的分離培養和生化試驗進一步鑒定。
3.1.4 實驗室診斷 一是細菌的分離與鑒定。無菌條件下采集病鴨的腦組織、心血、肝臟等病原菌較豐富的部位,分別接種于普通瓊脂、胰酶大豆瓊脂培養基(TSA)、巧克力瓊脂培養基、鮮血瓊脂培養基和麥康凱瓊脂培養基,置于CO2培養箱或蠟燭缸,37℃培養24~48 h[1,6,18]。
肉眼觀察菌落形態特點,鴨疫里默氏桿菌在普通瓊脂培養基、麥康凱瓊脂培養基上不生長(該特點可與大腸桿菌區別),在巧克力或TSA培養基上可見呈灰白色、圓形隆起、奶油狀、表面光滑、濕潤、直徑1~2 mm的菌落。挑取巧克力瓊脂培養基上的單個疑似菌落涂片,采用革蘭氏染色或瑞氏染色等方法染色,鏡檢,可見鴨疫里默氏桿菌呈短桿狀或橢圓形,散在、成雙或短鏈排列,革蘭氏染色呈陰性、瑞氏染色呈兩極著染[1]。
二是生化試驗診斷。挑取平板上的單個疑似菌落分別接種于生化反應管中,37℃培養24~48 h,與多殺性巴氏桿菌病不同,鴨疫里默氏桿菌不發酵葡萄糖、蔗糖。硝酸鹽還原、VP試驗、甲基紅試驗、尿素分解試驗等均呈陰性,不產生硫化氫。觸酶試驗、氧化酶試驗呈陽性。無溶血現象,可液化明膠[1]。
三是藥敏試驗診斷。由于大多數養殖場存在抗生素濫用的現象,不同血清型的RA對多種抗生素均產生不同程度的耐藥性。因此,RA耐藥性的鑒定對養殖場合理防治鴨疫里默氏桿菌病顯得尤為重要。主要采用K-B紙片擴散法,在已涂布分離菌的TSA平板表面貼上不同的抗生素紙片,48 h后通過測量各抑菌圈直徑大小判斷分離菌的耐藥性。抑菌圈直徑大于20 mm,非常敏感;抑菌圈直徑為15~20 mm,高度敏感;抑菌圈直徑為10~15 mm,中等敏感;抑菌圈直徑小于10 mm,低等敏感甚至不敏感[6]。
四是免疫學診斷。目前國內外常用的血清型鑒定方法包括玻片凝集試驗、試管凝集試驗和瓊脂擴散沉淀試驗[19,20]。1982年,Brogden[21]等認為瓊脂擴散沉淀試驗可以有效進行血清型分型,且通過稀釋瓊擴抗原可避免交叉反應。1991年,Sandhu和Leister[22]提出采用細菌洗滌的玻片凝集試驗可以快速有效檢測出大量野外分離菌。
近年來,Bin Huang[23]等建立了用RA的P45 N末端重組蛋白作為包被抗原的間接ELISA檢測方法,對RA早期感染進行檢測。2004年,程安春[24,25]等以采用超聲波裂解的血清1型、2型、4型RA作為包被抗原,建立血清1型、2型、4型的RA抗體水平檢測的間接ELISA檢測方法。這些新建立的ELISA法具有定性或定量檢測血清中的抗體水平、判定疫苗免疫效果、判定是否RA感染、特異性強等特點。
五是分子生物學診斷。PCR法也可用于RA鑒定,具有操作簡便、快捷、特異性強、靈敏度高等特點,適用于大量樣本的檢測。2002年胡清海[26]等以RA的15型CVL110/89株編碼42-kDa主要外膜蛋白的基因序列設計合成一對引物,建立了RA的PCR檢測方法,并利用該法對7個血清型的RA純培養菌的DNA成功擴增出809 bp的DNA,而對照組的大腸桿菌和沙門氏菌純培養物DNA擴增結果呈陰性。2005年,Hsiang-Jung Tsai[27]等建立了16S rRNA法,并利用該法擴增了18株臺灣株和10株參考株。
3.2 防治措施
3.2.1 日常預防措施 加強飼養管理和生物安全措施。對于規模化養殖場,應采取全進全出的管理模式。合理控制飼料配比,飼喂營養充足的飼料,適時補充維生素和礦物質等營養物質,有利于提高機體免疫力。盡量減少各種應激因素,定期進行環境衛生消毒,尤其避免飼料和飲水被污染。避免養殖場鴨群或鵝群接觸野生動物,也可以根據藥敏試驗結果選用合適的抗菌藥物。此外,如果養殖場位于疫病流行區,應及時對動物群體進行疫苗接種。由于RA血清型多樣,且各血清型之間無交叉免疫保護,因此可以制備當地流行菌株的滅活疫苗進行預防接種。
3.2.2 疫病發生時的措施 如果發生疫病,應及時將患病動物群與假定健康動物進行隔離。對患病及病死鴨、鵝等動物尸體和糞便進行焚燒、填埋等無害化處理。對被污染的禽舍環境可以使用高效消毒劑消毒[28]。根據藥敏試驗結果,對患病鴨、鵝進行藥物治療,嚴重者需及時淘汰,防止病原擴散。
4 結論與展望
鴨疫里默氏桿菌在我國養鴨地區廣泛分布,其復雜多樣的血清型和嚴重的耐藥性阻礙著我國養鴨業的健康發展。近年來,我國各地區的RA流行血清型有所變化且不斷發現新的亞型,此形勢對我國防控鴨疫里默氏桿菌病帶來了嚴峻挑戰,應對RA的耐藥機制加強研究,以便進一步為鴨疫里默氏桿菌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有效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