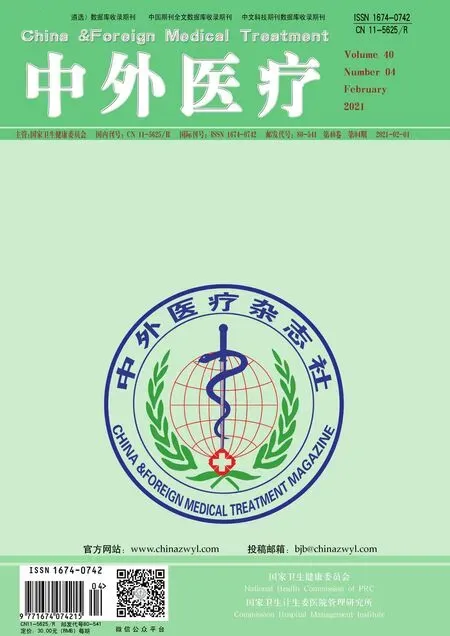顱骨缺損并腦積水的外科聯合手術方案研究
趙志軍,孫智敏
內蒙古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神經外科,內蒙古包頭014010
顱骨缺損多見于神經外科,多發于頭顱骨,部分患者由于火器性穿通傷或開放性顱腦創傷導致,部分患者由于顱骨病變引發穿鑿性破壞傷、去骨瓣減壓手術創傷或切除顱骨病損導致。不超過3 cm或(和)位于顳、枕肌下的顱骨缺損大多無明顯臨床癥狀,較大顱骨缺損可能會出現以頭痛、頭暈及注意力不集中等癥狀為主要臨床表現的顱骨缺損綜合征,部分嚴重患者也可能出現腦膨出和神經定位體征,臨床治療多以顱骨修補術為主要治療策略[1]。腦積水多由于顱內腫物或顱腦外傷引起腦脊液動力學改變進而引發腦室進行性、系統性擴張導致,常伴頭痛、尿失禁及步態站立不穩等典型臨床癥狀,中、重度腦積水可能出現進行性癡呆、大小便失禁及臥床不起等臨床表現[2]。據有相關研究報道[3],腦積水可引發腦萎縮,患者腦萎縮嚴重程度與神經功能障礙程度呈顯著正相關,顱骨缺損并腦積水后應積極采取措施診治。為此該研究方便選取2017年1月—2020年1月內蒙古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68例顱骨缺損并腦積水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探討顱骨缺損并腦積水治療應用外科聯合手術方案的臨床效果,效果滿意,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取內蒙古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收治的68例顱骨缺損并腦積水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治療方法分為研究組(34例)和對照組(34例)。其中研究組男20例,女14例;年齡24~63歲,平均(43.83±11.87)歲;顱骨缺損類型:閉合性23例,開放性11例;顱骨缺損原因:交通意外事故傷22例,跌倒或高處墜落傷6例,顱骨病變導致的穿鑿傷4例,斗毆傷2例;腦積水程度:輕度12例,中度14例,重度8例。對照組男21例,女13例;年齡23~62歲,平均(44.02±12.01);顱骨缺損類型:閉合性22例,開放性12例;顱骨缺損原因:交通意外事故傷23例,跌倒或高處墜落傷6例,顱骨病變導致的穿鑿傷3例,斗毆傷2例;腦積水程度:輕度13例,中度15例,重度6例。兩組性別、年齡、顱骨缺損類型、顱骨缺損原因及腦積水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可比性。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經腦CT檢查結果顯示,腦室出現系統性擴大,腦室間徑/頭頂間徑>0.26;側腦室擴張且周圍存在間質性水腫帶,其前角表現突出;病程不超過3個月;顱骨缺損直徑>30 mm;具有手術指征;分流術前顱內壓在80~180 mmH20;臨床主要表現至少包括以下癥狀中任意一項:行走時步態不穩、認知及意識障礙、注意力不集中、發作性意識喪失伴抽搐、括約肌功能障礙、頭痛、頭暈等;患者及家屬知曉該研究并簽署同意書,該研究經該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
排除標準:處于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合并腦卒中或(和)顱腦腫瘤或(和)凝血功能障礙者;存在認知意識功能異常;拒絕參與該研究;因諸多因素無法參與或無法全程參與該研究者。
1.3 方法
術前兩組均接受生命體征、顱內壓、腦積水病灶情況及身體各部位是否存在感染灶等常規檢查,并根據患者術前病情檢查結果擇一手術方案,確定顱骨缺損側穿刺點、分流管壓力及顱骨修補材料等,如:腦室前角入路需于前額發際內中線旁2.5 cm處作入路點,腦室后角入路需于中線旁3 cm及枕外粗隆上5~6 cm處作入路點,腦室三角部入路需于外耳道上方4 cm及后方4 cm處作入路點;根據腦CT檢查結果中顯示出的腦積水程度和顱內壓選取相應壓力分流管。根據患者顱骨缺損情況選擇鈦板或自己保留的顱骨作顱骨修補材料,并根據腦CT檢查結果中顯示出的骨窗大小制備相應顱骨修補材料。
對照組接受腦室—腹腔分流術后,于術后3~6個月開展顱骨修補手術。研究組接受腦室—腹腔分流術后,嚴密監測患者顱骨缺損區腦膨出及顱內壓情況,于顱骨缺損處無腦膨出且顱內壓下降、張力不高時開展顱骨修補手術。兩組患者于術前和術后1~2周內均應用抗生素。腦室—腹腔分流術:于患者全身麻醉下實施,取仰臥體位,于手術方案確定入路點切開額角或者枕角腦室厄頭皮,顱骨鉆孔。于劍突下腹部正中作切口,建立皮下通道,分流管一端置于盆腔,另一端經隧道導入頭部切口,連接閥門出口端,固定,于硬腦膜處作切口,確定腦室端分流管入口后入路,將閥入口端分流管與腦室段出口端連接,固定,期間可放出少量腦脊液(腦膨出明顯時可放至腦組織復位),確定分流通暢后沖洗術野,填塞骨孔后分層縫合切口。顱骨修補術:按原頭部手術切口入路,完全暴露骨窗,循潛在硬膜外間隙分離皮肌瓣(術中出現硬腦膜破損需嚴密修補),按骨窗大小調節制備好的顱骨修補材料,塑形后固定顱骨,分層縫合,留置引流管,固定。術后1~2 d拔引流管。
1.4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臨床療效并記錄兩組感染、分流管堵塞、分流過度以及硬膜下水腫和積血等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臨床療效評估標準如下:經腦CT檢查結果顯示,腦室前角低密度區消失或明顯縮小,腦室明顯縮小者視為顯效;經腦CT檢查結果顯示,腦室前角低密度區及腦室均有所縮小者視為有效;經腦CT檢查結果顯示,腦室前角低密度區及腦室均與術前大小無明顯變化者視為無效。顯效率=顯效例數/總例數×100.00%,有效率=有效例數/總例數×100.00%,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1.5 統計方法
應用SPSS 19.0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數據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差異比較以t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及百分比表示,組間差異比較以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
研究組總有效率為97.06%(33/34),其中顯效25例,顯效率為73.53%(25/34);有效8例,有效率為23.53%(8/34);無效1例,無效率為2.94%(1/34)。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0.59%(24/34),其中顯效13例,顯效率為為38.24%(13/34);有效11例,有效率為32.35%(11/34);無效10例,無效率為29.41%(10/34)。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研究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785,P<0.05)。
2.2 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
研究組出現術后并發癥3例,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8.82%(3/34),且無1例為硬膜下水腫和積血,其中出現感染1例,感染發生率為2.94%(1/34),經輸液抗感染治療后好轉;分流管堵塞1例,分流管堵塞發生率為2.94%(1/34),經疏通分流管后好轉;分流過度1例,分流過度發生率為2.94%(1/34),經調解分流管開放壓后好轉。對照組出現術后并發癥16例,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47.06%,其中感染4例,感染發生率為11.76%(4/34),經輸液抗感染治療后好轉;分流管堵塞3例,分流管堵塞發生率為8.82%(3/34),經疏通分流管后好轉;分流過度6例,分流過度發生率為17.65%(6/34),經調解分流管開放壓后好轉;硬膜下水腫和積血3例,硬膜下水腫和積血發生率為8.82%(3/34),2例經保守治療后好轉,1例經YL-1型血腫粉碎穿刺針微創穿刺引流后好轉。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比較,研究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968,P<0.05)。
3 討論
直接或間接受外力作用導致的顱腦缺損患者多出現蛛網膜下腔出血或(和)顱內血腫等臨床表現。據有關研究報道[4],蛛網膜下腔出血可能會刺激腦膜引發無菌性炎癥導致蛛網膜下腔出現粘連或壞死腦組織堵塞,阻礙蛛網膜吸收腦脊液,阻塞腦脊液循環。而腦積水多由于腦脊液吸收障礙或循環通路受阻導致,少部分患者由于腦脊液分泌過多導致,腦積水形成后腦脊液集聚可導致腦室系統性擴張,腦室擴張導致腦脊液進入腦室周圍組織后可引發白質水腫,腦組織出現不可逆性損傷[5]。早期、同期開展腦室—腹腔分流與顱骨修補治療顱腦缺損合并腦積水對臨床療效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
該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總有效率為97.06%,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0.59%,研究組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提示顱骨缺損并腦積水治療應用外科聯合手術方案臨床療效顯著。考慮外科聯合手術方案治療顱腦缺損并腦積水時,利用腦室—腹腔分流術放出適量腦脊液、降低顱內壓、緩解腦膨出、促進腦組織復位后開展顱骨修補術,不僅更有利于調節腦積水引發的骨窗腦膨隆,也更有助于塑形顱骨修補材料[6]。該研究發現,研究組總有效率為97.06%,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0.59%,相較于對照組,研究組總有效率明顯更高(P<0.05);研究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8.82%,對照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47.06%,研究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明顯更低(P<0.05)。提示顱骨缺損并腦積水治療應用外科聯合手術方案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較低。推測可能在于外科聯合手術方案更能有效減少腦組織及腹腔暴露,顱骨修補術更便于原手術切口利用和盡量減少硬腦膜損傷,而且大大縮短治療時間可更有效方便分流管理[8]。既往也有研究報道[7],接受同期腦室—腹腔分流術及顱骨缺損修補術研究組患者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7.2%低于接受先行腦室—腹腔分流術后擇期開展顱骨缺損修補術的對照組患者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42.8%(P<0.05),與該研究結果類似。
綜上所述,外科聯合手術方案治療顱骨缺損并腦積水的臨床療效顯著,且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