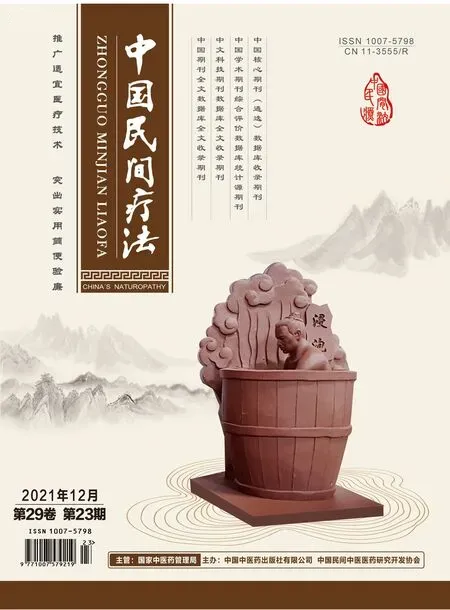孫郁芝運用活血化瘀法治療糖尿病腎病的經驗述要
劉宏飛,王紫欣,孫郁芝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省中醫藥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12)
糖尿病腎病(diabeticn ephropathy,DN)是糖尿病患者常見的微血管并發癥之一。根據流行病學數據顯示,DN可能是中國城市人口發展為透析性終末期腎臟疾病的主要原因,其病理變化包括異常的腎小球系膜擴張、腎小球肥大、腎小球基底膜增厚和腎小管間質纖維化[1],常見的臨床特征是蛋白尿、進行性腎功能不全、高血壓和水腫。近年來,醫學界對DN發病機制、診斷、治療等進行探索,臨床上依據其不同病理分期采取三級防治措施,嚴格控制血糖,給予降壓、降脂、抗炎治療,但糖尿病進展至DN,發生終末期腎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患病人數并沒得到有效控制。
孫郁芝教授為第1批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山西省中醫院腎病學科的奠基人。其從事臨床實踐、科學研究、教學工作60余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腎病的病因病機及臨床診治頗有建樹。“活血化瘀法貫穿糖尿病腎病始終”是其多年臨床經驗的精華。吾有幸侍診左右,觀摩學習,受益匪淺,現將吾師治療DN經驗總結如下。
1 活血化瘀法的立論依據
1.1 血瘀與糖尿病腎病關系 糖尿病屬中醫“消渴”范疇,中醫古籍并無“糖尿病腎病”這一獨立病名記載,多將其歸屬于“消渴”“消癉”“水腫”“腎消”等范疇。?靈樞·五變?云:“血氣逆留,髖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指出消癉期的病機主要為“血脈不行”,病位在血脈,可病及五臟六腑,四肢百骸,治療當以活血化瘀法。唐容川?血證論?曰:“瘀血在里,則口渴……內有瘀血,故氣不得通,不能載水津上升,是以發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則不渴矣。”明確提出“瘀血發渴”之說。可見,瘀血郁熱,耗傷津液,或瘀血內阻,氣化不利,均可導致津液不能上承于口,故見口渴。津液輸布失調,失其滋潤濡養之功,進而逐步發展為糖尿病。
血瘀與糖尿病及其并發癥的形成與發展密切相關,氣虛、陰虛、痰濕與血瘀互為因果,同時并存。呂仁和教授認為,消渴病腎病的病機特點為腎絡“微型癥瘕”,是由于腎臟先天稟賦不足,加之消渴病日久不愈、耗氣傷陰,導致腎元虧虛,“陳氣”與內熱相合,濕熱、郁熱、痰濁、瘀血各種病理因素膠結,久之病變入腎絡而形成[2]。徐遠教授認為“瘀”是該病的重要病機,DN病久瘀血漸顯,內阻三焦,致使精微循行失司外泄而形成蛋白尿[3]。孫郁芝教授則認為,糖尿病發展為DN是由早期陰虛燥熱發展為氣陰兩虛,甚則陰損及陽,經絡關聯周身及臟腑,病久傷津耗氣,脈絡瘀阻,氣化不能健運,治以活血化瘀。
1.2 啟發于現代研究 隨著現代中醫學的發展,現代醫療手段不斷創新發展,DN的中醫治療手段也在不斷提高,不少研究彌補了中醫在微觀方面的不足。研究表明,DN包括許多腎小球的彌散性和結節性腎小球硬化,是由腎小球膜細胞增殖和腎小球簇的瘢痕形成引起的,在超微結構水平,可觀察到足突的廣泛消失,內皮糖萼減少,窗孔缺失,內皮下間隙擴大和細胞質腫脹,而腎小球硬化最終會導致腎小球毛細血管閉塞,形成血栓[4]。同時蛋白尿的發生多與腎小球濾過膜的結構及功能發生改變有關[5]。DN的發展與多個腎區室結構的改變有關,隨著疾病的發展,最早的變化是腎小球基底膜增厚和其他腎小球的進行性變化,包括內皮細胞開窗缺失、系膜基質擴張導致的足細胞缺失及足部發育缺失[6]。血漿蛋白沉積在血管內皮下,形成高碘酸希夫反應陽性和電子致密沉積物,積聚在小動脈、小動脈和毛細血管的分支及微動脈瘤中,引起微循環障礙。儲全根等[7]采用痰瘀同治法干預糖尿病大鼠腎臟TGF-β1/Smad3信號通路,發現具有化瘀通絡法能顯著下調TGF-β1/Smad3基因水平,延緩腎臟纖維化的進展。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藥可以抑制胰島素α細胞合成胰高血糖素或改善α細胞對血糖的感受能力,增強β細胞分泌功能,提高對糖負荷的反應性或改善胰島素外周抵抗機制,減少胰島素的用量而增強降糖作用[8-9]。
2 活血化瘀法的臨床應用
在臨床工作中,DN血瘀證不僅可通過中醫的望、聞、問、切四診判斷,還可依靠西醫的血液檢測與腎臟病理檢查診斷。孫郁芝教授提出,活血化瘀法貫穿DN始終,既基于DN表現如蛋白尿、水腫、腰部固定疼痛等癥狀及“久病入絡為血瘀”的中醫辨證,也基于對DN病機的認識。DN的本質為廣泛的微血管病變,由于血糖長期過高,易造成微循環障礙、毛細血管管腔狹窄、血流阻力增大、血流速度減緩、循環淤滯等腎臟血流動力學改變,從而導致微血栓和微栓塞,造成組織缺血缺氧,導致視網膜病變和蛋白尿發生。中藥在改善血液流變學異常方面具有優勢。微血管病變多有口唇色紫或紫暗,或舌有瘀斑,或舌下靜脈迂曲等臨床表現,屬中醫血證,靈活運用活血化瘀法治療此類病證,可獲得較好療效。
孫郁芝教授認為,糖尿病以陰虛燥熱、氣陰耗傷為多見,發展至DN時,陰虛燥熱已發展為氣陰兩虛,乃至陰損及陽,病久經絡營衛俱損,血脈凝滯,結為瘀血,阻滯腎絡。自擬益腎活血方,藥物組成:黃芪15g,白術10g,茯苓15g,麥冬15g,枸杞子15g,生地黃15g,木香9g,杜仲15g,桑寄生15g,丹參30g,赤芍12g,當歸15g,石韋30g,薏苡仁30g,砂仁6g(后下)。DN多以氣陰兩虛夾瘀證多見,臨床以尿微量白蛋白量進行分期,歸屬于中醫“白濁”范疇,需脾腎同調,濕、瘀兼治,因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培補脾腎以扶正,利濕活血以祛邪,故可用黃芪、丹參作為化瘀藥對,既可補氣血,亦可活氣血,補而不滯,理血而不傷正。瘀血既可作為DN的病理產物,同時也是該病的一個重要病因,因瘀血內阻而致血行不暢的結果,使瘀證更加顯著,反過來又進一步加重腎損害,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導致臨床癥狀反復發作,遷延不愈,最終發展為E SR D。孫郁芝教授歷經多年的臨床實踐,總結并提出“腎病多瘀”論,認為瘀血凝阻于腎絡為其主要病理特點,與現代醫學關于DN的高血黏度、高聚狀態和微循環障礙相吻合。故采用活血化瘀法,對于改善或減輕DN的高凝狀態具有良好療效,且安全性好,不良反應小。
3 病案舉例
患者,男,50歲,2019年9月12日初診。患者發現2型糖尿病30年,目前采用胰島素降糖治療,血糖控制尚可,空腹血糖6.5mm o l/L。2018年發現尿蛋白(),葡萄糖(±),同時發現血肌酐升高。現癥:踝、足面腫,腿軟乏力,腰困,納呆,尿等待,小便不暢,大便干,4~5d一行,眠可,血壓145/80 mm H g(1mm H g≈0.133k Pa),舌淡紫,苔白膩,脈細弦。血肌酐112μm o l/L,尿素氮22mm o l/L,尿蛋白(),潛血(),尿微量白蛋白444μg/m L。西醫診斷:糖尿病腎病。中醫診斷:消渴(下消),脾腎兩虛兼血瘀證。治宜健脾益腎,利濕活血。處方:黃芪15g,太子參15g,當歸15g,丹參30g,白術10g,麥冬15g,杜仲15g,桑寄生15g,續斷片15g,懷牛膝12g,冬瓜皮30g,萹蓄12g,烏藥9g,土茯苓30g,肉蓯蓉片10g,枸杞子15g,生地黃15g,石韋30g,薏苡仁30g,茯苓15g,砂仁6g(后下)。水煎,每日1劑,分早晚2次服用。
2019年9月19日二診:腿足水腫已消,腿軟好轉,腰困,小便利,大便干好轉,納眠可,脈細弦。肝腎功(-),尿微量白蛋白580μg/m L,尿蛋白(),葡萄糖()。照上方加赤芍12g,女貞子15g,煎服法如前。
2019年9月26日三診:癥狀好轉,腰困好轉,便干,小便通暢,脈細弦。按2019年9月12日方加赤芍12g,女貞子15g,郁李仁10g,廣木香9g,當歸改為20g,煎服法如前。
2019年10月24日四診:腿腫明顯好轉,腿脹軟,口干,小便、便干均好轉,脈細弦,血壓120/80mmH g。按照2019年9月26日方加香附12g,麥冬12g。
按語:患者初診時表現為虛實夾雜,因脾腎虛弱,而致氣不化水,久則可見瘀阻水停,治療當扶正與祛邪相兼顧。方中黃芪、太子參、白術、茯苓補益心脾,可調整血糖,利水消腫,并能補益心氣以預防心衰。丹參養血活血化瘀;烏藥、砂仁行氣止痛,三藥相伍,寓氣行則血行之意。對水腫患者,血行則水行,活血化瘀可提高利水消腫的療效,故選用當歸補血活血、牛膝涼血活血。杜仲、桑寄生、續斷、肉蓯蓉、枸杞子為補腎之品,消渴日久及腎而發為下消,用此可陰陽并補,與?黃帝內經?提出的消渴易感體質“五臟皆柔弱者”頗為適合。濕濁內蘊與蛋白尿密切相關,孫郁芝教授認為濕熱不除,蛋白尿不消,故以利濕化濁法消除蛋白尿,本方運用石韋、薏苡仁利濕濁、消蛋白。萹蓄、冬瓜皮導熱下行,利尿排毒。消渴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陰虛燥熱,耗津傷液,津涸血竭,血脈澀滯,血行不利而成瘀血。麥冬、枸杞子、生地黃清熱養陰生津,土茯苓解毒除濕,通利關節,即為此而設。綜觀全方,標本兼治,治療預防并重,扶正祛邪兼施,寓補于攻,活血而不傷血,宿疾新病靈活辨治為其特點。二、三、四診,隨癥加減用藥,收效明顯。
4 小結
DN作為糖尿病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病情遷延。中醫早有“久病入絡”“久病必瘀”的理論。孫郁芝教授在治療DN時,針對病程中不同階段的特點辨證治療,靈活運用活血化瘀法,可改善糖脂代謝紊亂,有效減少蛋白尿,改善腎小球硬化,減輕高凝狀態,對于保護腎功能,延緩DN病程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