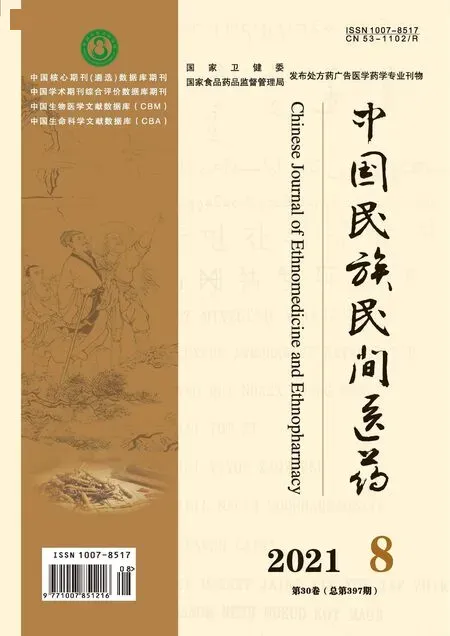傣醫學本科專業文化課程資源開發的思考
何婧琳 陳 普 陳清華 孔春芹 段小花
云南中醫藥大學/云南省傣醫藥與彝醫藥重點實驗室,云南 昆明 650500
傣族是我國云南省世居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等地,人口為122.2萬人。在東南亞地區傣族與泰國的泰族、緬甸的佬族、老撾的撣族等有著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淵源。傣醫學以“四塔(風、火、水、土)五蘊(色、識、受、想、行)”理論為主導思想,以“人體解說”“風病論”等為生理病理基礎,“四塔五蘊辨(病)證”“三盤辨(病)證”和“雅解理論”等為診療特色,有2500多年悠久的歷史,積累了很多獨特診療手段和用藥經驗,富有濃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1]。傣醫學是我國四大民族醫學之一,已被列入第三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
云南中醫藥大學2008年招收了傣醫學及傣藥學方向碩士研究生,2014年招收了傣醫學專業本科生,在傣醫學教學實踐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在過去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發現,由于學生對傣醫學文化的感受和理解不充分,導致了學生在學習傣醫學相關理論及臨床課程時出現了較大的困難,影響學生就業后的運用傣醫學進行臨床實踐的能力,不利于傣醫學的人才培養。因此對傣醫學文化課程的資源進行進一步的開發,豐富傣醫學文化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教學形式,是傣醫學教學改革中的重要內容。
1 傣醫學文化的內涵
傣醫學是傣族同胞漫長的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的防治疾病的知識與經驗。它屬于醫學的范疇,但同時它不僅蘊含著傣族人民的特有的生命觀、健康觀和疾病觀,體現傣族人民獨特的智慧、信仰及思維方式,還和傣族的雨林文化、水文化、竹文化、貝葉文化等緊密相連,因而具有濃烈的人文色彩,因此也是一種文化。文化的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物態文化層是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方式和產品的總和,是可觸知的具有物質實體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層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組建的各種社會行為規范;行為文化層是人際交往中約定俗成的以禮俗、民俗、風俗等形態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心態文化層是人類在社會意識活動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觀因素,相當于通常所說的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等概念[2]。從文化的結構上劃分,傣醫藥文化包含有物態文化、心態文化和行為文化。傣醫學在這3個范圍內都有著豐富的內容,其中物態文化包括傣藥、診療疾病的器具、采藥制藥的工具及記載文獻的貝葉經等;行為文化包含傣族人民獨特的防治疾病的方法、醫學傳承的方式及體育健身運動等,這些行為經過長期發展已成為一種習俗或禮儀;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是心態文化,傣醫學中蘊含豐富的心態文化,如傣族原始宗教信仰,其中包含著傣族萬物有靈、祖先崇拜、圖騰崇拜等思想;而南傳上座部佛教中的哲學觀念和醫學觀念都成為傣醫學基礎理論的組成部分。傣醫學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僅促進了傣醫學的傳承和發展,還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對于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建設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2 傣醫學文化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云南中醫藥大學傣醫學文化課程本科教學已有5年時間,總結教學中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為:學生中大部分沒有在傣族地區生活的經歷,教學多媒體素材缺乏,實踐教學環節設計困難,對于學生學習和感受傣族特有的文化造成障礙;傣醫學與雨林文化密切相關,而學生對傣族生活地區的特殊自然環境感受不夠,對傣醫學文化的理解欠佳;傣醫學受到南傳上座部佛教影響很大,基礎理論中的四塔五蘊辨(病)證體系更是與南傳佛教思想密切相關,學生中知曉佛學理論者較少,使得學生在掌握傣醫基礎理論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和困難。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在傣醫學文化課程資源的開發上多做思考和實踐。目前傣醫學文化課程的開發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表現為:開發主體對文化課程資源進行開發時缺乏清晰的目標;傣醫學文化課程資源的開發意識欠缺,開發的主體較為單一;文化課程資源的開發內容停留在對文化的淺層次介紹上,缺乏對傣醫學文化內涵深入且全而的挖掘;課程資源開發主要通過田野調查和文獻收集兩種途徑獲取材料,開發的途徑狹窄。
3 傣醫學文化課程開發的思考
傣族文化的內涵豐富,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元素都適合作為傣醫學文化的課程內容,在課程資源的選擇與開發中適切性原則十分重要。從現有研究看來,適切性可分為3個維度:個人維度、社會維度和職業維度[3]。從個人維度來說,傣醫學文化課程要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與學習興趣,使得學生通過課程學習對傣醫學文化的深刻內涵有自主學習探索的動力,從而提高學習效率,產生愉快的學習體驗;從社會維度與職業維度來看,傣醫學文化課程需要幫助學生產生對傣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傣族特殊的生活環境孕育了傣族醫藥理論,其中很多內容有些用現代的科學知識難以完全解釋,有些也與中醫等傳統醫藥不相同,只有在理解與尊重傣族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學習掌握這些傣醫學理論,并在以后的臨床工作中大膽施用。
其次在開發主體上,傣醫學文化課程開發的主體應該包括各類專家、教師及學生等。不同主體將為課程開發添加不同的信息資源,在現代課程觀中,教師不僅作為課程資源開發的重要主體之一,而且教師自身就是重要的課程資源。因為課程資源的鑒別、開發、設置和利用都需要依靠教師,而且沒有教師課程資源就沒辦法實施[4]。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組織與參與者,教師對學生的知識結構、興趣愛好、課堂反饋等最為了解,因此教師決定著課程資源的選擇和利用,是課程資源的直接開發者。由于傣族醫藥文化包括豐富的歷史、民俗及人類學等多學科內容,這些內容的審定需要專業的知識,專家的參與可以幫助學校教師的專業成長,為傣醫學文化課程資源開發提供智力支持。最后學生作為教學活動的參與者,同樣可以作為課程開發的主體,學生可以積極思考后提出自己對課程的看法,有的學生本身就是傣族,生活在傣族聚居區,對傣醫學文化有所了解,因此學生具有的知識、經驗也是傣醫學文化課程資源的構成要素之一。
在開發內容上,要避免枯燥地對文化進行淺層次介紹,應該對傣醫學文化內涵進行深入且全而的挖掘,帶領學生通過學習傣族醫藥文化,理解傣族的生存方式與行為邏輯,從而將傣醫學文化與傣醫學孕育出的獨特理論體系及治療方法緊密的結合到一起。比如學習傣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萬物有靈思想進而聯系到傣醫學中口功等神藥兩解的治療方法的由來;學習傣族南傳佛教中的佛教思想聯系到傣醫學對于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等。在開發途徑方面,應該充分的利用各種資源,包括實物資源、文字資源、音像資源、網絡資源等,尤其是在互聯網成為最重要的信息獲取手段的今天,因其具有信息容量大、智能化、便捷化等特點,成為重要的資源載體,極富有開發利用價值。其次了解傣醫學文化的專家、科研人員、民間傣醫、學生家長,甚至包括能夠提供素材的學生及其他社會人士等,均可以成為課程資源的載體,為豐富和深入挖掘傣醫學文化課程提供幫助。
傣醫學文化課教學對于后期傣醫學理論及臨床教學來說起到了前期鋪墊和引領的作用。如何全面深入地發掘傣醫學文化課程資源,利用教學使得學生理解認同傣族文化,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還有待傣醫藥教學工作者的進一步研究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