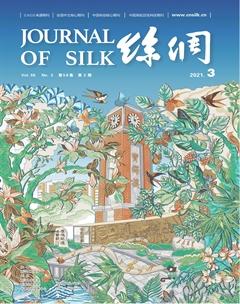近代民間眉勒紋樣的構成形式及其意向性研究
王憶雯 許悅



摘要: 眉勒是佩戴于額間的傳統服飾品,其形成歷史悠久,類型多樣,并以其裝飾紋樣最具藝術表現力。民間眉勒紋樣樣式精美,構成要素豐富,構成形式相對穩定,其搭配呈現程式化的特征,帶有含蓄隱喻的意向表達。文章通過對近代民間眉勒紋樣的研究分析,旨在得出紋樣的構成特征與規律。對以江南大學漢族民間服飾傳習館館藏的眉勒實物紋樣的描摹繪制和構成分析,發現民間眉勒紋樣的構成形式在紋樣組合、紋樣與造型的關系等方面呈現對稱與均衡,“適”形與“破”形的節奏和秩序美感,因此提出民間眉勒紋樣存在隱喻的吉祥寓意和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
關鍵詞: 近代;民間眉勒;紋樣;構成形式;意向性
Abstract: Meile is a traditional clothing ornament for wearing on the forehead.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various types, and its of artistic expressive force for its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folk Meile pattern is exquisite in style, contains rich elements and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form. Its matching shows stylized features, and expresses implicit metaphorical intention.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formation features and rules of the pattern by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folk Meile patterns in modern times. Through depicting and drawing of real Meile pattern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Han nationalitys folk clothing inheritance culture institution of Jiangnan University and formation analysis thereof, 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folk Meile patterns appear to be symmetrical and balanced in respect of pattern combin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tern and shape, and rhythmed and ordered in respect of "suitable" shape and "broken" shape. On this basis, it is inferred that folk Meile patterns contain auspicious implic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nature unity.
Key words: modern; folk Meile; pattern; form of constitution; intentionality
眉勒又稱“抹額”“頭箍”“纏頭”,是中國女性傳統的一種佩戴于額前的頭箍狀飾物,其具有約束頭發、保暖御寒、便于勞作的功能。眉勒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時期的“頍”,頍由絲帛制成。秦漢以后,男子流行用布帛將額頭圍住[1],成為“抹額”的濫觴。至明清,南北方婦女冬季皆戴暖額。常用的眉勒造型有船形、蝙蝠形、啞鈴形、眼罩形、雙葉形等。
目前學界對眉勒的關注和相關研究較少,且多散落在服飾史的部分章節,鮮有專門的深入研究,其中涉及眉勒的相關文獻多從語言學、地理學、民族學、藝術學和史學等學科視角出發,溯源眉勒的名稱及引申語義[2]、形制工藝[3]、審美價值[4]、與物質文化的關系[5]等內容,對眉勒紋樣構成及意向性的研究較缺乏。眉勒紋樣的題材多樣,象征意義豐富,體現出當時女性的審美訴求與藝術品位[6]。本文從近代民間眉勒的裝飾紋樣出發,通過對其布局形式、分布樣式等分析,探究紋樣的意向性表達,以期傳承民間女性群體智慧和傳統文化精髓,對民間服飾品紋樣研究提供理論和方法指導。
1 民間眉勒紋樣的構成形式
眉勒紋樣以單獨紋樣和組合紋樣為主,單獨紋樣大多采用刺繡工藝,構成與四周沒有聯系的獨立完整紋樣[7],其中少數以暗紋的形式出現,在表現形式美感的同時,采用均衡的構圖形式,使紋樣呈現較強的裝飾效果。組合紋樣多以各類元素組合形式出現,通過紋樣的變化組合,實現紋樣“形”的相互制約與“意”的相互關聯。花卉、蝴蝶、魚、荷花等動植物的自然意向出現頻率較高。單獨紋樣以寓意富貴美滿的花卉紋樣為主要內容,組合紋樣在雙葉形、魚形、橋形等造型中應用較廣泛。
民間眉勒紋樣在組織布局上多運用獨枝花、適合紋樣或滿地分散的紋樣形式,紋樣題材豐富,或呈現單獨的花朵、花枝、動物等,或以動植物組合、文字、器物等表現紋樣的節奏與秩序感。在紋樣的分布安排上體現對稱與均衡相結合的特點,通過“適”形與“破”形表現出紋樣的靈活性和巧妙性。
1.1 節奏與秩序美感的紋樣布局
眉勒作為裝飾在人頭部的服飾品,呈現出以帶形為基本樣式的多種造型形式,在帶形的平面空間內,制作眉勒的民間婦女將設計的智慧融入紋樣的布局和構成中。例如通過裝飾紋樣數量和體量的區別,或將植物紋樣在兩端簡潔裝飾,或將其作為滿底紋,營造眉勒裝飾紋樣的疏密對比和節奏美感[8](圖1)。
眉勒的佩戴對女性的面部也起到了極強的裝飾效果。其裝飾紋樣的構成分布也較好利用人的視覺習慣,通過紋樣之間的形狀組合、紋樣的骨式走向等內容,引導人的視覺重心,如圖2所示。眉勒紋樣通過植物花朵和枝葉的密集組合,將人的視覺重心集中在眉勒的正中位置,將觀者的注意力轉移到眉勒下方的面部,不規則的邊緣線條也對人的額頭起到了較強的修飾作用。相似的眉勒裝飾布局在民國時期婦女眉勒中盛行,如圖3中傅斯年母親何老夫人民國時期的照片[9],頭戴黑色眉勒,前中位置裝飾玉石和珍珠,同樣將人的視角重心集中在面部區域。又如圖4中的眉勒紋樣,利用紋樣的骨式走向,將人的視角重心轉移到眉勒兩側,并通過枝葉的蔓延纏繞,引導人的視角遍及眉勒的帶形區域,形成視角重心“收”與“放”的有機統一,在兼顧紋樣美觀性的同時營造了秩序美感。
1.2 對稱與均衡相結合的紋樣分布
眉勒由于其裝飾部位在人的額上,其外在形制與人的容貌以鼻梁為中線呈現左右對稱的特點相符,以中軸線為對稱軸,兩側完全相同的軸對稱平面圖形,遵循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對稱均衡的形式規律,也符合民間視覺審美習慣,眉勒的對稱造型在民國時期的眉勒中也可見一斑(圖5)。與眉勒形制之相搭配的紋樣,也大多按照眉勒外形的對稱軸,分布在眉勒兩側,呈現對稱與均衡之美[10](圖6)。除此之外,眉勒紋樣的分布也常打破完全對稱的固有模式,通過紋樣元素與走向的細微差異,形成均衡中的有序變化、統一中的非對稱協調。如圖7所示,眉勒下緣的圖案裝飾中,雖大小相仿,但形態各異,均依照下緣弧度有序分布,在追求變化和差異的同時并未破壞眉勒整體紋樣布局的對稱形式,表現了眉勒紋樣裝飾的靈活性,其均衡式的紋樣分布也使眉勒的表現效果更加靈活多變。
1.3 “適”形與“破”形的紋樣填充
民間眉勒的裝飾紋樣與眉勒造型相輔相成,呈現裝飾形式的多樣化和紋樣布局的靈活性。如圖8中的眉勒紋樣,采用多種裝飾元素,將線條的“曲”與“直”相融合,并巧妙地將云紋、植物紋和器物紋穿插其中,完美地契合了眉勒的外形。眉勒紋樣的排布還巧妙地利用在弧形邊緣和角隅中的轉角與填充,實現紋樣與外形的高度匹配。如圖9所示,金魚圖案的大小和外形弧度與眉勒外形的適度貼合,蝴蝶紋在眉勒兩端轉角處的處理,既填充了不規則形狀中裝飾空間的空白,又保證了圖案的完整與美觀。除紋樣的“適”形之外,制作者還將紋樣的外形打破眉勒的固有形態,出現紋樣的“破”形現象(圖10),避免了外形的僵硬感,構思巧妙。
2 民間眉勒紋樣的意向性
眉勒上的裝飾紋樣在滿足人們觀賞美觀性的同時,也帶有制作者的美好企盼與意向象征。如通過事物的外在形態、典型形象、發音與諧音等特征,將自然界的動植物、生活中的物品器物等通過聯想與想象,賦予其特定的文化象征、關聯內涵或隱喻表達。眉勒紋樣通過不同元素之間的搭配組合與構成排布,成為一種特殊的裝飾語言,在滿足裝飾目的的同時,表達創作者和使用者的內心情感訴求。通過圖形的象征性和符號化,訴說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與精神世界。
2.1 民間眉勒紋樣隱喻的吉祥寓意
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男尊女卑觀念深刻影響了女性在造物過程中的情感表達,在長期的父權、夫權社會及宗法和禮教的約束下,女性更多地處于從屬地位。在服飾紋樣的創造中,通過較為含蓄和隱晦的方式寄托情感,這一現象在民間眉勒紋樣中也得以體現。民間婦女在眉勒紋樣的制作中,將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形象通過自己豐富的想象力與出色的“女紅”技藝,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在眉勒上。民間眉勒紋樣的表現手法并無固定范式,長期的積累創造和技藝沉淀,使民間女性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帶有隱喻特征的紋樣,紋樣中關于吉祥寓意、求福求富、平安延年的企盼成為貫穿于眉勒紋樣的永恒主題,如表1所示。
眉勒紋樣以符號化的視覺語言所呈現,其吉祥寓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眉勒紋樣寄托了民間女性個人的精神世界,使紋樣寓意帶有主觀性的情感體驗;其二,眉勒紋樣中將獨具地域特色的構成元素融入其中,是紋樣寓意帶有地域吉祥文化的典型配色。以上兩種呈現方式,均借助各種聯想、想象、諧音、類比、比喻等多種手法,受到民間信仰、社會風俗、傳統的儒釋道思想等影響,通過不同的紋樣和圖形的指代及隱喻,賦予眉勒紋樣情感、經驗、觀點、理想的升華,表現出融合中國傳統美學和哲學的造物情感體驗。
眉勒紋樣始終貫穿著吉祥、富貴、平安、祈福長壽及婚姻幸福的觀念,其表現手法多樣,如諧音、比擬、象征、寓意、表號、嵌字等。通過對眉勒紋樣的梳理和研究發現,民間眉勒紋樣中大量運用植物和動物紋樣來表達象征意向,動植物紋樣本身所獨有的生命力與視覺美感,給人一種天然的親切感與歸屬感,同時其形態與名稱也為人們留下了眾多聯想空間和情感抒發,折射出眉勒制作者含蓄委婉、積極樂觀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
2.2 民間眉勒紋樣中的天人合一造物思想
“天人合一”首見于北宋張載《正蒙·乾稱上》:“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11]中國傳統思想歷來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將天與人相互滲透、相互依存的關系上升到哲學層面。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現在古代造物活動和人們生活的各方面,眉勒紋樣的創作者取自然之物寓于人道,在總結自然界動植物和生活事物規律的基礎上,或有意地主觀加工創造,或無意地將傳統的天人觀念內化其中,均成為天人合一造物思想在傳統眉勒中的典型體現。如表1中,民間眉勒中祈求“子孫滿堂”的生命繁衍的渴望,以及隱喻在紋樣中的生殖崇拜等主題。在生產力相對不發達的時期,人們將對生命的崇拜和敬畏轉移到自然、宇宙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客體中,希望通過對自然的膜拜敬告,消災降福并獲得佑護。這種現象反映在民間眉勒紋樣中,民間眉勒紋樣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表現在對傳統圖騰的崇拜及對人的個體關懷,將圖騰紋樣運用在眉勒中常常引申出崇高又獨特的審美觀念。如傳統的龍鳳崇拜,民間眉勒紋樣中多以“鳳穿牡丹”“鳳戲牡丹”等紋樣組合來表達這一思想。其次還包括對山與水等自然事物的崇拜,并賦予其更為宏大的家國情懷,如暗八仙紋之“家族興旺”“富貴吉祥”,山水紋之“國泰民安”“江山永駐”,日月星辰之“江山社稷”等。眉勒紋樣中的個體關懷體現在紋樣對于制作者情感的寄托和對使用者精神的護佑,并搭配眉勒材質、工藝、形制和色彩等多重要素,以具體的紋樣形象將人的精神世界轉化為物化形態,并在制作者和使用者之間形成認知和情感的有形承接,使得紋樣成為人美好祈愿的外在寄托。
3 結 語
近代民間眉勒紋樣是中國傳統服飾品紋樣的典型代表,其題材豐富、構成要素多樣,是中國民間女性集體智慧的集中體現。眉勒紋樣的構成形式多樣,并與眉勒造型相輔相成,采用對稱與均衡的紋樣分布形式,通過“適”形與“破”形的紋樣填充,呈現節奏與秩序的美感。民間眉勒紋樣還受到傳統思想的影響,通過動植物紋樣、器物紋樣等元素的組合搭配,表現出隱喻的“吉祥寓意”和“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反映民間女性對生命的熱切期盼和對生活的美好希冀。
參考文獻:
[1]高春明. 中國歷代服飾藝術[M]. 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9: 78.
GAO Chunming. Chinese Costume Art of Past Dynasties[M].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2009: 78.
[2]白雁南. 河南方言詞“抹兒”探源[J]. 語文學刊, 2009(9): 71-72.
BAI Yannan.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d "Maoer" in Henan dialect[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09(9): 71-72.
[3]王靜, 梁惠娥. 眉勒的裝飾工藝及文化內涵[J]. 絲綢, 2008(3): 50-52.
WANG Jing, LIANG Huie. Decor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eile[J]. Journal of Silk, 2008(3): 50-52.
[4]梁惠娥, 王靜. 論近代中國傳統首服之眉勒[J]. 裝飾, 2006(10): 18-19.
LIANG Huie, WANG Jing. On Meile, the first traditional costume in modern China[J]. ZHUANGSHI, 2006(10): 18-19.
[5]陳芳. 晚明女子頭飾“臥兔兒”考釋[J]. 藝術設計研究, 2012(3): 25-33.
CHEN Fang. Textual research on "Wotu" as a female headdres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J]. Art & Design Research, 2012(3): 25-33.
[6]牛犁, 崔榮榮, 王憶雯. 清代女褂的紋飾藝術: 以石青色江崖海水牡丹紋女褂為例[J]. 紡織導報, 2018(11): 99-101.
NIU Li, CUI Rongrong, WANG Yiwen. The art of decor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womens dragonflies: take the stone-colored river cliff sea peony pattern female dragonfly as an example[J]. Textile Guide, 2018(11): 99-101.
[7]涂樂, 辛藝華. 中國藍印花布紋樣的構成形式及審美特征[J]. 齊魯藝苑, 2011(4): 62-65.
TU Le, XIN Yihua. The composit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lue calico patterns[J]. Qilu Realm of Arts, 2011(4): 62-65.
[8]路永澤. 商周青銅器裝飾紋樣構成形式研究[J]. 裝飾, 2006(11): 91.
LU Yongze. Study of the decorative pattern construction on bronze wares in the Shang and the Zhou dynasties[J]. ZHUANGSHI, 2006(11): 91.
[9]岱峻. 民國衣冠: 風雨中研院[M]. 北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2: 64.
DAI Jun. Republic of China Crown: Wind and Rain Research Institute[M].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2: 64.
[10]張北霞, 吳衛, 張紅穎. 中國傳統卷草紋樣的構成形式及裝飾特點[J]. 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5(4): 126-129.
ZHANG Beixia, WU Wei, ZHANG Hongying. The composition form and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rling grass decorative pattern[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15(4): 126-129.
[11]于民雄. “道法自然”新解[J]. 貴州社會科學, 2005(5): 75-77.
YU Minxio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ao follows nature"[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05(5): 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