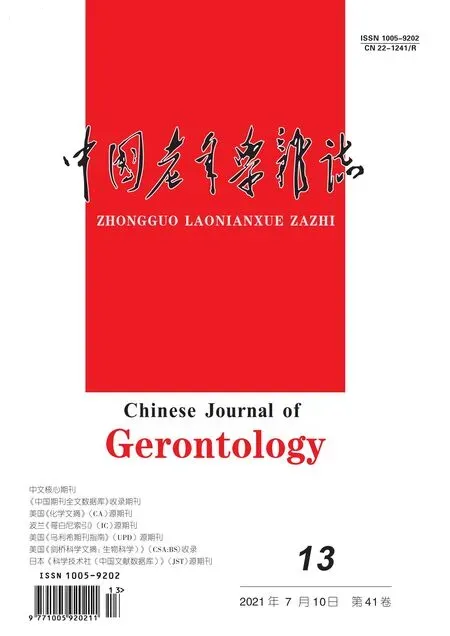結構與功能磁共振成像在輕度認知障礙及阿爾茨海默病中的應用
曾利川 王林 廖華強 謝明國 王渠 任逢春 張玉東 伍文彬
(1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72;2四川省人民醫院)
阿爾茨海默病(AD)是常見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其發生、發展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造成巨大社會經濟負擔,其在65歲以上人群發生率約11%,85歲以上老年人群發生率達32%。AD的發生及進展病理機制尚不明確,可能與β-淀粉樣斑塊過量沉積、腦血管病變等因素有關〔1〕。輕度認知障礙(MCI)表現為神經功能的損害,是發展為AD的一個重要早期階段,但臨床中并非所有MCI患者最終都進展為AD,因此了解MCI及AD的關系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磁共振成像(MRI)是檢出神經系統疾病的一項重要的影像檢查方法,具有無輻射、多參數成像等優點,常規MRI檢查在AD診斷中的價值有限,廣義的功能MRI(fMRI)包括動脈自旋標記成像(ASL)、彌散張量成像(DTI)、磁共振波譜成像(MRS)及血氧水平依賴功能成像(BOLD)等,近年fMRI技術發展迅速,可從多個角度研究AD患者的影像學變化,其研究結果可能對AD早期預防及治療提供重要價值。本文對fMRI在MCI及AD中的應用技術進展進行綜述。
1 T1結構像形態學改變
隨著高場強磁共振的廣泛應用,可在較短的掃描時間內獲得頭顱高分辨率T1WI圖像,對腦功能成像的圖像定位、功能融合十分重要,同時,高分辨率T1WI結構像可定量分析腦灰白質體積含量,用于定量分析AD患者發展過程中腦形態、結構的變化。目前容積MRI(MRI)研究結果顯示AD發生與腦組織體積萎縮有重要關系,目前有多種評價AD腦組織形態學改變方法〔2~4〕,包括1992年Scheltens等〔5〕提出的內側顳葉萎縮(MTA)量表、1996年 Pasquier等〔6〕提出的全腦皮層萎縮(GCA)量表、1987年Fazekas等〔7〕提出的腦白質改變量表,2011年Koedam等〔8〕提出的腦后部萎縮量表等。Harper等〔9〕提出的視覺評分量表通過分析MTA、腦后部萎縮,主要包括后扣帶溝、楔前葉、頂枕溝及頂葉皮層、前顳葉、眶額葉皮層、前扣帶回及前島葉幾個部位的萎縮情況來鑒別AD,其敏感性、特異性分別達94%、89%。Scahill等〔10〕研究也認為可通過楔前葉與后扣帶萎縮情況來評估AD及MCI的嚴重程度。此外多項研究表明AD患者在早期就可出現明顯的海馬體積縮小〔11~13〕,正常老年人海馬每年萎縮約0.9%,而AD患者萎縮達3%~7%,顯著高于前者,Du等〔14〕研究表明,AD患者相對于正常對照組,其海馬體積減小26%~27%,內嗅皮層體積減小38%~40%,而MCI患者MTA程度介于AD與正常對照組之間。有研究報道利用海馬體積萎縮情況預測AD亞臨床階段的準確性達80%〔11,15〕。而內嗅皮層被認為是另一個出現早期體積改變的腦區〔16〕。Nesteruk等〔17〕研究通過MTA情況可鑒別MCI是否向AD轉化。而相對于路易體癡呆和帕金森病(PD)引起的癡呆,AD患者的海馬體積萎縮更為明顯〔18,19〕,通過測量海馬、內嗅皮層、扣帶回等體積的變化,可很好地預測MCI向AD的轉化情況,其敏感性為64.7%,特異性達96.4%。此外松果體被認為與生物節律有關,研究表明其分泌的松果腺素不僅與睡眠節律有關,而且可能在AD發生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松果體素與β淀粉樣蛋白(Aβ)1-40、Aβ1-42作用可阻止淀粉樣纖維斑塊形成,具有保護神經元免受Aβ毒素損傷作用。AD的松果腺素水平低于MCI及健康志愿者水平,因此研究認為松果腺素產生減少可能預示AD早期改變〔20~23〕。Matsuoka等〔21〕利于T1結構像分析AD及MCI患者的松果體體積變化,結果顯示AD患者松果體體積明顯小于MCI及健康志愿者。Lupton等〔24〕將海馬、杏仁核體積與AD基因風險研究后發現健康老年人及MCI患者載脂蛋白(APO)E及髓樣細胞表達觸發受體(TREM)2均與海馬體積縮小相關,而APOE-4在MCI及AD患者中與海馬、杏仁核體積相關。此外,AD患者額葉區腦白質高信號(WMHs)顯著高于對照組〔4,25,26〕,可能與脫髓鞘及軸突損傷有關,側腦室旁腦白質高信號可預測MCI向AD轉化。
雖然目前有多種評價AD患者腦體積萎縮的方法,但腦組織體積萎縮同樣可能發生在其他退行性疾病,甚至在正常老年人中屬于常見生理現象,因此限制了其應用,美國神經病學學會發布的指南中〔1〕,也未將MRI腦組織體積測量作為臨床診斷癡呆的評價標準。
2 ASL灌注
ASL技術通過對水分子進行標記,一定時間延遲后,被標記的水分子作為內源性示蹤劑到達相應腦組織,通過探測被標記水分子信號從而檢測腦血流量(CBF),可無創評價腦組織的血流灌注情況,CBF與大腦神經活動及代謝密切相關,因此是一個反應功能的重要標志物。老年人CBF值減低可能與多種因素相關,包括神經元數量、大小、突觸密度及神經元活動等,同時也有人認為,隨著年齡增加,腦組織出現萎縮、皮層相應變薄,ASL部分容積效應(PVE)影響增加,由于動脈到達時間延遲,導致CBF測量值降低,因此應采用多個標記延遲時間進行成像。ASL所反映的腦血管功能改變,可能與血-腦屏障破壞、低灌注-低氧及內皮代謝障礙有關,CBF降低可導致蛋白毒素的集聚,包括Aβ、過度磷酸化tau蛋白等,進而導致AD的發生。
研究認為大腦總體腦血流量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但在某些腦局部會出現相對增高與降低〔27〕。AD患者與相同年齡階段認知正常的個體比較,其全腦CBF降低達40%〔28〕,而以海馬區、后扣帶回、頂上小葉局部CBF降低顯著〔29〕,研究顯示通過藥物治療后其臨床癥狀改善,而扣帶回區的灌注增加,說明ASL灌注與臨床具有較好相關性。AD患者ASL腦灌注降低與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PET)所觀察到的氟化脫氧葡萄糖(FDG)低攝取相似〔28,30〕。MCI患者腦血流灌注改變差異較大,一些研究表明〔30,31〕MCI的腦部低灌注改變與AD相似,但其減低程度與AD比較稍弱。一些研究表明MCI患者既存在CBF降低,也存在CBF升高的區域:CBF降低主要發生在顳頂額葉外側、內側顳葉、后扣帶回、海馬區等,而一些研究者報道內側顳葉、前扣帶回、島葉、海馬、杏仁核、紋狀體腹側等部位CBF值升高,與上述降低區有一定重疊,可能與各研究方法對MCI納入標準不同有關〔31,32〕,同時也有研究認為CBF升高與降低本身是并存的,即在疾病早期患者的CBF可能是升高的,隨著疾病進展轉而逐漸降低〔33〕。研究發現通過有氧的鍛煉及認知訓練,早期MCI患者的CBF是會發生改變的,因此ASL可能對檢測MCI的臨床轉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34,35〕。多數文獻認為后扣帶皮層(PCC)區低灌注表現發生在AD的各個時期,因此ASL可能是AD患者的一個重要的影像評價方法〔28~30,33〕。
3 DTI
DTI可提供水分子彌散信息,腦白質內水分子因為軸突等結構而出現擴散受限,從而反映白質纖維束微結構的完整性,主要的測量參數包括部分各向異性指數(FA)和平均彌散率(MD),正常腦白質纖維束彌散異性分數FA明顯高于其他組織。白質纖維束微結構損傷后MD值升高與FA值降低的原理尚不完全清楚,可能與纖維束致密度降低、脫髓鞘改變、膠質增生、炎癥及缺血等相關〔36,37〕。Lacalle-Aurioles 等〔38〕研究表明AD患者會出現腦白質微結構損傷與腦組織灌注降低,FA值在AD的亞臨床階段可出現改變,因此通過評價腦白質纖維束微結構改變反映AD的臨床進展。Sexton等〔39〕對納入的研究進行薈萃分析顯示AD患者除頂葉白質及內囊區外其余腦區的FA值均不同程度降低,而MCI患者除頂葉及枕葉以外其他腦白質去FA值均下降。AD患者各腦區MD值均升高,MCI患者除枕葉、額葉外其他區域MD值均升高。認為DTI可顯示AD早期患者的腦結構損傷,主要部位包括海馬、顳葉、后扣帶區、頂葉等,研究顯示〔40〕結合海馬區體積及DTI可提高診斷aMCI的準確性,左側海馬前部彌散系數與AD早期患者語言記憶功能相關,其MD值并與PET中FDG攝取相關。DTI能反映海馬的微結構完整性,Fellgiebel等〔41〕的一項關于30例MCI患者長達1.5年的縱向觀察研究顯示,對于最終轉化為癡呆的MCI患者,其左側海馬MD值明顯高于未轉化組,該結果與Kantarci等〔42〕研究結果相似。此外研究結果顯示DTI可定量評價患者認知功能儲備情況〔43〕。DTI纖維示蹤成像可重建和定量分析纖維連接情況,可用于自動功能結構網絡分析,聯合DTI及其他影像學檢查手段,可進一步了解AD及MCI患者的病例、功能及網絡連接完整性等特點。
4 MRS
MRS可反映腦部特定代謝物的濃度,從分子代謝水平無創性、無輻射的評價AD及MCI患者腦功能改變。正常腦組織N-乙酰天冬氨酸(NAA)是反映神經元完整性的重要標志,其峰值最高,是反映神經元密度及功能狀態的有效指標;膽堿峰增高提示組織的增生活躍,肌酸(Cr)是有氧代謝的產物,而肌醇(mI)主要位于膠質細胞,在AD患者中,mI被認為是反映組織炎性改變的重要代謝指標。文獻報道〔44,45〕AD患者出現NAA降低而mI增高,mI水平升高發生于NAA降低之前,研究認為可將NAA降低、mI升高作為預測MCI向AD轉化指標〔46〕。研究顯示NAA在AD相關基因攜帶者表現臨床癥狀前就出現了下降,而mI在PET顯示的淀粉樣斑塊陽性的認知功能正常個體出現水平升高〔47,48〕。AD患者頂葉NAA濃度及NAA/Cr比值均減低,而MI及mI/Cr比值增高。MCI患者后扣帶回區NAA/mI比值降低、膽堿(Cho)/Cr比值增加,而海馬區mI/Cr比值增加〔49,50〕。Chantal等〔51〕研究發現左側MTL區NAA/水比值降低,雙側MTL區膽堿/水比值降低,而右側顳頂葉皮層(PTC)mI/水比值明顯增高,其結果與AD患者的神經病理改變及認知癥狀相一致,該作者的另一項研究顯示〔52〕AD與MCI患者在左側MTL區均表現出NAA/水、Cho/水明顯降低,提示MCI與AD具有相同的病理基礎。目前許多文獻支持NAA/Cr比值用于診斷AD患者的神經損壞程度。Wang等〔53〕通過對AD、MCI及對照組海馬及后扣帶回區MRS研究發現3組被試海馬區NAA/Cr、mI/Cr、mI/NAA比值均具有明顯差異,而AD患者后扣帶回區mI/NAA與MCI組及對照組具有明顯差異,mI/NAA比值與患者認知功能下降顯著相關。Rupsingh等〔54〕關于海馬區的MRS研究發現AD患者谷氨酸(Glu)水平明顯降低,提示海馬區Glu降低可能成為AD的一個診斷指標。MRS目前尚未廣泛應用于臨床,但是這些技術可提供代謝等重要相關信息,具有其他影像學檢查無法比擬的優點,在AD、MCI檢查中具有巨大潛力。
5 BOLD
BOLD是狹義的功能MRI,腦組織在執行任務時各腦區激活及灌注情況不同,神經元活動導致細胞代謝增加,此時腦組織氧耗量增加,局部腦血流量增加比氧耗量增加明顯。組織的血流參數不同,其組織信號強度不同,氧合血紅蛋白/脫氧血紅蛋白比值變化,從而導致T2*信號改變,BOLD通過檢測組織信號強度,間接反映組織的激活程度。BOLD一般包括靜息態及任務態檢查,前者可檢測腦組織在靜息狀態下腦組織活動,各腦區之間被認為是相互連接的,稱為功能連接。靜息態研究最大的優點在于不需要被檢查者執行某些特定活動,具有較好的可重復性,目前已經證實有多個功能連接,研究最多的是默認網絡(DMN),靜息態DMN可反映AD各結構間在靜息狀態下腦組織的功能連接情況,研究證實DMN連接在AD早期、甚至MCI階段就已發生損害而出現連接異常。Greicius等〔55〕研究顯示內側顳葉結構(包括海馬、內嗅皮層、后扣帶皮層)靜息態異常激活,顯示內側顳葉DMN連接改變是診斷AD的一個指標。早期AD患者腦后部DMN減弱,而前部及腹側DMN增強,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全腦連接明顯下降,在MCI患者中也發現了DMN的連接降低,該現象說明在AD早期階段DMN存在代償機制。研究發現AD患者DMN連接異常區域與病理解剖高度重疊,如Aβ沉積區、低代謝區及腦萎縮區等〔56〕。Li等〔57〕利用靜息態fMRI功能連接強度(FCS)和基于種子點功能連接分析AD、MCI及健康對照組腦功能變化,研究顯示相對于對照組,MCI及AD患者默認網絡及枕葉皮層的功能連接強度降低,其中后期轉化為AD的MCI亞組患者左側角回、枕中回FCS顯著低于未轉化組,fMRI可能成為評價早期AD發生的一個有效指標。Celebi等〔58〕研究表明AD患者中PCC與其他DMN結構的連接水平與神經功能受損相關,PCC后皮層連接水平下降與腦脊液中Aβ水平降低相關。此外靜息態下除了DMN以外,還包括其他多種網絡連接,包括:視覺網絡(VN)、感覺運動網絡(SMN)、額頂網絡(FPN),研究發現AD患者這些靜息態功能連接出現不同程度損害。Liu等〔59〕研究表明海馬旁回是邊緣系統的一個重要區域,在記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關于記憶任務態的相關研究顯示AD患者與對照組比較海馬及鄰近內側顳葉結構激活程度明顯降低〔60〕,在編碼階段頂葉及后扣帶區的腦激活增加,可能與代償相關,而MCI患者表現與AD表現相似。
綜上,目前各種影像學檢查方法各有其優勢,能從不同病理方面為早期診斷AD及MCI提供信息,而多模態影像檢查為多數學者所推崇,聯合多種影像學檢查可從不同方面為AD早期診斷及MCI轉化提供更好的診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