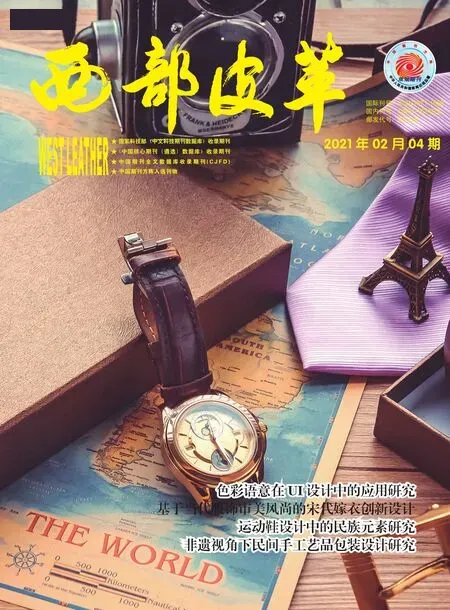隱逸文化與魏晉南北朝私家園林發展嬗變初探
董鑫童,史承勇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陜西 楊凌 712100)
1 政權頻繁更迭是社會不穩定的誘因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是政權更迭最為頻繁的時期。漢末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后四百年間,先有魏、蜀、吳三國鼎立,西晉八王之亂,北方游牧民族舉兵南下,諸國混戰,十六國割據;經北魏統一華北,南方開始宋、齊、梁、陳王朝禪代的斗爭。封建割據和連綿戰亂,中原動蕩不安,兵連禍接,豪強兼并,政權更迭頻繁。從民族融合看,南北方統治的特點是胡漢分治,將漢人與胡人以不同的制度統治。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士族政治制度由形成走向繁榮發展的時期。皇族與士族門閥的勢力此消彼長,爭斗愈演愈烈。士族政治在東晉時期達到巔峰。由曹魏開創的九品中正制,一直延續了三百多年的官吏選拔制度,至隋廢止。任中正者本身一般都是九品中的二品,因而,大多由門閥世族擔任的二品,實際上淪為他們把持官吏選拔之權的工具,甚至成為唯一標準。在真正品第過程中,“寄雌黃于一人之口”,德才逐漸被忽視,而出身愈來愈重要。晉初《請罷中正除九品疏》有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勢力控制中央和地方大權。
面對社會巨變,魏晉士人因傳統價值觀念的失范而出現的信仰危機、危機和憂患情結等,他們開始重新審視自我價值,思考人生命運,尋求安身立命之本。政壇大統一局面崩潰;莊園經濟的發展鞏固了士族門閥的勢力;儒學式微,玄學、佛學的興起,動搖了儒學獨尊的地位,沖破思想桎梏,帶動了文藝思潮的活躍。思想解放帶來了人性的覺醒,推動了藝術領域的開拓,同時也對園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造園活動在民間得到普及,并被升華為一種藝術創作的境界。[1]私家園林的興盛,寺園擴展了造園領域,向著世俗化發展,形成了皇家、私家、寺院三大類型共生共榮的格局和略具雛形的園林體系。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成為了中國古典園林史承先啟后的轉折期。
2 莊園經濟的發展是私家園林的物質基礎
經濟上民生凋敝持續戰亂導致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人口銳減,農田荒蕪,生產停滯。維系小農經濟基礎薄弱,莊園經濟持續發展,使得大地主逐漸成為門閥士族。亂世局勢混亂,朝廷勢弱,士族宗族紛紛結塢自保,廣占田莊,壟斷山澤,不斷積累生產資料,形成規模效應,莊園形成。據《洛陽伽蘭記》記載:“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競爭,祟門豐室、洞房連戶,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蕓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入其后園,見溝讀賽產,石蹬碓堯。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云。”由此可見,門閥士族的經濟實力雄厚,這成為他們建造園林的經濟基礎。這一時期水利灌溉的推廣和建筑技術的進步,必然有利于私家園林的興建。魏晉發達的莊園經濟為私家園林的興盛提供了經濟支撐。
《園冶》中“世之興造,專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諺乎?”園林的營造不僅指造園中疊山理水栽樹種花,更是前期資源的積累,其“營”含規劃經營之意,以身為度,追求理想意境與園景和諧共生。士族生產和經濟的運作,融糅于莊園生產和生活的功能規劃之中。在承襲東漢傳統的基礎上,更講究“相地卜宅”,延納大自然山水風景之美,通過園林化的手法來創造一種自然與人文相互交融、親和的人居環境——“天人諧和”的人居環境。[2]莊園經濟的發展催生出莊園生產功能逐漸向娛樂游賞功能的轉變。謝靈運是首開山水詩派的大家,代表作《山居賦》中“爾其舊居曩宅……曲術周乎前后,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溪而傍沼,乃搶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于巖麓,棲孤楝于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辟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崗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異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粳,送夏早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生何待于多資,理取足于滿腹。”莊園的富饒廣闊,水渠交錯,耕地肥沃,禾稼茂盛,百谷豐收,富裕甜美。這正反映了莊園自給自足,有了“供粒食與漿飲”的生活資源,方可心放世外,閑居游樂,“生何待于多資,理取足于滿腹。”《宋書·謝弘微傳》中“資財鉅萬,園宅十余所,奴僮猶有數百人”。謝氏一族資產豐厚,善于經營,十分注重莊園建設。莊園是生產經濟實體,但其天人諧和的人居環境,及其所具有的天然清純之美,則又賦予以園林的性格。莊園式的山居田園風光,經過詩文吟誦,逐漸培養出了士族內部蘊含著隱逸情調的審美情趣,這對田園詩和山水畫的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私家園林的產生和發展與門閥士族所擁有的莊園密不可分,莊園也逐漸成為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3 隱逸文化的衍生是私家園林美學核心
隱逸文化是伴隨著古代封建集權制度的發展而演變的。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出自小雅·北山》)壓抑的政治統治下,客觀地揭示出統治階級內部和外部關系中的深刻矛盾。道家莊子的隱:“我寧游戲污讀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將個人人格提高到至上的地位來對抗專制集權制度。魏晉時期,隱逸文化開始自覺以老莊思想作為其理論基礎,隱逸不僅是士人的遁身遠跡,而且還全面包容了士人的理想追求、人生信仰、生命實質、審美意趣等的物象表現。[3]在白居易《中隱》中“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出世與入世之爭,有為與無為之爭。大隱享名祿之實,但卻有枉道徇物之憂;小隱雖能潔身自好而又太困窘寂寞,中隱正是在這夾縫中安身立命之法。隱逸文化的產生正是士人郁郁不得志政治抱負的代理滿足。
魏晉南北朝是隱逸文化的成熟期,也是園林的發展期和轉型期。美感因地理環境、民族、時代觀念、心理活動諸多因素影響而具有獨特性。士人在審美活動對于美的主觀反應、感受、欣賞和評價集中體現個人精神表現。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看,一切藝術都是情緒的宣泄。[4]士人遁跡于山林,在矛盾的夾縫中歸園田居。面對壓抑的社會生活、山川草木、文學藝術的多樣化、隱逸文化的產生,士人的思想、意趣和追求,培養了士人對山水的執著與熱愛的審美意識,從而形成了把自然式風景山水縮寫于私家園林的藝術。“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5]自然山川獨立于社會世俗生活之外,在審美主體觀察審視并達成某種精神上的默契和情感上的對流時,自然山水才會變得空靈蘊藉,蘊藉雋永;審美主體也可以在自然山川中得到極高的審美享受和精神享受。[6]魏晉士人對自然山水的感知沖破比德的條條框框,而是欣賞山川草木自然純真的生機勃勃。自魏晉之后,士人將自己的生命追求寄托在藝術創作上,采取藝術生命化或藝術人生化的生活態度,在狹隘的天地中安排他們的生活節奏。這就是“游山玩水”。魏晉于玄言中澄懷觀道、適性任情,構成了山水詩興起的內在動力。在《招隱士》采用夸張渲染的手法,極寫深山荒谷的幽險和虎嘯猿悲的凄厲,“猿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的森然可怖,魂悸魄動之景,造成怵目驚心的藝術境界。當士人流連忘返于自然山水,他們不再受原始宗教萬物有靈影響,也不再是受儒學道德倫理的影響,而是形成了一種生動審美化的自然觀。自然山川之美,不僅被普遍地認識到,而且被廣泛表述出來。[7]晉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并序》中“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因此,人與山水的關系逐漸成為主客關系,自然山水成為人的精神家園,被士人視為最理想的寄居地。
4 結語
私家園林的興起,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典園林發展的轉折期的標志。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是合力作用的結果。政權更迭下社會動蕩,莊園經濟為私家園林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山水有音”的山水情結,游弋于林泉之間的山水審美意識,魏晉人物風象,在我國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對后世的重要影響。私家園林作為隱逸文化的載體,其自身的發展過程是多種文化共同演變的過程,隱逸文化就是其典型代表。在追尋的過程中形成的隱逸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各個歷史時期的烙印,將其自身的繁榮、成熟、衰敗影射到士人園林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響到私家園林的發展。而隱逸精神在隱逸文化中的萌發、成熟與消亡則是私家園林經歷的一個過程,通過對隱逸文化與士族、私家園林及隱逸文化的關系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繼承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