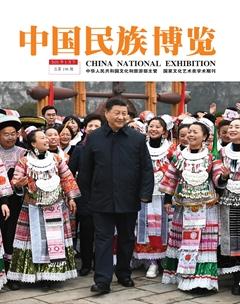簡析明末清初傳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動

【摘要】本文通過清史稿以及其他史料中記錄的史實,從明末邊兵制度名存實亡、地方土司制度以及外部勢力干擾脅迫等三個方面簡要分析了明清之交甘肅全境的復雜格局。
【關鍵詞】明末清初;衛(wèi)所制度;土司;甘肅;漠北蒙古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2-105-03
【本文著錄格式】肖鑫.簡析明末清初傳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動——以清史稿中甘肅全境為例[J].中國民族博覽,2021,01(02):105-107.
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兵在多鐸的指揮下迅速拿下關中地區(qū)并一路往南到達西安,四月初,多鐸率眾經(jīng)歷兩個月的整頓收取了甘肅,并任命黃圖安為滿清第一任甘肅巡撫,而后多鐸率軍向河南、安徽等地進發(fā),然而各地區(qū)的歸附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和,各種勢力犬牙交錯,尤其以甘肅全境最為典型但最容易被忽略,清史稿中雖然沒有記載完整甘肅的當時的形勢,但一項看似尋常的人事任免則從側面反映了甘肅當時復雜的境況:順治二年四月末清廷任命孟喬芳為陜西三邊總督。與此同時滿清政府做了一個更加看似平常但頗有深意的舉動即以太宗(皇太極)第八女固倫公主下嫁科爾沁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子巴雅斯護朗。[1]這些舉動的背后無不折射著當時風起云涌的甘肅全境。本文將通過清史稿中記錄的部分史實通過對明末邊防,當?shù)赝了炯爸車贁?shù)民族政權等三個方面來論述明末清初復雜的甘肅態(tài)勢。
甘肅省在明朝時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省,而是和陜西省合并在一起管轄。明初沿襲了元朝的行政劃分將整個這片地區(qū)歸屬陜西等處行中書省管轄。而后明政府為了杜絕中書省權力過大進而引發(fā)類似于唐末節(jié)度使的狀況取消了中書省的管轄,設置了陜西程宣布政使司來統(tǒng)一管理。原甘肅境內共設置5府、9州(隸屬于府)、50縣。除府(直隸州)、屬州、縣外,還設有衛(wèi)、所。[2]按照明朝對邊境地區(qū)的管理制度,對邊境特別設置了衛(wèi)、所于邊境和要沖地區(qū),在邊境重鎮(zhèn)設行、都指揮使司(行指揮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實際管轄的范圍不同)。衛(wèi)、所實行軍事屯田制,屬軍事機關,但后來在邊境地區(qū)衛(wèi)、所也兼理民政(其設置類似于我們現(xiàn)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明朝中后期,出于對衛(wèi)所對地方政府政務掌控力的忌憚,明朝政府大量地派遣文官輔以個別流管對衛(wèi)所管控力進行了架空,同時默許各地操練營兵來代替衛(wèi)所官兵,衛(wèi)所勢力被極大地削弱了。[3]
明朝在甘肅總共設置有17(將設立又撤銷的也核算在內)個衛(wèi)(洮州衛(wèi)(今定西市臨洮縣)、岷州衛(wèi)(今岷縣)、靖虜衛(wèi)(今靖遠縣)、甘州衛(wèi)(今張掖市,分左右中前后5衛(wèi))、肅州衛(wèi)(今酒泉市)、山丹衛(wèi)(今山丹縣)、永昌衛(wèi)(今金昌市永昌區(qū))、涼州衛(wèi)(今武威市)、鎮(zhèn)番衛(wèi)(今民勤縣)、莊浪衛(wèi)(今天永登縣南)、沙州衛(wèi)(今天敦煌市西)、赤金蒙古衛(wèi)(今天玉門市西北赤金堡)、罕東衛(wèi)(今酒泉市西南))和3個千戶所(西固城守御千戶所、古浪守御千戶所、高臺守御千戶所)。甘肅的衛(wèi)所在成立之初僅僅是具有純軍事用途的軍事機構,但后期明朝政府通過地方巡撫的改良以及衛(wèi)所軍民融合成分的加深,衛(wèi)所漸漸地由純軍事用途的機構改制為當?shù)赝撩瘛⑥r民及官兵多位一體的復雜機制。[4]由于衛(wèi)所設立之初特殊的軍事屯田制特性以及后期被募兵制壓制和弱化,使得大明甘肅的衛(wèi)所在明清之際更加凸顯出了偏向民用和農業(yè)的性質,而沒有介入正面戰(zhàn)場對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賀錦部及滿清多鐸、阿濟格部的主要戰(zhàn)斗。[5]這一奇特的特性麻痹了至少四個方面的勢力:首先以賀錦為首的李自成大軍想當然地認為這些衛(wèi)所士兵因為募兵制的興起已經(jīng)解甲歸田,不會對他造成麻煩;以多鐸、阿濟格為首的滿清一方則認為隨著大明東北及華北防線的崩潰西北防線的守將及士兵不會做任何的反抗都會望風而降,且參照他們與衛(wèi)所兵士的交鋒記錄,他們覺得明末衛(wèi)所士兵根本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和普通農民無異;甘肅當?shù)氐拇笸了疽惨詾橥V萍s他們的官方軍事勢力(衛(wèi)所)會因為天下大亂而徹底消失;喀爾喀蒙古(漠北蒙古)在甘肅一帶的入侵和騷擾沒有受到吐魯番汗國及留守的殘余撤回嘉峪關內衛(wèi)所士兵的抵抗,所以喀爾喀蒙古也以為衛(wèi)所徹底消失了。然而衛(wèi)所從來就沒有退出那一段歷史舞臺。
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甘肅爆發(fā)了由回族將領米喇印、丁國棟、黑承印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聲勢浩大,先后攻克了今張掖、酒泉、蘭州、臨夏、臨洮、岷縣等地。[6]雖然是農民起義,然而起義軍所打的旗號竟然是反清復明,義軍甚至將明偽延長王朱識錛抬出來做精神領袖。轟轟烈烈的起義軍在順治六年的時候被撲滅了,但是給剛剛入關組織全國政權的滿清政府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因為在滿清統(tǒng)治者一貫的印象中甘肅全境應該是老老實實地執(zhí)行剃頭令執(zhí)行得好好的,怎么會發(fā)生暴亂和叛亂這么嚴重的問題?這一事件甚至引發(fā)了滿清體制內部對西部流民安撫戰(zhàn)后重建工作失誤的反思。為什么幾個甘肅回部的將領起義就能讓當時的清廷如此頭疼并派遣親王督師追絞呢?這不得不回到我們前文敘述的明朝衛(wèi)所制度。領導這次起義的將領米喇印、丁國棟及黑承印等原本就是大明衛(wèi)所的將領(舊時為衛(wèi)所所設義勇先鋒營統(tǒng)領)。[7]這些將領熟知當?shù)氐奶鞎r地利,所以起義軍在初期才能滾雪球一般地將戰(zhàn)場由河西地區(qū)推進到河東地區(qū)。另一方面清廷領導的剿匪部隊也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很快撲滅了起義軍,其中也是前明的衛(wèi)所制度發(fā)揮了巨大威力。參與剿匪的將領中有很多原衛(wèi)所的指戰(zhàn)員,例如清廷孟喬芳(清初總督西北)手下猛將李守奎本就是原大明靖遠衛(wèi)負責人。[8]所以在順治六年的這場剿匪本質上可以看作是原大明衛(wèi)所的將領們同僚打同僚。明朝衛(wèi)所制度的余威在這次剿匪的過程中被展露無遺。
明朝后期財政困頓加之地方將領私募兵丁,衛(wèi)所力量被極大地削弱了,而隨之此消彼長的則是甘肅當?shù)卮笸了緦Ω拭C全境的控制。土司是元明清西北常見的一種地方政治制度,自宋元開始,中央政權為了管理西北及西南少數(shù)民族事務而設立的一種管理體制,其本質是少數(shù)民族首領世襲的自治制度。甘肅的土司大都是在明朝初年設立的,時明名將徐達收復甘肅,甘肅的一眾番族土官紛紛歸降,有些土司選擇融入了明朝的衛(wèi)所制度,有些則沒有,明沿用元朝制度,設立土司分管所屬地區(qū),而明中央政府也對土司進行考核定級及征收稅負。[9]甘肅土司中有名的大土司如魯土司等勢力范圍大到上百公里,甚至深入青海內部。[10]而由于甘肅內部少數(shù)民族眾多,土司的實際管轄范圍要比控制住主要大城市的中央政權大很多。明末清初之際,甘肅眾土司的態(tài)度也撲朔迷離,使得這一地區(qū)復雜的態(tài)勢陡然升級。清史稿中土司傳則詳細記述了不服從清初管轄也未曾歸附清朝的甘肅土司。
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列傳三百零四中所載甘肅岷州(今岷縣)土司綽思覺,就是頑固派土司的一員,他一直堅持到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才歸降;洮州廳(今臨洮縣)土司此夕的孫子楊朝樑于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才率眾歸降,同為臨洮縣的土司昝南秀節(jié)的后代昝承福也晚至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歸降;西寧縣(今甘肅甘南以南,青海西寧市東北)土司李文后代李珍品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歸附;循化廳(今青海循化市)土司韓寶元的后代韓愈昌更是遲至康熙年間才歸附;平番縣(今永登市)土司鞏卜失加后代印昌子宏于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歸附。[11]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以順治二年(公元1643年)全國望風歸降大浪潮為時間線,至少在這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甘肅的土司都是搖擺的,且這種搖擺應該是和當時還比較活躍的南明小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鑒于土司對于當?shù)卣嗟膶嶋H控制狀態(tài),可以說在明清之交,清廷控制的甘肅僅僅只有少數(shù)幾個城市,而外圍勢力的壓迫(尤以漠北蒙古、吐魯番汗國的騷擾為甚)又大大縮減了清廷的控制空間。清初甘肅復雜的態(tài)勢如下圖所示:
在清廷控制著的甘肅周圍有著許多強大的勢力,而這些勢力一度讓滿清政府不知道如何處理,在甘肅嘉峪關以西自從明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開始沙州衛(wèi)內遷,明朝徹底放棄了甘肅沙州地區(qū)(即今天的敦煌地區(qū))直至滅亡。[12]這一地區(qū)的實際控制者是土魯番汗國(東察合臺汗國分支),滿清建國后這一地區(qū)也一直是和土魯番汗國反復爭奪,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徹底平定準格爾才將土魯番汗國的地盤徹底納入中央政權的管轄范圍。而在甘肅的北部,漠北蒙古的勢力猶如一片碩大的黑云一直籠罩在明王朝末期以及清王朝早期各個統(tǒng)治者的心中。雖然這種情況在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滿清在喀爾喀蒙古設立八扎薩克以圖交好漠北蒙古之后有所改善,但在此之前甘肅經(jīng)常受到喀爾喀蒙古的騷擾,刀兵不斷。[13]滿清統(tǒng)治者在初期對漠北蒙古針對甘肅的騷擾持默許和支持態(tài)度的,因為漠北蒙古的騷擾可以逼迫明末的衛(wèi)所官兵為了保全當?shù)匕傩彰馐苊晒抛虜_而投降滿清,以滿清為靠山抵御蒙古。然而部分衛(wèi)所官兵的這種左傾機會主義態(tài)度恰恰坑害了當?shù)匕傩眨逋⒅活櫤湍泵晒胚_到戰(zhàn)略上的短暫和平而保證自己不會腹背受敵,從來不會真正關心百姓的死活,更不會為衛(wèi)所官兵的生計著想,這也為后來順治五年的回部將領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埋下了種子。
西北地區(qū)的復雜態(tài)勢一度是滿清幾代統(tǒng)治者最為頭痛的問題,而西北的軍務又是這一系列問題里的頭號問題,清政府在處理這類問題上甚至不惜進行政治體制的創(chuàng)新,如雍正年間設立大名鼎鼎的軍機處。[14]清政府在這一地區(qū)的處理一開始是任其出于混亂狀態(tài),沿用部分的明朝衛(wèi)所制度,保留部分衛(wèi)的名字,以圖效仿明朝,但漸漸地發(fā)現(xiàn)甘肅這一地區(qū)的兵民轉化十分復雜,有些所謂的衛(wèi)早已為自己做好了變更為州府的準備,至少清政府的部分杰出將領就發(fā)現(xiàn)了這一端倪,例如雍正年間的西北軍事主管年羹堯就曾建議雍正皇帝撤銷甘肅部分衛(wèi)或者廳的名稱改作州府。[15]作為滿清政府的首腦,清朝統(tǒng)治者十分清楚清初甘肅乃至全西北的這種幾股勢力犬牙交錯的狀態(tài),而早在開國之初的幾任封建統(tǒng)治者都確定了通過一場或者幾場浩大的軍事勝利來徹底將幾股勢力肅清,從而將西北變成類似于中國南方的便于統(tǒng)治管理的統(tǒng)一政區(qū)的這么一種國策。然而滿清統(tǒng)治者的這一設想?yún)s經(jīng)歷了從努爾哈赤開始算起到乾隆前后六代統(tǒng)治者殫精竭慮,消耗無數(shù)國庫錢糧的艱苦卓絕的百年斗爭才得以實現(xiàn)。從這里我們也能看出西北地區(qū)尤其是甘肅地區(qū)多民族國家政區(qū)的復雜。尤其是復雜的地區(qū)態(tài)勢碰到了王朝更迭的大變動期更加加劇了這一地區(qū)的不穩(wěn)定性。
綜上所述,在明末清初政權更迭的大背景下,甘肅全境表象上處于傳檄而定的狀態(tài),但實際上傳檄而定的僅僅是蘭州、武威、張掖等城市。嘉峪關以西的甘肅領土從來都沒有被傳檄而定直至康熙年間;隱藏在軍民中間的明朝衛(wèi)所勢力依舊攪弄著明清之交的風云;世襲罔替的大土司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的選擇投降,有的選擇觀望,沒有徹底讓渡實際控制權讓渡給當時即將形成的中央(清初統(tǒng)治者);喀爾喀蒙古,東察合臺蒙古的后裔也虎視眈眈地盯著已經(jīng)支離破碎著的甘肅。 面對這樣一種狀態(tài)想象中的傳檄而定兵不血刃收納甘肅只能是滿清政府當時的爪牙親王多鐸、阿濟格及漢將孟喬芳之流哄騙上級自欺欺人的理想狀態(tài)。其后爆發(fā)的武裝農民起義也是這種和平之下暗流涌動的縮影,甘肅復雜的態(tài)勢在中國歷史的任意一個時期都折射出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在建立過程中的波折和磨難。而甘肅大地兵民融合的歷史也是甘肅地方歷史的一條暗線,通過研究這條暗線可以對研究邊疆史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歷史提供更多的思路。
參考文獻:
[1]趙爾巽.清史稿·第二冊(卷一到卷八)(紀)[M].北京:中華書局,2003.
[2]肖立軍.明代邊兵與外衛(wèi)兵制初探[J].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2):39-47.
[3]劉曉斌.芻議明末兵役制度與國家興亡[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11(1):41-43.
[4]崔云勝.對黑河均水制度的回顧與透視[J].敦煌學輯刊,2003(2):144-146.
[5]張磊.明代衛(wèi)所與河西地區(qū)社會變遷研究[D].西寧:青海師范大學,2019.
[6]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十五史:清史稿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7]白壽彝.回族人物志[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8]甘肅白銀市圖書館.甘肅歷史名人[Z].
[9]閆天靈.明清時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與寄住政策[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19(4):33-46.
[10]秦永章.元明清時期甘寧青地區(qū)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變[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3.
[11]同文獻[5].
[12]周松.明代沙州“達人”內遷新論[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2(5):99-112.
[13]馬嘯.17至18世紀清政府與蒙藏地區(qū)政治互動模式研究[D].蘭州:西北師范大學,2008.
[14]劉青瑜.《清會典·辦理軍機處》嘉慶本與光緒本之比較研究[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
[15]鐘賡起.甘州府志[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作者簡介:肖鑫(1988-),男,漢族,上海人,碩士研究生,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大數(shù)據(jù)考古,歷史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