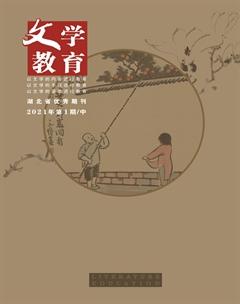從《巨流河》看齊邦媛的教育背景與人文情懷
蔣雯雯
內容摘要:作為新時期的知識分子,齊邦媛的一生經歷了太多。戰爭時期的顛沛流離,建設臺灣時期的艱難,后半生致力于教育的用心,從事文化交流的欣喜,她都在《巨流河》中一一道出,將家國史和個人史悲喜交集地放置在20世紀的舞臺上。從這部回憶之作中可以管窺父母給予的教導、學校的教育和文學的滋養對齊邦媛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基于這種認識,本文擬從《巨流河》入手,簡要分析齊邦媛的人文情懷的養成與其教育背景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齊邦媛 知識分子 教育 文化 情懷
《巨流河》繁體版的腰封上有一句話:讀了這本書,你終于明白,我們為什么需要知識分子。作為20世紀在戰亂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齊邦媛通過這本書告訴我們,越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刻,越是需要知識分子的擔當,擔當青年的引領者、文化的傳承者與民族的守護者。通過她的書寫可以看出,正是父母從小對她的言傳身教,以及學校恩師的教誨和中外文學的滋養,得以讓齊邦媛在面對生活中的困苦、磨難時能夠平淡面對。也使得她的文學能夠超越個體、種族、國家,表現出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出對知識和文化的尊重。
一.家庭教育
1.母親的啟蒙:生命底色的奠定
齊邦媛一出生,父親便不在身邊,是母親的堅持與努力才為先天不足的她撿回了一條命。而且母親在那些苦難日子中的掙扎和堅守,陪伴著童年時期的齊邦媛,給予她終身的觀念和文化影響。
齊邦媛說:“在我的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吃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原本也是作為大戶人家的明珠,十九歲嫁給父親,婚后不久父親就離家在外奔忙十年,母親也就在老家莊院待了將近十年,盡心侍奉祖父母、撫養兒女,孤獨地等待父親偶爾的探望,從不表露半句怨言,就連在突然痛失幼子后悲傷哭泣也只能躲在牧草堆后面流眼淚。痛失幼子之后的母親精神狀態一日不如一日,前來看望的姥爺知道一個女人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下決心把母子三人送去南京與父親團聚。一路上母親的冷靜和沉默是被她深刻印記的,前路未知的緊張,舉目無親的恐懼,都在那一句充滿想象的“鬼哭狼嚎山”的回答中了。十年等待,終于得以和父親團聚的母親,此后便一直在父親身邊,幫助他料理家事、處理政事,照顧參加革命的朋友們和那些因為戰爭流離失所的學生。一生都在為兒女操心,為丈夫奔勞。
就是這樣一位母親,依靠著自己的堅韌和愛,與孤獨作伴,與動蕩相向,與苦難斗爭,在最初無望守候的十年中,在那些顛沛流離的歲月里,為兒女們樹立了待人處事的榜樣,給了齊邦媛最初的文學啟蒙。她認為:“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上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她把那蒼茫大地的自然現象、虎豹豺狼的威脅,和那無非言說的寂寞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給我童年至終身的啟發。”激發了她一生的文學情懷和想象,使得她的文字具有溫潤與不屈的底色。
2.父親的教導:文學理想的確立
在齊邦媛心里,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父親的言傳與身教為齊邦媛樹立了為人為學的理想和標桿。
童年時父親的缺席,并沒有造成她與父親之間的隔膜,反而使她對父親更加敬重。十歲那年,患上了嚴重的肺病,須得去北平療養,父親親自帶著她坐火車北上,第一次在餐車上和爸爸面對面吃飯,爸爸貼心地為她切好牛排,這都是以前沒有享受過的關懷,這一幕幕也成為了齊邦媛心中永遠忘不了的深情。但父親的教導是嚴厲的。孩童期間的一件小事至今讓她記憶深刻,當她在泥濘不堪的小巷里遇見坐在汽車上的父親,卻被教導不可以因私事而占座公車。可以看出,這位溫和的父親,在對待人、事上有自己的原則。他以自己的言行舉止為齊邦媛樹立了為人的標桿,也使得她在治學方面更加嚴謹。
在30年代風雨飄搖的局勢里,看著許多流落街頭的青年,父親力排眾難在南京創立中山中學,收留那些流離失所的青少年,希望在動蕩中存續知識和文化的力量。南京陷落后,學校和學生只能南遷,一路上,父親多方設法、各處奔波,解決學生基本的吃住問題,保護每一份教學設備。他知道,越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越需要教育、知識和人才。這是父親的理想與責任,也亦使齊邦媛第一次親眼目睹并感受教育與國家命運的牽連。
大學期間,因為時局的原因,進步學生們組織游行、示威等活動,這對年輕的齊邦媛來說是很新鮮的,但父親的一封來信為她在迷茫中指明了方向:“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這封信如一盞明燈,讓齊邦媛發熱的頭腦得以冷靜的思考。后來她雖然在機緣巧合下從事了一段時間的政治工作,但很快就全身而退,一方面是因為自己不適合從事政治,另一方面也是謹記著父親的勸導,覺得救國的道路并非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父親的關愛和安排使齊邦媛在動蕩的年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且在父親那一輩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濟世理想和家國抱負,不僅使她深受感動,更促使她能夠更深入地思考政治和文學問題,明確自己的方向,確立一生為人為文的理想與情懷。因此在以后逐漸安定的日子里,她依然堅持著父輩以教育啟蒙國人的文化理想。
二.學校教育
1.國內教育:人文情懷的養成
齊邦媛的前半生處于內憂外患的民國,國家危急,教育中便處處滲透著愛國意識。這些在傳統文化中浸染過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他們的教育理念、濟世救國情懷、文化認同等觀念深刻影響著課堂內外的學生們。作者在《巨流河》中動情地回憶起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的恩師們。他們于硝煙炮火的一隅維護著獨立自主的辦學風格,傾盡所有培養學生的家國意識和人文素養。
因為戰亂,小學畢業后,齊邦媛先后輾轉于多個中學,其中在南開中學待的時間最為長久。當時的南開中學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任校長,倡導以教育救國,鼓勵學生在國家危難之時,更要有所擔當,要明確“中國不亡,有我”的意識。家國與民族開始在齊邦媛心里有了重量。
孟志蓀老師的國文詩詞課也讓她深受啟發,初中的新文學,高中的《詩經》到民國文學,孟老師用他的學識,輸出優秀的文學知識,加上齊邦媛自身流亡的經歷,她更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也更能理解詩詞中的國仇家恨。教授世界人文地理的吳振芝老師,在遭逢大難之后依舊堅持回到學校上課,為他們講述異國土地上的風土人情,更加激發了齊邦媛日后探索其他文化的決心。
因為父親的原因,齊邦媛選擇在武漢大學就讀哲學系,一年后轉入外文系。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上培養了她的英文詩歌鑒賞能力和文學品位,與她在中學孟老師的課堂上所學的中國詩詞相結合,中外兩種詩歌或形同或相異的意象和意境引領她走進了一個全新的神奇的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了詩對人生的力量,文學對人生的力量。
在南開中學,齊邦媛受到了較好的基礎教育,也使她看到了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并萌生救國救民的理想。在武漢大學,得遇名師,了解到了大千世界和中西文學,使她的文學生涯有了一個較高的起步。特別是在孟志蓀老師、朱光潛老師的課堂上,她領悟到了詩歌的力量。當她得知張大飛殉國的時候,她想起惠特曼的《啊,船長!我的船長!》;當她遠在異國懷念親人時,她心中浮現了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人生的大悲大慟,全都內化于詩歌和文學浸潤的心靈中了。
2.國外教育:文化交流的給養
大學畢業后,思慮再三,齊邦媛最終選擇去臺灣工作。等到工作、家庭逐漸穩定,年紀漸大,但是追求知識、探索文化的心從未停歇。
1956年,33歲的齊邦媛考取了“美國國務院交換教員計劃”獎助,開啟了她的文化交流之旅,到美國進修、訪問,在密西根大學進行英語教學訓練,深切地了解到了美國的生活方式。這一次是齊邦媛的一個“夢”,但是卻觸動了她一直追求學術的心。
1967年,44歲的齊邦媛再三考慮后申請了“美國學人基金會”的進修獎助,先到印第安納州的圣瑪麗學院教授中國文學,四個月的時間里,她開始有系統地讀書,也是從此時萌發了傳播臺灣文學的念頭。之后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比較文學,更是利用每一分從為妻為母的職責中偷來的時間學習,她說這是她一生中最勞累也是最充實的一年。
中西文化的交涉、碰撞,不同國家之間文化的相通之處和差異之點,使得齊邦媛的文學生涯又開創了另一重境界——“聲音與意象的結合,令她著迷震撼,仿佛是構筑了一種感情的烏托邦,表現出強韌的生命力,長久縈繞在她心間,化為一種生命品質和成長力量。”新質的加入,讓齊邦媛對文學有了更深的領悟,激發了她致力于臺灣文化與西方文學交流的拳拳之心。
三.結語
在齊邦媛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心中,戰爭與流亡是他們心中抹不去的記憶,但是他們的經歷,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所感知的文化——“五四”新文化、啟蒙精神、“人”的文學以及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思想等等,使他們在流亡中始終保持著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始終堅持著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為自由、平等、獨立等普世價值奮斗不止,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盡心盡力。
懷抱這樣的理想和情懷,齊邦媛在流離中堅持不斷汲取知識和文化,在后半生致力于中國文化與文學的重建、交流與發展。她在臺灣中興大學創辦外文系,引介英美文學到臺灣;在國立編譯館潛心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推動了中國文學的一大步;組織重新編寫中小學國文教科書,希望孩子們能夠學習到更純粹的文學作品;在臺灣大學退休后依然為臺灣文學的發展盡心盡力,努力將臺灣文學推介到西方等。
參考文獻
[1]齊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2]王德威.“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與《巨流河》[J].當代作家評論,2012(01).
[3]楊小露.故國回望與使命回望——論齊邦媛《巨流河》的精神旨歸[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5(06).
[4]袁玲麗.以文學之舟涉渡:《巨流河》的女性成長主題探析[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2018(04).
[5]楊君寧.民國顯影·臺灣軌跡——跨海知識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實踐:以齊邦媛為中心[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5.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