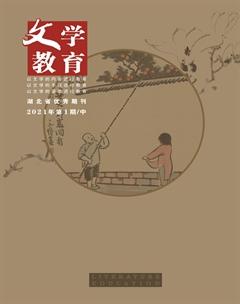淪陷時期張愛玲散文創作中的個人營銷
王健
內容摘要:因文風和身世以及傳媒眼中張愛玲的性格原因,大眾皆認為她是一個孤高冷漠的女作家,殊不知在上海淪陷時期的張愛玲是一個極其善于自我營銷的作家。本文僅從其淪陷時期或發表或出版的散文,來見證其獨特的營銷手法。
關鍵詞:張愛玲 散文創作 自我營銷
大多數人認為淪陷時期的張愛玲行為舉止略顯孤僻乖張,比如嚴格的時間觀念,略顯怪異的服裝搭配,對人嚴重的防備心,斤斤計較的金錢觀念亦,顯赫衰敗的家世等而疏漏其主動用文字來進行個人IP營銷的事實。其實,她很善于用散文來和讀者做交流,先不著痕跡地打造一個她想讓讀者看到的形象,引發她所需要和引導的共情,在肉體的疏離和文字的構建中,高明的完成極具個人特質的營銷,在激烈的文壇競爭中快速打開知名度,樹立高辨識度的IP。“從創作主體的心態看,張愛玲早年的身世無疑影響了她人格心理的發展,進而影響到她對外部世界的感受和體驗。”①某種程度上,她是將自己的文本形象和公眾形象也作為一個商品在營銷。
張愛玲不自覺的給自己定下若干人設,將自己和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區隔開。在淪陷時期,張愛玲通過散文創作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熱愛上海,家世華麗但已破落,從小缺愛,不得不獨自求學謀生的上進年輕女知識分子形象。但女作家不能模仿女明星那樣炒作自己,畢竟是文人,而且對自己的身份有著高度的認同,她不是冰心白薇那一路的作家,非要拎出一個同道中人,也許只有蘇青了,但她和蘇青唯一相似的地方在于對世俗的熱愛。于是,怎樣在雅和俗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又怎樣在保持自我又能最大程度的吸引自己想要吸引讀者,才是擺在張愛玲個人營銷的難題。
上海灘的女明星是靠“噱頭”博眼球,維持曝光抬高身價。“噱頭”包括:各類緋聞、勁爆新聞、高片酬和熒幕外的各種人設打造,然后分門別類細化各自的市場。女作家其實也屬于此類靠眼球謀生存的人群,但宣傳手段卻不能如女明星般難登大雅之堂,大多數女作家可以炫耀學歷,但張愛玲大學因為戰爭未能畢業;有一部分可以靠美貌,張愛玲顯然不行;還有一部分靠高端戀愛,比如借助男作家的戀愛加持,但張愛玲的戀愛對象是胡蘭成,有名的漢奸文人,藏都來不及,如何宣傳?也有一部分直接花錢,但張愛玲還指望稿費過生活,或者用最流行的站隊方式,將自己歸類在某種主義之下,但張愛玲顯然也不適合;又或者題材取勝,花妖狐媚花前月下這類鴛鴦蝴蝶她喜歡但是不完全認同,兇殺暴力色情歷史懸疑她完全無法勝任;至于人脈,作為一個剛剛出道的女學生,連辨明雜志背景的能力都很有限;家世上,早已和父親鬧翻的她無法取得任何援助。很顯然,常見套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另辟蹊徑來營銷。
張愛玲不自覺地給自己做著個人營銷,她善于精準定位,深知自己的主要受眾是上海的受過一點教育的市民,尤其是有一定收入的中產或小資產階級女性,她很自覺的把自己劃入她們的陣營,做起了代言人,真的是低至塵埃,并努力在塵埃中開花。首先是贊美衣食父母,然后自訴其苦,也給大眾看一點她們想象的豪門,以及亂世孤女的謀生不易,最后結合實際談談亂世中的兩性關系,當然也忘不了拍拍雜志或書商老板的馬屁。一套流暢的“組合拳”打下來,不僅小說、雜志更加暢銷,自己的收入也隨之增加,且讓自身的公眾形象更具傳奇性。一舉多得,她用自己的文字,終于把自己包裝成當時的實力“網紅”。
一.身份營銷
營銷的第一步就是找準受眾群體,對于孤島時期的張愛玲來說,就是滯留在上海的廣大小市民。當時張愛玲靠著一本《傳奇》暴得大名,但根基并不穩固,所以一向給現在讀者高冷之感的張愛玲,在面對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讀者群時,也不免用最熱烈的詞語贊美自己的讀者,就差把自己“低到塵埃里”。
但民國時期上海人的名聲并不完全正面,張愛玲面對這一群并不容易討好卻對自己這個初來乍到的女新人格外青睞的衣食父母們,一時之間如同獲得最佳新人獎的幸運兒,感恩得顫顫巍巍甚至有點語無倫次。
《到底是上海人》中,張愛玲幾乎通篇在贊美自己的讀者,首先在外形上:“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仿佛張愛玲剛從化外之地歸來,一見故人十分相親,頓覺神清氣爽,仿佛一掃香港島的暑熱,瞧著鄉親父老就是清爽。接著是智商和情商,直言褒贊上海人的“通”,先是“文理清順”:“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嗯,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熏風的‘熏”。對自己潛在的市民讀者的智商和審美品位充滿自信。最令張愛玲稱道的是上海人的情商,這情商在外地人眼中也許是奸猾虛偽,可張愛玲給予最深切的體貼:“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并對上海人的標簽形象做了廣泛而悲憫的安慰,廣大的上海市民和新興女作家張愛玲一樣在亂世中如履薄冰的掙扎著,她對社會底層生活有著深切的認知,對上海市民讀者的真實生活狀態了如指掌,并深切同情:“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上海人不那么幼稚”。這已不是對讀者的精準定位了,這是在闡述和營銷自己的創作理念,現代讀者多認為張愛玲是貴族作家,技巧大于內容,這是對她的誤讀。她至始至終為最廣大的市民發聲,寫市民的真實故事,不過是用華麗的筆觸,道盡亂世中的世態炎涼,展露亂世中人性的幽微隱秘,而絕非風靡上海灘多年的公式化鴛鴦蝴蝶派。她不僅用全新的語言,還要用亦古亦今的視角,冷峻卻悲憫的現代手法書寫獨居一格的上海意象,上海群像。
張愛玲對第一本小說中將重心放在香港深感愧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榮莉香片》、《心經》、《玻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幾乎已是完全的身份認同,仿佛要從紙面上跳出來:“我張愛玲是上海人,哪怕是第一本書寫香港大賣,我也是上海人!”“特殊的人生經歷與現代女性在新舊交替社會中的都市生活,造就了張愛玲‘上海女性視角的特殊質素,形成文學上的‘張看式的‘冷,從而把她對都市文化持以沉醉于玩味的心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呈現為自我主義傾向的‘虛無”。②
最后幾乎直白的拉票:“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張愛玲的身份認同呼之欲出。銷售的潛臺詞,變成了鄉里鄉親的互助,張愛玲巧妙地完成了第一階段的營銷,不僅妥帖的贊美了自己的受眾群體,還把自己融入期間。
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對讀者的贊美幾近虔誠:“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買雜志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么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張愛玲對自己的職業有著清醒認識,雖然勞苦,但起碼是正當的受歡迎且收入不錯的職業,對大眾對自己的文化消費預期做了近乎明察秋毫的論斷。
一炮而紅的《傳奇》雖是香港故事,但1945至1949年間,時局變化,頂著“漢奸妻”的名頭,她依然沒有離開上海,她對上海人的身份認同,相當徹底,她用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的誓言做了最坦蕩的注腳,哪怕這座城市一度拋棄她,張愛玲的身份認同十分徹底。甚至多年后在美國,她依然不斷重復著早年間的上海故事寫作。
二.共情營銷
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民國上海的“特產”,張愛玲不介意民眾的“窺視”,甚至有意的展示。這也是其主動營銷的策略。論美貌和曝光率,女作家自然不是女明星的對手,但極擅長用繁復筆調描摹市民生活的張愛玲,以一種自嘲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生活,盡管是人人稱羨的女作家,但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住的公寓也絕非民眾想象中的廣寒宮。
亂世的人不如狗,又遭戰亂,廣大市民生存堪憂,身逢亂世實屬不幸,張愛玲一上來就悲亂世人之苦,尤其是悲亂世女人之苦,將自己的身份認同泛華成全體淪陷時期的上海女性,上海米貴,白居不易,獨居更不易。
她深知上海寸土寸金,能有頭頂上的一片瓦已屬不易,哪怕是住在租界里隨處可見的公寓中,居住條件也比一般市民要強太多。所以對自己的居住條件,張愛玲的敘述談不上炫耀,更多的是拉近距離共歷時艱,不過文字表現上亦是張氏風格的“幽默”。《公寓生活記趣》發表于1943年12月的《天地》雜志,時值深冬,可“公寓房子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從煤貴了之后,熱水汀早成了純粹的裝飾品”。
張愛玲明了民眾對女作家的居住環境深感好奇,很多市民連公寓也是住不起的,但淪陷時期的上海公寓早已不是普通民眾想象的那樣,它已然是一座半癱瘓的廢墟,甚至供水還不如貧民窟方便,“若是當初它認真工作的時候,艱辛地將熱水運到六層樓上來,便是咕嚕兩聲,也還情有可原。現在可是雷聲大,雨點小,難得滴下兩滴生銹的黃漿”。但張愛玲善于苦中做樂,于艱苦或乏味中找尋生活的小確幸,這也是廣大普通市民的慣常心態:“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風如果不朝這邊吹的話,高樓上的雨倒是可愛的”;“我喜歡聽市聲。比我較有詩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濤,聽海嘯,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風雨和市聲,到了張愛玲這里便雅得緊,大有一種“大隱于市”的悠然自得。張愛玲對所謂的都市獨立女性的難處最感同身受:“恐怕只有女人能夠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優點:傭人問題不那么嚴重。生活程度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準備著受氣。在公寓里‘居家過日子是比較簡單的事。找個清潔公司每隔兩星期來大掃除一下,也就用不著打雜的了”。
除了住就是吃,正如蘇青所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耶”。張愛玲對淪陷區的吃也做了營銷式描寫,但不是直言上海,她在《燼余錄》中寫了戰后香港的飲食風情:“在戰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所有的學校教員,店伙,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卜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銳肯定。”《燼余錄》發表于1944年2月,冬天還未結束,在這種香港上海的互文關系中,上海的情況也可想而知,物資的短缺讓人退化成動物,生理的饑餓比什么道理都不講道理。這種饑餓不需要刻意營銷,人所共知的東西,張愛玲不過是略略一提,便能激發讀者的身心共鳴。
衣食住行刪繁就簡就是錢這一個字,迫切想經濟獨立的張愛玲對錢有著格外真切的感知,推己及人她毫無困難的就能推演出亂世中都市女性的困窘和驕傲,以及一些些男性作家所不能感知的微妙心理,這才是最有區分度的營銷,人無我有,人有我精。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精妙傳神的擊中了女性受眾的軟肋。“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于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官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張愛玲的寫作主題不同于五四時期嚴肅主題的書寫,她只寫日常都市中的‘男女間的事情,本人對金錢的爽直態度也有異于傳統較為清高的知識分子。”③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氣吧?一句蒼涼道盡亂世里所謂獨立女性的辛酸,驕傲中透露著不甘,強悍中摻雜著委屈。這些因為種種原因得不到男性庇佑的女性,心甘情愿的被張愛玲所營銷,感同身受永遠是營銷技巧中最能打動受眾的技巧。在廣泛的施以同情之后,張愛玲仿佛覺得自己在財務上有點高高在上,于是她祭出營銷技巧的升級版——有所遮蔽的“賣慘”,她相對的財務自由,來之并不易,亦充滿不足為外人道的委屈。
三.身世營銷
原生家庭對作者的影響巨大,張愛玲終其一生都在和原生家庭做抗爭,這在她創作的早期尤其明顯。她對自己原生家庭的諸多不滿溢于言表,既展示給大眾前清貴族破落戶的生活,滿足大眾的窺視欲望和想象,又將成長時期的委屈和苦痛相對真實的呈現出來,從而達到多重營銷的目的。這些目的包括:對祖上榮耀生活的追憶;對童年幸福生活的緬懷;對父母失敗情感的傷感;對少年缺愛的埋怨;對時局艱難導致自身發展困境的嗟嘆等等,無不在敘述中將自己打造成一個看似錦衣玉食富貴人家,其實真實生活不如小家碧玉的悲涼人設,喚起讀者大眾對自己的同情,并化解一些潛在的階級對立。張愛玲的身世營銷是其營銷策略中最有技術含量也最成功的部分,于是《私語》的橫空出世既滿足了大眾,又成全了自己。“張愛玲筆下的悲劇人物,大多因為親情愛情的缺失、家庭婚姻的不幸,二導致產生了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憤恨等種種仇恨心理,他們或嫉恨他人幸福,或憎恨世界不公平或疾惡如仇,在仇視與憤恨的情緒、情感中糾結了一生、凄涼了一生、悲慘了一生。”④
1.父親的無力和暴戾
民國文學大家似乎都有一個父親缺席的童年和青少年,無論是肉體意義上的缺失,抑或成長過程中的父親作為精神引路人的缺失。張愛玲很顯然也遭遇了這種情況,甚至更加不幸。如果父親是單純的死亡,起碼不會對成長造成負面影響,他只是一個零而不是負數,張愛玲的父親在他看來陋習較多,就是個負數。如果父親貧窮而對成長無力顧及,起碼不會變成成長的阻力,張愛玲的父親到了后期就演變成一個阻力,逼得她不得不變成一個“娜拉”。
父親是張愛玲童年見到最多的人,但并不能稱為有效的“陪伴”,她對父親是骨子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摻雜了嫌惡的畏懼。“然而我父親那時候打了過度的嗎啡針,離死很近了。他獨自坐在陽臺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目直視,檐前掛下了牛筋繩索那樣的粗而白的雨。嘩嘩下著雨,聽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說些什么,我很害怕了”。后來畏懼嫌惡變成了悲憫和絕望:“另一方面有我父親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鴉片,教我弟弟做《漢高祖論》的老先生,章回小說,懶洋洋灰撲撲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強行分作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于我父親這一邊的必定是不好的,雖然有時候我也喜歡。父親的房間里永遠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張愛玲的青春還未開始便要結束,這樣的下午讓人想起《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房間,而父親的形象便幻化成《金鎖記》里曹七巧的癆病丈夫。張愛玲期待著改變,母親的回歸,為張愛玲陳腐的童年打開一扇窗。“中學畢業那年,母親回國來,雖然我并沒覺得我的態度有顯著的改變,父親卻覺得了,對于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說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學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壞的演說。他發脾氣,說我受了人家的挑唆”。父愛的缺失在青春期變成了暴戾的父愛,他不能容忍妻子其他而去之后,女兒也要棄他而去,父親此刻變成了曹七巧,絕望而有破壞力。“我父親趿著拖鞋,拍達拍達沖下樓來。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一陣踢。終于被人拉開”。這樣的暴力徹底摧毀了僅存的親情,于是升級為禁錮。“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墻,片面的,癲狂的”。禁錮到最后便是逃亡,張愛玲終于成功了。對父親的種種描述,也完成張愛玲為何顯得叛逆的解釋,不僅是對自己的解釋,也是對大眾的解釋,沒有誰愿意做一個家庭里的叛逆者,如果不出逃,就只有和他們一起腐爛。所幸,張愛玲的父親沒有用鴉片來禁錮她。對父親的敘述完成了自我營銷的一個質變,張愛玲不是不想做一個亂世中的乖女兒,而是一旦向父權低頭,自己也將墮入無邊的黑暗之中。
2.母親的缺失
在張愛父愛的缺失是家世營銷的第一步,但不是最重要的一步,可以模仿的母親,以及母愛的貧瘠,讓張愛玲所向往的光明生活變得不那么觸手可及。母親教會了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最可靠,一如亂世,只有腔子里的這口氣最靠得住。在她有意無意的展示中,母親一直是缺席的,無論精神還是金錢。張愛玲在某種上也是弒父娶母,但因為她是女性,只能自覺不自覺,半被迫的變成母親。
“最初的家里沒有我母親這個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從一出生,母親的不在場,并沒有對張愛玲的生活造成影響,只是覺得可有可無,這和傳統的“缺失的父親”大相徑庭。隨著母親的回歸,家中氣氛為之驟變,“我們搬到一所花園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話書,家里陡然添了許多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我母親和一個胖伯母并坐在鋼琴凳上模仿一出電影里的戀愛表演,我坐在地上看著,大笑起來,在狼皮褥子上滾來滾去”。母親像一個遲到的光亮,照進她昏沉沉的童年,帶來短暫的幸福,隱約中,此時的母親也變成她以后想要成為的偶像,她的生活不再暮氣沉沉。母親是那個時代的新鮮空氣,富有生機活力,英語,鋼琴無一不令張愛玲著迷。母親幾乎代表著所有美好生活的想象,她的形象對于廣大女讀者而言是一個最好的影響偶像,自由獨立,財務自由,盡管這財務自由是父權授予她的,張愛玲的母親之所以財務自由是由于繼承了她父親的遺產,但這并不妨礙她成為一個成功的娜拉,一個跳出夫權的勝利者。可歡時易過,父母婚姻的破裂,終結了稍縱即逝的快樂。“我父親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來,不拿出生活費,要我母親貼錢,想把她的錢逼光了,那時她要走也走不掉了”。母愛來得太濃烈又短促,更襯得父親的陳舊遲暮。父親的舉動不僅逼走了母親,也讓張愛玲情感天平嚴重傾斜,父親對她僅剩的牽絆開始松脫。“不久我母親動身到法國去,我在學校里住讀,她來看我,我沒有任何惜別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興,事情可以這樣光滑無痕跡地度過,一點麻煩也沒有”。家庭再無可念,母親不愿深陷泥潭只好再次動身出洋。希望來了又走,張愛玲失落可想而知。這種失落讓讀者尤其是女讀者感同身受,但又無可奈何,張愛玲的身世營銷通過母親的形象達到自身形象的重塑,一是母親這樣的獨立女性經濟尚且堪憂,張愛玲的母親除了靠遺產,自己是不能實現經濟再生產的,張愛玲不想走母親的老路;二是母親的心狠,也讓張愛玲對親情不再毫無保留的依賴,濡慕之情也不得不變成錙銖必較,甚至,在母親的幸福和女兒的幸福之間,母親毫不猶豫的選擇了自己。雖然后來到底母親還是拿出了錢供她讀書,但是張愛玲懂得世間再也沒有什么不問條件的愛了,所以也就別怪她是個涼薄而“貪財”的女作家。至少,在自尊心強烈的張愛玲看來是如此,連母愛都是要靠交換和看臉色才能得來。女人要想獨立,必須要經濟長期獨立,就連嫁妝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這和父親吸鴉片蕩盡家產也無區別,至少,在她張愛玲看來,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有錢的雙親只顧自己豪奢的消費從未在她身上毫無保留的付出過什么,就連學費都是預支的嫁妝。而且,她更明了想要獲得一個傳統意義上慈母的愛,是絕不能向一個洋派的母親去索取的。親情營銷的高潮是親生母親對于張愛玲前途的猶疑,她心目中宛若天使一般闊綽的母親也有凡人計較的一面,她好不容易斬斷前塵來投奔的母親,其實也不過如《傾城之戀》中那個勸她改嫁的母親一般“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在《童言無忌》中張愛玲不無遺憾的坦言:“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親情營銷的下一步是自尊自立營銷。
3.和繼母的關系
張愛玲和繼母的關系也是一大營銷策略,是張愛玲自尊自立營銷的前奏,自我的覺醒。帶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繼母,不排除她迎合讀者對“繼母”形象的想象,以強化自己的孤苦無依,而且相對于自己如天使一般的生母,后來的姨奶奶和繼母,無論從身份,教養、學識等方面相較,她們實在難以突破張愛玲的心防,張愛玲對她們的母親職責并不認同。她也希望她的讀者認同她的選擇,或者說她的選擇就是讀者們潛在的選擇。
張愛玲在《私語》中對那位姨奶奶的描述相對客氣,隱隱透著姨奶奶巴結她的意思:后來我父親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帶我到小公館去玩,抱著我走到后門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門,雙腳亂踢,他氣得把我橫過來打了幾下,終于抱去了。到了那邊,我又很隨和地吃了許多糖。小公館里有紅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圓桌上放著高腳銀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最重要的是姨奶奶不重男輕女,或者說她犯不著去培養有繼承權的弟弟:“姨奶奶不喜歡我弟弟,因此一力抬舉我,每天晚上帶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童言無忌》中:“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并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于心了”。這是發自內心的喜歡,因為這位姨奶奶始終保持著尊卑有序,顧忌著張愛玲的自尊。但張愛玲對姨奶奶的出身和學識實在不能茍同,她骨子里對父親的這位妾談不上深刻的欣賞。強烈的身份意識,令她對姨奶奶的示好只能做到情感上的接受,但難以達到精神層面。
后來的繼母和母親一樣也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但這位繼母和墮落的父親過于般配,這種落后的般配,以及這種般配的后續效應簡直就是對張愛玲成長的巨大阻礙。在《私語》中張愛玲首先坦言“我后母也吸鴉片”,她對父親愛吸鴉片無能為力,對后母的芙蓉癖則是略帶嘲諷的嫌棄,尤其是和興趣高尚的生母一對比,高下立判。而明媒正娶的繼母對妻子身份的在意也不斷刺激著張愛玲:“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里,為甚么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張愛玲認為繼母是自己的恥辱有個特別有名的例子,在《童言無忌》中:“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讓她穿舊衣服,張愛玲完全不能接受。以至于一直致力于和張愛玲搞好關系的繼母,因為張愛玲的刻意疏離扇了她一巴掌,彼此終于徹底的終結了名存實亡的母女關系。“回來那天,我后母問我:“怎樣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我說我向父親說過了。她說:“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里哪兒還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個嘴巴,我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過來拉住了。”雖然這段所謂的史實,張愛玲自己也在《雷峰塔》第三章中澄清過,繼母沒有打她,但這已不重要,張愛玲對繼母的反感顯而易見。繼母就是落后生活的直接化身,張愛玲連父親都可以嫌棄,就更不需要繼母來行使教養之權。
經過姨奶奶和繼母的對比,張愛玲在個人營銷上的“賣慘”更進一步,她和童話故事里的白雪公主,灰姑娘是同一類型的人物,更絕望的是,幾乎沒有人幫她。幸好,在逃出家門后被姑姑收留。
4.求學的艱難
自尊自立的形象營銷首先從考上香港大學開始,張愛玲不負眾望考取倫敦大學,因戰爭爆發只好改去香港大學。在那個年代女大學生人數稀少,女留學生就更加物以稀為貴。張愛玲的這一經歷踐行了自我奮斗的人設需要,她為自己的命運也曾孤注一擲的拼命過,她考上大學的經歷完成了一次極具人格魅力的營銷,激發了讀者的上進之心和認同之感,將張愛玲很容易的和男作者以及其他女作者區分開來,她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女讀者對女學霸的想象。
但戰爭的瘋狂無情的摧毀了她的奮斗之旅,《私語》中張愛玲:“不得不以考進大學,但是因為戰事,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來。公寓里的家還好好的在那里,雖然我不是那么絕對地信仰它了,也還是可珍惜的。現在我寄住在舊夢里,在舊夢里做著新的夢”。
肄業生的身份回上海謀生,她人生的第二次巨大挫折,令每一個讀者都為之扼腕嘆息,末世之感驟然而生。可淪陷區的上海,大學畢業生尚且不容易找工作,何況她這個肄業生,還是個女生。亂世求存的人設令每一位女讀者都心有戚戚,這不就是她們自己嗎?戰爭的恐怖,前途的叵測,生命的無常讓很多人躲回家庭:“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凄凄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里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于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但張愛玲并沒有選擇匆匆嫁人,她選擇了雙手劈開生死路,用自己的才華為自己掙得一個相對獨立的未來。她母親沒有做到的事,她做到了。
身逢亂世,成長的委屈,謀生的不易,每一次進步都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不正是每一位上海女性的生存困境嗎?張愛玲一步一步將自己變作她們的代言人,完成身份的終極營銷,也就是亂世中的生存營銷。張愛玲就是掙扎在上海普通的年輕女人,掙扎在上海的普通年輕女人就是張愛玲。
5.僅有的溫情
在苦難營銷的間隙,張愛玲也難得為自己保留了兩塊溫柔之地,一塊是姑姑,一塊是炎櫻。雖然這兩塊溫柔之地不可能像在家里那般毫無顧忌,可張愛玲這樣長期被生存這條瘋狗逼迫的涼薄之人迫切需要溫情的撫慰,她的受眾也需要舒壓。
《私語中》對姑姑的描述飽含深意和深情:“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然而我對于我姑姑的家卻有一種天長地久的感覺。我姑姑與我母親同住多年,雖搬過幾次家,而且這些時我母親不在上海,單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對于我一直是一個精致完全的體系,無論如何不能讓它稍有毀損”。“因為現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細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來撞去打碎東西,而真的家應當是合身的,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張愛玲如一艘漂泊的船,終于暫時找到一個可以停泊的港灣。也許最終她沒有變成她的母親,但好在終于變成了她的姑姑,一個沒有豐厚遺產卻可以自食其力的獨立女性。張愛玲的營銷手段在這里又深了一層,讓讀者更有代入感。不是只有她一個人可以獲得如此自在,只要努力每個女人都可以活得自在!但這樣的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的維系,畢竟她也只是借住在姑姑家中,姑姑再好,總不是親媽。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和她的姑姑都視張愛玲的母親為偶像,可最終兩人都因沒有豐厚遺產而不得不走向自食其力的道路,這也是廣大都市女性的共通之路。張愛玲通過姑姑的形象塑造,展示了都市女性最終之路,這也是她個人營銷所追求的結果,大家都沒有祖蔭,還是靠自己!
另一塊溫柔的樂園是炎櫻,沒有閨蜜的獨立女性是寂寞的,在張愛玲的自我營銷中,饒是她再有能耐,她也需要友情,無論是逛街還是作畫,總要有個人的陪伴。炎櫻是最好的選擇,外型一般,還是外國人,也不算窮,更好在彼此品味相似,真是沒有威脅的閨中良伴。張愛玲可以在文字中打造了炎櫻俏麗的形象,她仿若一個紅娘,或者一個不甚美麗的薛寶琴。
四.勞資營銷
張愛玲寫蘇青是其個人營銷最微妙的一環,蘇青也是女作家,作品銷量很不錯,而且還是自己的老板,最讓張愛玲欽羨的是蘇青的社交能力強張愛玲太多。大眾很期待這樣同性同量級的作家之間的評論。
張愛玲的散文營銷從來不會回避矛盾,甚至會把利害關系首先挑明,起碼看上去坦蕩,有些東西遮遮掩掩反而引人遐思。這也是張愛玲老練之處,與其被動的等人指摘,不如主動出擊,擺事實講道理,擺明利害,也顧及情理,于是深思熟慮通達老練的《我看蘇青》成了張愛玲的散文代表作。“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里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愿意有蘇青這么一個人存在,愿意她多寫,愿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代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荻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甘心情愿的”。張愛玲直言自己和蘇青的關系,但她也愿意和蘇青一個陣營,兩個人是真的在生活,也許蘇青的文藝技巧弱一些。甚至于張愛玲愿意承認自己欣賞蘇青多一些,哪怕是蘇青的世故,因為一個女人如果不世故,她怎么可以在亂世做老板,發稿費養活張愛玲呢?但蘇青好在是一個通透熱情體貼的好老板。“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并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并不是一個清淺到了一覽無余的人。”張愛玲更想通過蘇青的形象告知世人,作為相對弱者的女人,文人,尤其是女文人能夠自己養活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她張愛玲不介意成為下一個蘇青,蘇青是她想變成的樣子。“而且無論怎么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
張愛玲甚至是同情蘇青的,誰愿意出來在亂世拋頭露面呢?蘇青的丈夫依然無法養家,父權夫權的缺席,將蘇青一人拋向生活的最前線,并且一大家子人都靠她蘇青支撐,境況可能比張愛玲更慘,甚至離了婚有了錢的蘇青沒有時間戀愛。“蘇青是亂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么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于她的責任范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
張愛玲在蘇青身上看到了以后可能的自己,她也通過營銷的蘇青的形象告知她的讀者們,誰都活得不容易。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做亂世里的名女人難上加難,尤其還是離婚帶娃的名女人。
五.結語
張愛玲的散文營銷,到蘇青這里就是結尾了。至少在她孤島時期的散文中,除了父親弟弟幾乎沒有男性的出現,社會關系相對單純。令她的目標人群,也就是上海的獨立女性們深感愜意,張愛玲通過一連串的文字營銷,打造出一個她所預期的個人公共形象,培養了一大批代入感強,忠誠度高的受眾,完成了聲望和經濟轉換的雙贏。
注 釋
①宋聲泉.在“男女”與“時代”之間——重論《金鎖記》[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59(04):123- 132.
②計明月.女性視角下的上海與流言體敘事——張愛玲、王安憶上海書寫研究[J].當代教育實踐與教學研究,2019(14):235-236.
③董汶倩.真實人生的鏡像投射——論張愛玲《傳奇》中金錢書寫的緣起[J].名作欣賞,2020(23):105-107.
④楊錦鴻,汪稀稀.“恨”得化不開——論張愛玲小說的仇恨情結[J].江淮論壇,2019(04):169-173.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