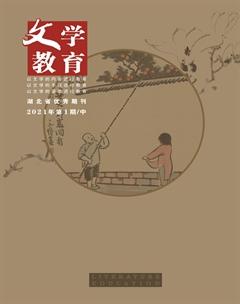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
方婕 馮裕智
內容摘要:浙江當代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不僅在譯介學、中日文學交流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諸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有利于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幫助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讓世界了解中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關鍵詞:浙江 當代文學 日本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從共和國誕生起,浙江當代文學即走進扶桑,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開始了在日本的譯介和傳播。尤其是1978年以來,我國政府采取構建法律框架、加強政策扶植、導入市場機制等措施,推進兩國圖書貿易交流,加快了包括浙江當代文學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對于增加中日兩國的文學交流、加深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要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之一,文學不僅要惠及國民,而且要走出國門。文學不僅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浙江當代作家創作了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浙江當代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時,由于種種原因,浙江當代文學受到了極大的忽視,使人難窺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譯介與傳播的全貌。研究總結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不僅在譯介學、中日文學交流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諸方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利于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幫助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讓世界了解中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從總體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傳播與歷史翻譯在日本,由于政治歷史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呈現為“1949年—1971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91年”、“1992年(我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至今”這三個階段。本文擬從以上這三個階段入手,探討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情況。
一.1949年—1971年
1949年以來,浙江作家作品中最早被翻譯成日語的作品是巴人(王任叔)的《遠東民族革命問題》和艾青的《煤的對話》、《魚化石》、《人皮》、《反侵略》。兩人的上述作品都是在1951年被譯介到了日本。《遠東民族革命問題》收入社會科學研究會編譯的《社會科學基礎教程續編》,《煤的對話》等作品收入世界抵抗詩刊行會編譯的中國抵抗詩集《從延安到北京》。這一時期艾青大部分被譯介的作品都是被收錄在詩集中且大部分都與新中國的成立和人民對侵略的抵抗有關聯。除了艾青的作品,夏衍的《毛澤東思想與創作方法:延安文藝講話發表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邵荃麟的《文學、藝術與共產主義:蘇同盟共產黨20回大會后的新的發展/文學》等。這一時期被譯介的作品大部分都與中國革命和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從1949年到1971年被譯介的共計51篇作品中,有40篇與中國的革命和政治有關,占比高達78%。
二.1972年—1991年
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一事件直接促進了中日的建交。1972年7月,田中角榮出任日本的新首相,并對外公開發表“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的言論,同年9月訪問中國建立外交關系,雙方還簽訂了《中華民族人民民主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部門聯合聲明》,之后中日敵對的局面得到緩解。而文學上的交流也從建交前的單一化逐漸向著多元化發展。這一時期被譯介到日本的浙江當代文學作品有:琦君的《下雨天的回憶》,這篇散文表達了作者在下雨天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對真善美品質的追求,對質樸無憂無慮生活的想念;徐遲創作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被譯介在日本評論社的《數學研討會》上。除此之外還有錢鋼關于唐山大地震的文章、吳晗關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文章、張抗抗與女性文學相關的作品《愛的權利》等。從以上的例子中我們能夠看出,這一時期被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類型百花齊放。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關注到的一點是,很多的作品雖通過譯介傳播到了日本,但若把原作在日本的反響與在國內進行對比,結果往往是失衡的。其中存在的原因有:其一,日本原有的市場已經一定程度上被本土和其他國家占領,影響深遠。其二,日本和中國的民眾到這一時期所經歷的生活、政治背景、國情等都存在差異,導致文學作品接受和理解上也有差別,難以引起共鳴。其三,中日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時間較短,出版社存在商業上的考量。這一時期的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同時也取得不小的發展,譯介更加的多元化,為日后的譯介與傳播打下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三.1992年至今
1992年,我國于10月15日加入了“伯爾尼公約”,又于同一時期加入了“世界版權公約”。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越來越重視知識的價值,懂得保護知識版權的重要性。這兩個公約都含有翻譯作品在不損害原作者的權利的前提下,受到與原著同等的保護的條約內容。創作是文化發展產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著作保護也是相對重要的領域,它的作用就是使人們重新關注社會文化教育領域,從而也促進了文學譯介作品的傳播。傳播的范圍不斷變大,影響就越來越廣,日本的出版社對浙江作家作品的引進也就發展的更加具有規范化,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這一時期,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余華共有十余部作品被譯成日文。余華出生于浙江杭州,是著名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深受廣大讀者的青睞。截至目前,余華的主要代表作品都被譯介到了日本。《活著》是余華作品中最早被譯介并傳播到日本的作品,譯者綿貫浩子并不是直譯《活著》這一書名,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將書名具體化,用簡短的日語詞組簡單易懂地表達了《活著》的主要人物與內容。除此之外,《第七天》、《十個詞匯里的中國》、《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的譯名也并非簡單的直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譯者所在國家的語言表達方式。
飯塚容是余華作品的主要日譯者,先后翻譯了《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余華的代表作。飯塚容是日本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早在大學時代便已經開始翻譯中國的著名文學作品。飯塚容曾翻譯過魯迅、曹禺、鐵凝等幾十位中國的著名作家的作品。除了飯塚容,余華作品的其他譯者在日本也有一定的影響力與傳播力。他們都是致力于向日本傳播中國文學作品的文學者,是連接中日文學譯介與傳播的重要人物。泉京鹿曾為翻譯余華的作品《兄弟》,向出版社極力推薦此書,詳細地介紹了余華本人、書的背景和此書在中國的影響等,最終才得到出版社的認可。
余華的作品以細致的敘述和獨特的話語系統,構建了一個個黑暗、殘酷的、令人深思的故事。正是其文字表達的獨特魅力,與文字間人性善惡的糾葛,吸引著讀者們的興趣,也吸引力了眾多的外國文學者。日本譯者對其進行譯介,傳播的不單是余華所敘述的故事,更是從另一種語言文字的角度解讀余華的作品。另外,《活著》通過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擴大了作品的影響力。在對余華作品《活著》的譯本介紹中都帶有這樣一句話“世界的名匠、張蕓謀監督により見事に映畫化された。“(由世界級名匠張藝謀導演將其電影化)。由此可見,《活著》得以被傳播至國外并被翻譯,不僅是作者余華本身和其作品的魅力被外國文學者所知曉了解,電影化的方式擴大了其傳播與影響的范圍。
但是從譯介的時間來看,余華的作品并未在風靡一時的時候就立刻被譯介到日本。《活著》首版出于1993年,在1998年榮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1994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版《活著》榮獲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的評委會大獎。但那時在日本,《活著》的表現極為平淡,反而在歐美風靡一時。直至2000年,《活著》才由綿貫浩子譯介到了日本。從此以后,余華其它的作品不斷被譯介到日本。不同國家對不同文學的接受與融合的程度不同,文學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譯介則為了文學的交流與融合創造了一個更好的平臺,能夠使不同國家的文學者們接觸并了解國外的文學觀念與思想。
從1949年至今,中國有很多作品傳播到了日本,浙江當代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譯介的作品數量不多但種類豐富。雖然在這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文學的傳播取得了進步,但還存在著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在實行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背景下,我們要增強文化軟實力,建立自立自強的文化形象,才能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增強話語權。我們能夠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20世紀以來我們的娛樂和學習的方式都在不斷的被改變,甚至獲取信息的方式都不一樣了。從報紙書籍到電影電視,最終發展成現在的電腦手機。人們是先觀看了影片,從而對作品產生了興趣,最終幫助作品的推廣,也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余華的作品也是通過電影才進一步打開了知名度。這樣的發展方式雖有缺陷,但危機與希望并存。時代在發展,文化想要更好的做出去,就應該走多樣化的道路。
第二,眾所周知翻譯作品的好壞對一部作品在國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翻譯的水平是至關重要的,對作品的域外傳播有非常大的影響。要重質量,在質量達標的前提下再加大數量。優秀的翻譯作品,譯者不僅要對兩國的語言非常精通,還要有較高的文學素養,而且對翻譯的作品十分了解。掌握翻譯理論和技巧的同時還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對自己的作品高度的負責,反復校對審核,并且盡可能的在貼合原著作的基礎上,做出適應日本本土化的改造。
第三,借助民間的力量并加以政策的扶持。即使是在以前因為政策上交流比較困難的年代,民間的能人志士也會想著各種方法維持兩國在文化上的交流。現在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去了解日本文學市場對中國文學的具體需求。我們可以借助民間文學團體更好的細化需求,有針對性的發展文化走出去。
參考文獻
[1]楊四平.現代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J].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4(03):95-100+107.
[2]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編.中國新時期文學邦訳一覧(増補·改訂版)[M].東京:駒沢大學総合教育研究部塩旗研究室,2007.
基金項目:2019年度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浙江當代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傳播”(201911058031),指導教師:馮裕智
(作者單位:寧波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