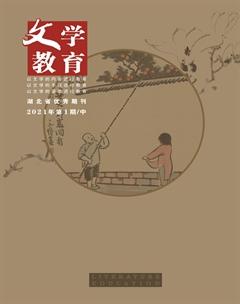土地的沉香
都說童年的味道是人一生最難忘記的味道,我的童年則留下了酒香,這讓我對酒充滿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情愫。
大約在我兩歲的時候,家里添了個小嬰兒,父親常年在外奔忙,母親身體羸弱。屋漏偏逢連陰雨,那年冬天,我又在保姆奶奶家里發生了點意外,母親一下子愁得瘦了好幾斤。“把蕾蕾送我這里來吧,只要你們不嫌條件差。”這時,是外婆向我張開了懷抱,這個懷抱從那時候起,便永遠地環繞著也溫暖著我了。
我們居住的小鎮,有一座小村子,是名“鰲頭山”。這里,曾經因為上不著天,下不著河,只能靠山吃山,相當貧窮。但,村子卻以苞谷酒名揚四方。
苞谷酒,是糧食釀出的酒,自然口感醇厚,香飄十里。村里也有不少人有釀酒的手藝,我想,外公是一定會這手藝的。我從沒有看見過他釀酒,他去世太早,在我六歲還沒能太有記憶的時候就故去了。卻不知為何,想到他就自然會想到鰲頭山的酒,想到他正穿了白衫黑褲和自編的草鞋,時時有微酒后站在山頭睥睨人間的那一種剛正和灑脫。
那時候,我這個小娃娃得到了身為一家之主的外公無限疼愛。農村家里來了客人,總要擺出一張平時不用的八仙桌,四條長凳。待客人們你謙我讓好不容易坐團圓時,外公會把我抱在懷里,我便隨著他的尊貴地位坐了上席。吃過什么都已忘盡,唯記得外公端著酒杯,與賓客笑言笑語穿梭來往,這時,一股嗆辣的味道直沖入我的鼻息,我卻沒有躲閃,反而貪婪地張大嘴巴呼吸那嗆辣中的特別芳香。對世界無限好奇的我,本能地接納了這經過特殊處理的糧食的味道。我乖乖的樣子讓外公不勝喜歡,他笑瞇瞇地拿筷子蘸上一滴酒,沾上我的嘴唇。看著我齜牙咧嘴卻多多益善的樣子,滿桌的客人都大笑起來,“只怕這個小娃子長大好酒量哩!”我似懂非懂,只隨外公臉上舒展開來的笑意感覺到了一種無法言說的快樂。
以后,但凡來了客人,看見外公的杯子里還有一點殘酒,我都要賴在他身邊,喊著:“嘗嘗,嘗嘗。”然而,外公是不會放縱我的,畢竟,我才三歲。后來,我換了說法:“聞聞,聞聞。”舉著外公的空酒杯,不停放在鼻前嗅,家里人無不被我惹得樂不可支。再后來,趁著外公不注意,我會把他的空酒杯拿起來偷偷用舌尖舔干……
沒有人知道,這個小娃娃為什么這么嗜酒。
六歲的時候,要上學了,我只好回到父母身邊。有一次,家里來了一位叔叔,父親與他對酌了幾杯小酒,我遠遠地觀望著,不動聲色。直到飯畢,父親送他出大門,母親往廚房端碗,趁這個空隙,我迅速而敏捷地把桌上父親沒喝完的半杯白酒一仰頭吞進了肚里。那滋味有多美妙?還沒顧上品匝三分,母親的腳步聲就從門外傳來了。有道是,做賊心虛。我正正經經規規矩矩坐在屋子里大氣不敢出,豈不知這樣子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母親進來湊近一聞一問,便明白了我的罪惡行徑。
酒,為何有如此之魔力,吸引著一個外表秀秀氣氣的小女孩?細想來,也許是那聲聲“不能、不準、不可以”更加激發了人對某種事物的興趣和新奇?終于,十二歲那年的暑假,回故鄉度假的我,與大舅家的表哥一起,趁家中無人,就著兩盤園蔬對飲,以一場大醉徹底放縱了自己對酒的迷戀……
當然,也因此滅絕了我與酒的因緣。
從此,酒,對我來說,不再香,不再甜。取而代之的,是苦,是辣,是暈眩是失憶是種種不可承受……那些聞酒香、偷喝酒的前塵往事如一場大夢,似乎并不在我的生命中存在過。偶爾故鄉來人,說起從前的故事,大笑之余,已覺渺然遠矣。
酒,棲身于天地之間的精靈,居住在糧食里的精魂,人們只可懷著珍惜的心情品嘗,不可任意放縱與泛濫。
神秘的,是美好的。萬物皆如此。這,大概是現在的我回憶起少年事所能明悟的吧。
只是每每聽到故鄉的名字,依然會想到它作為“酒鄉”的種種傳奇。在那片曾經被稱作“窮鄉僻壤”的黃土地上,為何盛產了“酒”這樣一物?再想起家族中包括我自己與酒的一些被時間沖不淡的記憶和往事,更覺有一種解不開的血濃于水的關聯存在。外公釀酒的手藝傳給了兒孫,這樣的代代相傳在故鄉并非奇事軼聞,在世人眼中,它或許與生計有關,或許與繼承有關,也或許沒有人去細想過流淌其中的血汗,體味蒸騰其中的悲歡,只是這滴滴清露、裊裊酒香中,濃縮了人世間一切任憑歌哭吟詠的滋味……
而今,一種名叫堯治河的酒成為故鄉甚至家鄉酒業的圭臬。堯治河,離我的故鄉鰲頭山村僅距離二十公里左右,當年同樣是一片貧瘠的土地。然而,這于貧瘠中奮飛涅槃的土地,不僅涌動流淌著一股令人驚異的力量,還滋生了慰人肝腸的甘泉——現代化的制造工藝與傳統的糧食釀酒完美結合造就了神奇的堯治河酒!
舉杯共觴時,誰能說,其中滋味,沒有暗含著那片土地的沉香?
張蕾,湖北保康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省市級報刊發表散文近百篇,出版散文集《鄉間花事》《行走河岸》,其中,《行走河岸》獲第八屆孟浩然文藝創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