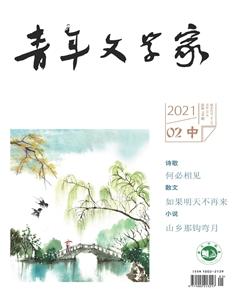淺析《活著》中的儒家家庭倫理思想
陳帥 石秋仙
摘? 要:本文通過對《活著》小說文本中以福貴為交點所構建的三個家庭圈子進行人子之責、人物言行舉止、家庭男女分工等方面探究,結合儒家思想的有關內容,綜合分析小說中蘊含的孝道、婚姻、男女兩性家庭關系等傳統儒家家庭倫理思想。
關鍵詞:活著;儒家;家庭倫理思想
作者簡介:陳帥(1998-),浙江金華人,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學生;石秋仙(1972-),河北保定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錢江學院教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5-0-02
引言:
在《活著》中,余華巧妙地以福貴為交點,構建起三個家庭圈子,在這三個圈子中,福貴和福貴爹娘構成的第一個家庭是舊社會地主家庭的縮影;以福貴、家珍、鳳霞、有慶構建的第二個家庭組成在舊社會,發展在新社會;鳳霞二喜組建的第三個家庭則完全處在新社會。而通過閱讀,我們可以發現,盡管三個家庭連接的時間線跨過了新舊社會的分界,但它們在前腳踏進河里的同時,后腳依然保守著井的規矩,在這三個家庭種,無論是成員關系、構成模式,還是組織分工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儒家倫理思想的影子。
一、孝道
儒家以“禮”作為發散點、“仁”作為目的點形成的思想體系部分中,“孝”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部分,歷來是傳統道德的根本,而家庭倫理所對應“齊家”,是儒家看來是人達成“修身”之后與社交圈子產生的第一步聯系。
福貴身上“孝”的體現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破產前。破產前的福貴是浪子形象,在這個階段,福貴的家庭意識單薄,對個人感觀愉悅的追求是生活的全部,家中的百畝家財是他享樂的資本,這種資本使得他對人際關系的處理上始終處于一種理所應當的“上風”位置,比如,讀私塾時對先生所說的“好好聽著,爹給你念一段”[1],這是經濟基礎剝奪文化話語權的赤裸裸的體現,而私塾作為儒家德育的載體,福貴與私塾先生的隔閡寓示他和儒家傳統德教相背離,是儒家孝道的反面教材。
在儒家的體系中,“仁者愛人”之愛以血緣關系區別親疏,以宗法等級區分遠近。《禮記》中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道之大者也”[2],“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3]“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4]親親和尊尊是人道的發端。如果說在上文中,面對“天地君親師”的“師”,福貴的出言不遜是在“尊尊”層面對禮制暴力突破,那么,當福貴爹明白福貴“做生意”的實情時,他的嚴厲管教受到福貴的強烈反抗,福貴既還口又還手,這就在“親親”上叛離了儒家的孝道。
第二個階段在福貴破產后。破產后家珍被接走,福貴想的是得養活他娘和鳳霞,這里體現的就是家庭倫理中的事親,《孟子》:“事,孰為大?事親為……事親,事之本也。”[5]從這里開始,福貴逐漸開始向傳統的倫理框架回歸。“儒家家庭責任倫理思想要求子女對待父母,既應該滿足其物質需要,更應該關注他們的精神世界,從而實現‘養與‘敬的和諧統一。”[6]生計所迫下地做農活,對他娘說“娘,你趕緊回去吧。”這是福貴在悲痛過后第一次表達對家人的關心。《紀孝行》中載:“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7]破產后的娘常說:只要人活得高興,就不怕窮,則不僅是困難中的激勵,也是生活的一個反映;福貴娘年老病發,福貴連夜去城里請郎中;等到戰事得脫,回到家知道母親的病亡,福貴的表現是哀痛的,可見,重回倫理之下的福貴是不折不扣的孝子形象,這在一個側面上可以理解為福貴意識中孝道意識的蘇醒,即青年時期坐擁資本想沖破傳統的福貴依然是無法脫離儒家思想框架的,這不僅體現儒家思想影響之深,也同時反映出當家庭運行面對出現跳脫預計的現實,縱欲之惡向道德之善的人性轉變是余華思考給出的道路。
二、婚姻觀念
《活著》中家庭倫理還體現在家庭構建上。“儒家認為婚禮所奠定的夫婦關系是人倫之始。如果沒有婚姻結成穩定的夫妻與其子女的家庭關系,那么孝道無從談起。”[8]在中國古時的規制中,男女婚姻“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時避不開的環節,這兩個傳統由來已久,《禮記·曲禮上》中記載:“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9]可得“媒妁之言”是成婚的必要條件,《詩經·齊風·南山》寫道:“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10]可見“父母之命”也是成婚的必要因素。媒妁之言可以當做 是風俗形式,但是父母之命往往并非只充當男女青年婚配的橋梁作用,《禮記·昏義》:“昏禮 者,將合二姓之好”[11],父母之命更多出自于家族利益的考慮,畢竟這種形勢下讓年青一代 結婚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滿足男女雙方的感情和愉悅需求,而其作用于家族的興旺和延續才是雙方父母更多的考量,是實現兩家間經濟往來和力量結盟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才可視作是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規范。
這一點在福貴和鳳霞兩個家庭圈子的組成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的規矩即便是浪蕩如年輕時候的福貴也是不容易越界。他也得回家找父母出面托媒人出馬才能抱得美人歸。家珍作為米行的千金,不僅有條件穿月白色旗袍和時髦的高跟鞋,而且在當時,她的家族還能有條件供一個女子上夜校,福貴家當時正是“瘦的半死的駱駝和馬大”,走路帶錢響,倆人正是門當戶對,地主作為階級權力的代表,米行作為經濟實力的代表,福貴家珍兩人的結合背后是米行兩個家族的強強聯手,即“有錢人嫁給有錢人”,這也符合千百年來儒家在家庭婚姻倫理方面一貫的認知。在后文有慶死后,鳳霞的出嫁一樣遵循這樣的傳統。二喜是縣城戶口,職業賺錢多,但是偏頭,鳳霞勤勞肯干,漂亮善良,但是聾啞,雙方各有缺陷。可見隊長作為媒人,在幫鳳霞物色如意郎君的時,依然是在門當戶對的標準下篩選符合條件的最優人選。
三、兩性家庭倫理
《周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12]性別有別之后,夫婦關系即為人倫之始,《禮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13]又,《禮記·郊特牲》:“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14]儒家的夫婦關系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是分工與活動范圍,雙方的活動分為“外”“內”兩個獨立領域。“外”是男性的活動空間,“內”是婦女的活動空間。男性獨擅家庭之“外”的社會生產與社會交往,即“男主外女主內”之說;二是男女兩性的地位有別,從生產力的角度,從進入父系社會開始形成“男主女從”形式,隨著歷史的強化,這種形式最終形成“男尊女卑”。《荀子》載:“請問為人夫?日: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15]丈夫作為“主”,要善待妻子,不放蕩胡來,講究禮儀,注意夫婦有別,而妻子作為“從”,在配合男性作為“主”的行為上,遵循若夫循禮義,就柔順聽從,如不循,就惶恐,自己保持肅敬的原則。“在男權統治下,女性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獨立人格和話語權,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女性的社會價值被漠視,成為男性的附屬物,只能‘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16]
在福貴及其爹娘、福貴家珍和子女的兩個家庭圈中,福貴爹希望福貴能光宗耀祖時,福貴娘并沒有當面說破,只是“偷偷”告訴福貴他爹年輕也說過同樣的話;福貴喜歡去妓院,家珍做菜暗示以警,福貴娘采用的是指桑罵槐的方式揭福貴爹的老底;這些不公然說開道事的舉動無疑是在明面上維護她們丈夫的尊嚴。福貴賭輸破產后,福貴爹出面訓斥,而福貴媽則是當時回避,事后心疼,同樣體現出家庭關系中的男性占據主導地位。福貴賭博鉆妓院,即荀子所言的“夫無禮”,而家珍從來采取逆來順受的守勢,委婉勸誡福貴戒嫖,即便在外是勸福貴戒賭,所做到的程度也只是保持沉默任憑福貴踢打,只能用無聲的力量進行堅持,這就體現儒家家庭倫理中“女從男”的男女不平等一面。鳳霞、二喜組成的第三個家庭圈中,二喜娶鳳霞進城,她的家庭分工也由原來的田地勞動力變成在家里掃地織毛衣,而“外”的責任依舊是二喜承擔,這標志著她的女性分工角色回歸到原本倫理規范的框架之下,這種轉換是男外女內傳統意識下自然自覺性完成的。
四、小結
儒家思想作為影響中國至今的最具有代表性文化符號,它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歷經千年沉淀下來的精髓,從它在歷史中對中國家庭倫理的合理思考和長期實踐、不斷探索與完善補充得出的成果總結中探尋作品的價值效果是站在其他角度所不能比及的。傳統文化給予了余華創作充足的養分,《活著》中三個家庭從不同的正側面展現儒家作為傳統正統思想在中國家庭中的影響力,其中亦承載對人性惡善、兩性關系等社會話題的價值思考和道德辯證,在呼喚社會對家庭倫理的重新審視過程中發揮有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8.
[2]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67.
[3]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117.
[4]楊伯峻.孟子譯注[M].2版.北京:中華書局,2005: 179.
[5]楊伯峻.孟子譯注[M].2版.北京:中華書局,2005: 189.
[6]趙燕.儒家責任倫理的當代價值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7.
[7]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167.
[8]唐祉星.兩戴《禮記》孝道思想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16.
[9]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171.
[10]王秀梅.詩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57.
[11]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230.
[12]陳戍國.周易[M].長沙:岳麓書社,2002: 172.
[13]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247.
[14]胡平生,張萌.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7:254.
[15]方勇,李波.荀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5:112.
[16]呂紅平.先秦儒家家庭倫理及其當代價值[D].保定:河北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