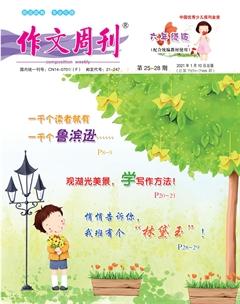父親都是藝術(shù)家
孫道榮

作文本收上來了,他在昏暗的燈光下,一本本批改。這次的作文題目是《我的父親》。
他覺得,這些跟隨打工的父母進(jìn)城的孩子,事實上,對自己的父母了解得并不多,而尤其讓他擔(dān)憂的是,有的孩子對自己民工身份的父母,懷著一種自卑和輕視。他希望通過這篇作文,讓孩子們對自己的父親,更多一點理解。
一篇篇作文看下來,基本都是寫打工的父親怎么辛苦,如何勞累。這也難怪,民工子弟學(xué)校的家長,不是工地上的泥水匠,就是烈日下的清潔工;不是忙碌于餐館的服務(wù)員,就是奔走在樓道的送水工……
又翻開一本。作文的標(biāo)題讓他眼前一亮——《我的藝術(shù)家爸爸》。藝術(shù)家?這怎么可能!在這所條件極其簡陋的民工子弟學(xué)校,哪可能有藝術(shù)家的子女?本能的感覺是,這個孩子是虛榮心作怪,在編故事。
他好奇地讀下去。孩子寫道:我的父親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工作室,里面堆滿了大小、粗細(xì)、厚薄不一的木頭和木板,空氣里彌漫著木頭的香氣,地上到處都是卷曲的刨花,而在刨花下面,是泥土般細(xì)碎的木屑,刨花是木屑土上開出的花朵……
難道孩子的父親,是位民間雕刻家?他止不住好奇,繼續(xù)讀下去。接下來,孩子筆鋒一轉(zhuǎn):沒錯,我的爸爸是一位木匠,但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藝術(shù)家。
看到這里,他忍不住“撲哧”一聲樂了,果然只是一位普通的木匠。再讀下去,他的笑容凝固了。孩子寫道:爸爸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位普通木工,那些大樓里的很多木工活,都是爸爸做的。他靠自己的汗水,養(yǎng)活了我們一家。爸爸雖然只是一位木匠,但他心靈手巧,木頭在他的手里,仿佛有了生命。剛搬到出租屋時,我們家一無所有,很多東西都是爸爸親手做出來的。比如我做作業(yè)的桌子,是爸爸用工地上廢棄的邊角料做的,其中的一條腿,是用四截短木棍連接起來的,每個榫眼都嚴(yán)絲合縫,整張桌子,甚至沒用一根鐵釘。
孩子驕傲地寫道:爸爸經(jīng)常會帶些小玩具回來,給我和妹妹,那是他利用午休時間,用碎木塊做出來的。我12歲生日時,他給我做了只木刻小公雞,那是我的屬相,至今仍掛在我的床頭。有一次,房東看見了小公雞愛不釋手,以為是從哪個精品店買來的。因為他也屬雞,爸爸就給他也做了一個,還按照他們家每個人的屬相,各做了一個木刻。爸爸給我做過手槍,做過棋盤,做過文具盒,還幫我們學(xué)校修過桌椅呢。
最后,孩子寫道:爸爸是建筑工地的木工,我沒看過他在工地上做過的東西,但我想,那些住進(jìn)大樓里的人,一定像我一樣,使用過并會喜歡上他做的東西。爸爸因為貧窮,沒讀過幾天書,不然,他一定會成為藝術(shù)家。不,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位藝術(shù)家,他是能讓每一根木頭說話,讓每一片刨花唱歌的藝術(shù)家。
他的眼睛濕潤了……
(選自《生命時報》2013年7月9日,有改動)
品讀
文中做木匠的父親,不僅用微薄的收入負(fù)擔(dān)了一家人的生活,還用精湛的手藝將普通的生活點綴得幸福無比。泥水匠、清潔工、服務(wù)員、送水工這些普通人,雖然身份、工作平凡質(zhì)樸,但他們用辛勤的勞動創(chuàng)造著城市的美好生活,也是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藝術(shù)家”。
- 作文周刊·小學(xué)六年級版的其它文章
- 形象鮮明 事例突出(上)
- 良藥苦口利于病
- 歇后語談《三國》
- 我班有個“林黛玉”
- 團(tuán)圓松濤
- “大胃王”官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