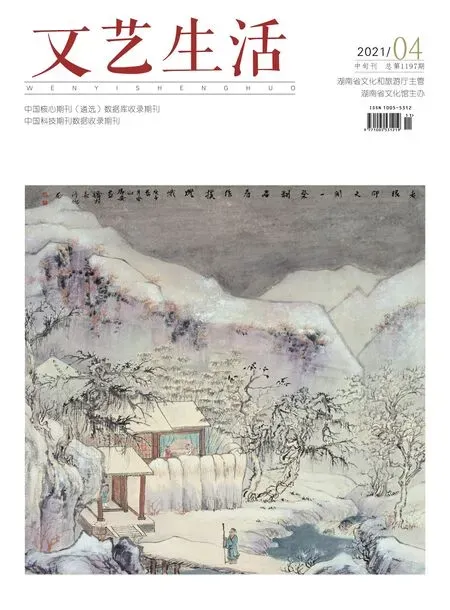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長安十二時辰》
——國產古裝劇的野心與短板
韓 笑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00)
一、前言
《長安十二時辰》在“靜悄悄”第一次放出劇集后就得到了豆瓣8.7分的高分,最終獲得8.3分的成績,評價數為三十多萬,算得上2019年的優質網劇。故事的主角張小敬出身行伍,后受任為主管偵緝逮捕的官差“不良人”,長期協調維護地方安全工作,但卻因違法被關押于獄中。負責長安城治安的靖安司發現了混入城內的可疑人員,由于張小敬對事發地點人事與地理的熟悉,靖安司特例委派張小敬戴罪立功、偵破此案。經過張小敬的一番調查,發現敵人的陰謀是為了在上元節晚上的集會中制造混亂,而張小敬必須在上元節花燈大會前抓住搞破壞的刺客。在一次次的斗智斗勇中,張小敬在最后關頭揭穿了背后主謀,阻止了破壞的發生,而這一疑案的主謀是自信能做宰相卻懷才不遇的八品官員徐賓。
對比我國以往的古裝懸疑劇,《長安十二時辰》顯然在視覺效果方面有明顯的進步和變化。2.39:1的畫幅類似電影的寬銀幕,可以在鏡頭內容納更多的內容,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張智華所著的《電視劇類型》中提到,古裝劇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藝術的娛樂本質的強調,①所以在視覺上滿足觀眾的需求甚至提高觀眾整體審美水平都是創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本劇注重光線的造型作用,運用長鏡頭、運動鏡頭展現人物和場景,改變了以往古裝電視劇的主要攝影方式,能夠觀眾更好的觀賞體驗。同時,本劇存在編劇、節奏的問題,劇中塑造了很多具有鮮明特征的角色,最突出的是男主角,一個東方“反英雄”式的人物——張小敬。除主角外,許多角色存在不符合邏輯的行為,未能將所有人物塑造成典型人物。由于故事設定在24小時,故48集的長度需要對故事節奏進行嚴格把控,而電視劇在某些情節的設計中過于注重小人物的心理狀態而忽略了整體故事的推進,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節奏混亂和與主題的偏離。
二、注重鏡頭語言的造型作用
攝影風格取決于故事和劇情的設定,也離不開創作團隊。《長安十二時辰》的導演曹盾和攝影指導荊沖善于使用戲劇化的色彩和光線,善于拍攝大場景,剪輯節奏快,在形式上更像電影畫面。而《瑯琊榜》的導演孔笙有多年電視劇拍攝的經驗,基于劇中人物的設定,《瑯琊榜》的光效遵循了自然主義,鏡頭克制而沉穩,剪輯節奏慢。《長安十二時辰》在人物活動的影像空間營造方面,于室內有豐富的光線運用,室外則構筑了一個主人公高速運動的擁擠的都市空間,都有助于塑造世事紛擾中的英雄人物。②
(一)戲劇性光效刻畫人物和場景
本劇借鑒了好萊塢戲劇電影的光線處理,造型強調主體和空間的結構,強調修飾光的運用,在效果光的使用上,注重視覺效果而不注重真實的表現。③由于故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內,所以具體到每個時間點的光線氛圍都具有微妙的變化,光線的控制需精確到每個時辰。在不同的地點,光線展現特定環境的氛圍;在塑造每個人物時,利用光線來塑造此人或陰暗或陽光的個性。光線在劇中不僅起到了塑造人物的作用,還肩負著推動敘事、延展時空,以及于細節之中展現唐時代特征的任務。較硬的光線和高對比度的色彩有利于增加畫面的力量感,以此適應唐朝繁盛時期的氣場,本劇在大場面遵循自然主義光效的基本方向,而在細節刻畫上則使用更多的戲劇性光效。
例如在第一集奠定全局的色彩基調:以暖色調為主,使用偏冷和偏青的色調修飾個別環境。劇中故事發生的時間設定為晴朗冬季的正月十五這一天,冬季太陽高度角較低,所以光線能夠直射進室內,人工光線形成從窗口投射進室內的狹長光線,形成了冬季暖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其實在實際生活中不論哪個朝代光線都是一樣的,劇中之所以用暖色調作為基調以及曝光過度的光線,還因為暖色調有利于展現回憶的事件,從而將整體的故事與現代觀眾隔離開,似在講述遙遠、夢幻而又真實的故事。
人物方面,張小敬出場的第一個鏡頭是在牢獄中,他的臉處于黑暗中,只有他的眼睛上有透過墻壁的洞口射進來的部分光線。一方面這樣的光線氛圍交代了他所處的黑暗的環境,另一方面也暗示著他即將面對一個重生的機會,死刑犯即將擁有生的希望。在初入靖安司的部分,相對于李必面部的明亮,張小敬是始終處于畫面的暗部的,即使是在和李必處于同一個光線環境下,兩人的中景拍攝也是有著光線的區別。此時兩人的地位差別顯而易見,主角在劇情中還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人物。
(二)長鏡頭展現動作場面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導演用了大量長鏡頭來拍攝動作場面,使得打斗動作一氣呵成。在以往的古裝懸疑劇中用長鏡頭來展現動作場面的并不多,大部分沒有大量的打斗場面。而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動作戲分量多,鏡頭內部的運動克服了長鏡頭本身容易帶給觀眾的疲憊感,配合密集的鼓點,動作場面的長鏡頭變得流暢而過癮。而大多在這個時候,節奏變快,觀眾會覺得被劇中人物推動著前進,從而產生深入劇情的緊張感。對于《瑯琊榜》來說,在戲劇沖突集中的段落基本是由演員的表演和臺詞來展現。《瑯琊榜》中雖然其穩重、冷靜的鏡頭都適用于表現人物和劇情設定中儒雅的文化氣息,但畢竟沒有在造型手段方面進行大范圍的突破,所以它的故事的確比形式更令人稱道。
三、劇情與主題短板
(一)反派塑造失敗
劇中徐賓這個人物的存在頗有為了反轉而反轉的嫌疑,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所謂的“兵諫”策劃了劫持君主的案件,利用了退伍士兵、外邦刺客,甚至是當朝宰相和太子,只為提醒帝王他怠政的事實以及顯示自己的才能。對比劇中前半部分對徐賓的刻畫,人物的動機明顯不足,最終甘愿被射殺,徐賓這個人物也難以站得住腳。對比原著,電視劇的反轉實在多余。其次是龍波和林九郎,劇中極力渲染了反派林九郎的虛偽,展現了一個古代中國左右逢源的權臣形象。在主角完成自己任務的過程中,林九郎顯然是造成主角和龍波先前悲劇的罪魁禍首,而被君主寵信使龍波將矛頭對準玄宗。在親身經歷過社會對自己家庭的傷害后,一個為了殺掉玄宗而活著的反派竟在危機時刻為了保護了玄宗的性命而獻身,轉而追求自己作為一名士兵的意義。同時劇中并未給主角和林九郎更多的矛盾沖突,林九郎的反派形象顯得可有可無,他最終只充當了阻礙主角完成目標的障礙之一。而在《瑯琊榜》中,反派與主角的關系處理得當,反派即主角完成任務過程中最大的阻礙。
(二)改編失敗
主人公及戰友龍波的回憶顯得多余,反派龍波即主角張小敬的戰友蕭規,在多年前的戰役中兩人存活下來,也因為上級的錯誤失去了幾百位戰友。對回憶場景的具體描繪有助于展現龍波和張小敬聞無忌的情誼,以及張小敬作為士兵對長安人的擔當。本次事件只是龍波復仇的原因之一,而本劇卻用了大量篇幅刻畫普通士兵面對戰爭的抵抗。創作者大概欲借此批判將軍蓋嘉運和右相林九郎,上層官僚為了自身前途命運而罔顧人命的無恥行為。而到故事結尾,罪魁禍首也并未獲得應有的懲罰。相比原著,電視劇為了反轉而增加了眾多人物和劇情。原著中策劃此案件的主謀自殺,未能找出兇手,而也就無人關注其背后支持的安祿山,符合作者對“平凡的充滿危機的一天”的設定。而在電視劇中,弱化了安祿山,增加了動機不足的主謀,君主依舊怠政,造成多年前悲劇的兇手并未受到懲罰,張小敬也在又一起悲劇中再次認清了上位者的本質,故劇中的這些人物并未獲得成長。
(三)落后的價值觀
本劇增加了很多權貴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一方面為主角的目的設置障礙,另一方面映射古代中國帝王權術和官場的負面影響,創作團隊的野心是在懸疑劇中增加古代宮斗戲碼。而實際上這些敘事是多余的,包括太子的猶豫,都像是在碎碎念。劇中所體現的觀念不外乎寄希望于一個明智的君主,而以“有能力”對權臣辯護,人們沒有建立更好的制度的訴求。從主角的性格特征來看,他并沒有能力對上位者和反派的錯誤進行有效的矯正,只是在對方的控制下艱難地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電視劇成功塑造了一個“為救一船人不惜犧牲一個人”的英雄形象,但過于注重古代權術的描繪,并未揭露君主專制下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反而美化了反派的動機,極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國古代仁的觀念。
與此相比,《瑯琊榜》在價值觀上就先進許多。主角雖同樣是名義上的罪人但能量無限,能夠實現逼迫帝王改正錯誤,為家族正名,扶持開明君主,在古代朝廷懲惡揚善、激濁揚清的任務,并為此犧牲了自己的婚姻甚至生命。雖然展現的依然是帝王將相的故事,但塑造了一個理想的儒式英雄形象,主角梅長蘇集合了東方式英雄的優點,整部劇也體現了宏大的歷史格局。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劇的創作者在視聽語言方面的優勢為《長安十二時辰》贏得好評是自然的,但在劇情方面的短板也暴露無遺。觀眾總是由淺入深地觀看,更為優秀的視聽效果呈現也是目前古裝電視劇正在努力的方向,而這也是目前國產古裝劇所能達到的水準。但在一片華麗之下,故事的內核和正確的價值觀才是真正考驗創作者水平的內容,國產古裝劇的目的并不只是給觀眾創造一個歷史的時空,更重要的是我們從故事中獲得對現在的價值觀念更有用的補充。
注釋:
①張智華.電視劇類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22).
②陳鐳.由《長安十二時辰》透視古典人物之“黑澤明”式投射[J].電影評介,2019(15):31-34.
③劉永泗.影視光線藝術[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278).
——以《在一起》中的《救護者》單元為例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