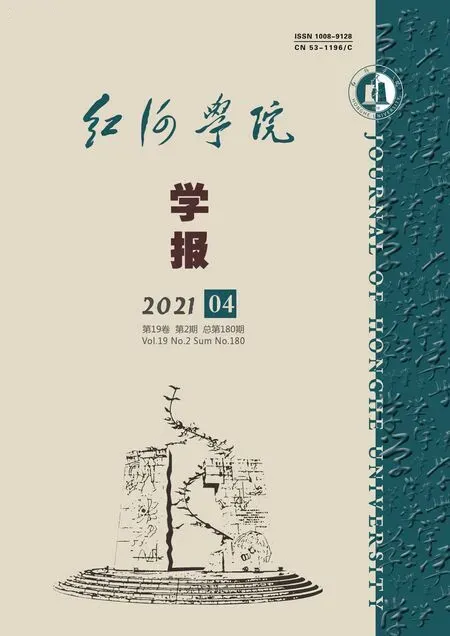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對負性情緒的影響
——樂觀的中介作用
周碧薇,錢志剛
(蚌埠醫學院精神衛生學院,安徽蚌埠 233030)
社會適應是個體心理健康水平和社會化發展的重要指標。[1]大學階段是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適應是否良好直接影響大學生的學習生活,還將會影響其今后的工作與發展。[2]當前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有留守經歷大學生已成為大學生的主要群體。但由于早年“留守”的經歷和進入大學后所面臨環境劇變的雙重壓力,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的社會適應狀況不容樂觀。[3]社會適應不良是指個體成長與周圍環境呈現不和諧、不平衡的狀態。[4]研究發現相較于無留守經歷大學生,有留守經歷大學生更容易出現自我評價偏低,人際交往敏感退縮,在學業、就業等問題上常表現出猶豫不決、消極應對。[5-7]如果個體長期處于社會適應不良的狀態中,就會嚴重損害身心健康。
根據有關大學生心理健康的調查結果中顯示,大學生遭受負性情緒困擾的個體逐年增多。[8-9]在影響大學生負性情緒的眾多因素中,社會適應不良的作用尤為突出。研究發現情緒與社會適應關系密切,社會適應不良可引發個體精神緊張進而產生焦慮、抑郁,甚至自殺意念。[10-12]在一定程度上,適應狀況的改善可降低負性情緒水平。[13]
已有研究證實,社會適應不良作為一種負面影響給大學生帶了諸多情緒困擾,但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處于社會適應不良狀態的個體都有負性情緒,這就說明某些保護性因素在發揮作用,樂觀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樂觀是指對未來期望積極結果或相信好而非壞會發生的傾向。相關研究顯示,樂觀負向預測消抑郁,樂觀水平越高,體驗到消極情緒越少。[14-15]樂觀水平的個體表現出較高積極情感水平,較低的消極情感水平。[16]樂觀不僅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也是一種解釋風格[15],樂觀的人在面對壓力與問題時,更能夠積極應對,認為事情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樂觀可以以緩解社會適應不良對個體造成的不利影響,減少自身負性情緒體驗。[17-18]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由于特殊的成長史,社會適應問題更為凸顯。本文以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擬考察樂觀在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對負性情緒的影響中的作用,以期為改善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提供實證借鑒。
一 對象與方法
(一)對象
選取安徽省3所高校大一、大二在校學生為被試,共發放問卷700份,有效回收問卷661份,問卷有效率94.4%。其中:女生428人55.8%;大一學生340人,占51.4%;大二學生321人,占48.6%;有留守經歷學生233人,占35.2%;無留守經歷學生428人,占64.8%。
(二)研究量表
1.社會適應不良量表。該量表采用由余益兵等人編制《青少年社會適應狀況評估問卷》的消極社會適應分量表。[19]量表共有23個題項,包括消極退縮、自我煩擾、社會疏離和違規行為四個維度。采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5點計分,得分越高說明個體社會適應越消極。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0.77。
2.樂觀主義—悲觀主義量表。該量表是袁立新等人編制,共有11個題項,包含樂觀和悲觀2個分量表。[20]采用1(非常贊同)—5(非常反對)5級評分,本研究將樂觀主義分量表反向計分后,與悲觀主義分量表原始得分相加得出總量表得分。總量表得分越高說明樂觀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的Cronbach's α系數0.87。
3.抑郁—焦慮—壓力量表(簡體中文版)。該量表是Lovibond編制,龔栩等人修訂成簡體中文版。[21]用來測評個體在過去一周內負性情緒體驗,問卷共21個題項,包含抑郁、焦慮和壓力3個維度。問卷采用4級計分,0-3分別表示“不符合”到“總是符合”。得分越高,說明負性情緒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數為0.86。
(三)方法
使用Spss20.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采用因子分析進行同方法偏差檢驗;采用T檢驗考查有留守經歷大學生和無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的差異;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考察各變量間的相關性;采用Mplus7.0構建結構模型。
二 結果
(一)共同方差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方法統一收集數據,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因而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其結果顯示,共有9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個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30.05%,小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二)有留守經歷和無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的差異
對有留守經歷和無留守經歷大學生的社會適應不良得分進行差異檢驗,其結果(見表1)。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得分顯著高于無留守經歷大學生(t=5.43,P<0.001),有留守經歷大學生在自我煩擾、社會疏離維度得分顯著高于無有留守經歷大學生(t=2.71,7.82,Ps<0.01)。但在消極退縮和違規行為維度得分兩者沒有顯著差異(t=0.88,0.81,Ps>0.05)。

表1 有留守經歷和無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的差異(±s)
(三)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樂觀和負性情緒的相關性
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可知,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各維度與負性情緒各維度間呈顯著正相關(0.432≦r≦0.574,Ps<0.01),樂觀與社會適應不良和負性情緒各維度均呈顯著負相關(-0.723≦r≦-0.491,Ps<0.01)。

表2 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樂觀和負性情緒的相關分析(r,n=233)
(四)樂觀在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與負性情緒之間的中介作用
在相關分析基礎上,以社會適應不良為自變量,負性情緒為因變量,樂觀為中介變量建構結構方程模型模型。其結果顯示,模型各項指標X2=28.936,df=18,RMSEA=0.061,CFI=0.985,TLI=0.976,SMR=0.030均符合擬合標準,表明擬合情況良好,該模型是可以接受的(見圖1)。

圖1 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樂觀和負性情緒中介模型
為進一步檢驗、分析中介效應,本研究采用Bootstrap程序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隨機重復抽取1000個樣本,計算95%的置信區間,如果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設中介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其結果顯示,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 負性情緒,95%的置信區間為(0.259—0.597),置信區間不包含0(P<0.001),說明直接效應顯著;社會適應不良樂觀的負性情緒,95%的置信區間為(0.226—0.548)(P<0.001),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樂觀在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與負性情緒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值為0.387。
三 討論
(一)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現狀
社會適應是指個體無論在何種環境條件下,都能客觀認識,積極調整行為,使自身的心理狀態很好地適應環境,是衡量個體社會性發展和社會成熟的重要標志。[1研究發現,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得分顯著高于無留守經歷大學生,這一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是一致的。[3]家庭和父母是影響大學生社會適應的重要外在因素。個體成長過程中,父母的支持、陪伴,積極的教養方式有利于青少年社會適應發展。[22-23]有留守經歷大學生在童年期,普遍缺少父母心理關愛,大多數留守兒童與父母的交流僅限于“學習成績如何”“身體是否健康”。而其自身心理成長的困惑被表現了“好的學習成績”“能否考上大學”的外表下。[5]加之進入大學后,面臨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條件和個人素質差距,學習生活環境、方式改變,負面影響進一步增大,有留守經歷大學生所產生的社會適應不良也越來越明顯。本研究還發現在消極退縮和違規行為兩方面,有或無留守經歷大學生之間的無顯著差異。這可能是由于在特殊成長環境中,能夠通過自身努力考入大學的學生,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和意志力,注重學習,能夠遵守學校規范,希望能夠通過學習,擁有與父輩不同的人生,改變自己的命運。
(二)樂觀在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與負性情緒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過中介作用分析發現,樂觀在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與負性情緒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說,社會適應不良對負性情緒水平的影響是通過樂觀人格特質這一中介變量來實現的。社會適應不良作為一種負面存在,必須通過個體的內部才可以起作用,而人格因素是壓力對個體產生影響之優劣的關鍵因素。[24-25]樂觀是指向未來的積極期望。[26]對于有留守經歷大學生來說,在面對社會適應不良時,樂觀作為一種積極、保護的因素,可以對負面情境作出積極的情感應對,以減輕自身的負性情緒體驗,幫助個體恢復身心平衡。相反,有些大學生在經歷適應不良時,則會悲觀失落,使自身沉浸于不良的情緒體驗中,無法自拔,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樂觀可以被看成心理彈性的成分,能夠緩沖社會適應不良的不利影響,增強個體的積極情緒體驗。
四 結論
根據前述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社會適應不良會增強個體負性情緒體驗;二是增強有留守經歷大學生的樂觀水平可能緩解社會適應不良的不利影響,提升積極情緒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