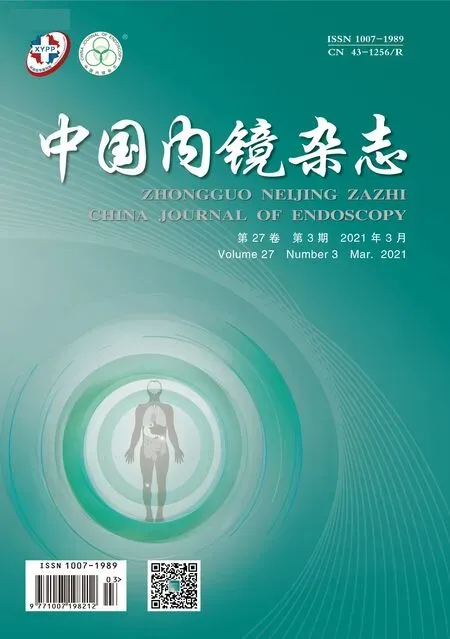腹腔鏡下肝切除與開腹肝切除術對原發性大肝癌患者遠期療效、胃腸功能及氧化應激反應的影響*
周祿科,楊潔,劉林,陳健,謝輝
(德陽市人民醫院 肝膽胰外科,四川 德陽618000)
目前,對于原發性大肝癌的治療仍以根治性手術為主,開腹肝切除術發展較成熟且主要向精準肝切除發展,而腹腔鏡下肝切除術為近年來新發展的微創技術[1-3]。隨著腹腔鏡技術的發展,其可達到與開腹手術相當的效果,且具有微創的優勢,但腹腔鏡技術使用二氧化碳氣腹,會影響患者微循環狀態,可能導致預后不良[4-5]。近年來,關于腹腔鏡下肝切除與開腹肝切除術對患者遠期療效、胃腸功能及氧化應激反應影響的研究較少[6]。本研究旨在通過分析兩種術式的上述指標,進一步探討腹腔鏡技術的優勢與不足,以期為此類患者臨床術式的選擇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3年2月-2016年7月97例在本院接受手術治療并隨訪至2019年10月的原發性大肝癌患者的病例資料。根據患者接受的治療方式,分為對照組(n=50)和觀察組(n=47),對照組行開腹肝切除術,觀察組行腹腔鏡下肝切除術。對照組中,男32 例,女18 例;年齡49~73 歲,平均(59.03±14.27)歲;腫瘤最大徑5.4~9.7 cm,平均(7.19±2.04)cm;Child-Pugh 分級:A 級38 例,B 級12 例。觀察組中,男27例,女20例;年齡47~76歲,平均(58.74±14.19)歲;腫瘤最大徑5.3~9.8 cm,平均(7.15±2.11)cm;Child-Pugh 分級:A 級33 例,B級14 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腫瘤最大徑和Child-Pugh 分級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1.1 納入標準①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1年版)》[7]的相關診斷,并經病理學檢查確診;②腫瘤最大徑為5.0~10.0 cm;③未出現肝內外轉移;④患者神志清醒,可配合進行相關治療;⑤手術均由同一組醫護人員完成。
1.1.2 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的心、肺和腎等重要臟器疾病者;②合并其他肝臟疾病者;③合并其他惡性腫瘤者;④臨床及隨訪資料不全者。
1.2 方法
1.2.1 觀察組行腹腔鏡下肝切除術。患者仰臥或取頭高足低位,視病變部位將手術臺向左或右傾斜,建立氣腹,壓力控制在12~15 mmHg,置入Trocar使其圍繞病變部位呈扇形分布,以5孔法為主。先對病變程度及腹腔總體情況進行探查,手術過程中以超聲確認腫瘤位置,并在超聲輔助下標記預切線,視腫瘤生長情況決定手術方式及肝血流阻斷方式。先以超聲刀游離肝周韌帶,以鈦夾夾閉離斷肝左/右三角韌帶。從肝表面開始在電刀及超聲刀聯合下,逐步切開離斷肝組織,血管及膽管在鈦夾夾閉后離斷,采用內鏡下直線切割閉合器完整切除腫瘤及其周圍組織,以雙極電凝對斷面滲血進行處理,當出現活動性出血時,以3-0 或4-0 可吸收線進行縫合,用無菌蒸餾水對肝斷面進行反復沖洗,以確認無明顯的活動性出血及膽汁漏。經腹操作孔擴大切口或恥骨聯合上橫切口,將切除標本取出。斷面徹底止血后噴灑止血粉,常規放置引流管。
1.2.2 對照組行開腹肝切除術。麻醉方式與體位選擇同觀察組。以倒“L”切口入腹,用全方位拉鉤充分暴露術野,入腹后探查,肝臟游離切除方式同觀察組,視腹腔情況選擇是否對第一肝門進行阻斷,阻斷時間控制在15 min/次以內,視腫瘤部位和大小決定行規則或非規則性肝切除,斷面處理方式及引流管放置同觀察組。
1.2.3 術后處理兩組術后均常規行抗炎保肝等治療,術后3 d 復查胸腹CT 平掃,視情況拔除引流管,出現局限性積液者可在彩超定位下行穿刺置管引流,7~10 d 后拆線。出院后定期門診隨訪,對血常規、肝功能和甲胎蛋白(alpha protein,AFP)等實驗室指標進行檢查,并行腹部彩超或增強CT 檢查來確認復發情況,乙肝患者常規復查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抗體并行抗病毒治療。術后前2年每3個月復查1次,第3年開始每6個月復查1次。復發者視病情嚴重程度選擇手術切除或射頻消融等治療。
1.3 評價指標
對比兩組患者手術一般情況、遠期療效、胃腸功能、氧化應激反應和并發癥發生情況。①手術一般情況: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等;②遠期療效:比較兩組患者總生存期及無復發生存期,總生存期為術后至死亡或隨訪截止時間,本研究隨訪截止時間為2019年10月14日;無復發生存期指術后至腫瘤復發的時間;③胃腸道功能和氧化應激反應:比較兩組術前及術后3 d 的胃腸功能指標[胃泌素(gastrin,GAS)、胃動素(motilin,MTL)、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CCK)]和氧化應激反應的指標[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和晚期氧化蛋白產物(advanced oxidation protein products,AOPP)];④并發癥:比較兩組患者惡心嘔吐和胸腔積液等并發癥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行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手術前后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以Kaplan-Meier 法繪制生存曲線,并以Log-rank 檢驗進行比較。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一般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與術中出血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術后引流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明顯較對照組短,兩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手術一般情況比較 (±s)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conditions of surg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表2 兩組患者手術一般情況比較 (±s)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eral conditions of surg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組別對照組(n=50)手術時間/min 231.04±50.18術中出血量/mL 473.19±87.05術后引流時間/d 6.75±1.84術后住院時間/d 14.93±2.48觀察組(n=47)t值P值233.15±49.73-0.29 0.774 459.06±90.17 0.79 0.434 4.25±1.09 8.08 0.000 11.02±3.08 6.91 0.000
2.2 兩組患者無復發生存期及總生存期比較
2.2.1 無復發生存期對照組中位無復發生存時間為17個月(95%CI:14.532~19.468),觀察組中位無復發生存時間為23 個月(95%CI:20.845~25.155),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94,P=0.087)。見圖1。

圖1 兩組患者無復發生存期比較Fig.1 Comparison of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2.2 總生存期對照組中位總生存時間為31 個月(95%CI:27.931~36.092),觀察組總生存時間為34個月(95%CI:29.743~37.06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6,P=0.692)。見圖2。

圖2 兩組患者總生存期比較Fig.2 Comparison of overall surviv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3 兩組患者胃腸道功能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術后GAS 及MTL 水平均明顯下降,對照組下降幅度較觀察組更大;兩組患者術后CCK 水平均明顯升高,對照組較觀察組升高更明顯;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胃腸功能指標比較 (±s)Table 3 Comparison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表3 兩組患者胃腸功能指標比較 (±s)Table 3 Comparison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注:?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
組別術后143.85±15.16?GAS/(μmol/L)術前75.94±13.09術后13.68±4.16?術后69.04±10.29?對照組(n=50)MTL/(ng/L)術前156.83±19.38 CCK/(pg/mL)術前9.42±3.01 152.07±17.91?-2.45 0.016 77.26±11.04-0.34 0.734 11.94±3.75?2.16 0.033 73.11±7.18?-2.25 0.027觀察組(n=47)t值P值159.06±20.01 34.44 0.003 10.07±3.28-1.02 0.322
2.4 兩組患者氧化應激反應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術后SOD 水平均明顯下降,對照組下降幅度較觀察組更大;兩組患者術后MDA與AOPP水平均明顯升高,對照組較觀察組升高更明顯;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氧化應激反應指標比較 (±s)Table 4 Comparison of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表4 兩組患者氧化應激反應指標比較 (±s)Table 4 Comparison of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注:?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
組別MDA/(u/L)術前18.93±3.62術后64.05±8.81?術后31.07±6.92?對照組(n=50)SOD/(μg/mL)術前21.49±5.18術后12.37±2.75?AOPP/(μmol/L)術前30.18±6.90 18.29±4.09 0.82 0.416 56.27±8.05?4.53 0.000 26.74±5.81?3.33 0.001觀察組(n=47)t值P值20.63±4.29 0.89 0.377 16.24±4.11?-5.48 0.000 29.37±7.26 0.56 0.574
2.5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術后均未出現膽漏、出血和肝功能衰竭等嚴重并發癥,對照組出現7 例(14.00%)Clavien-Dindo 分級在Ⅰ至Ⅱ級的輕度并發癥,其中惡性嘔吐1例、疼痛3例、發熱1例、床旁輸血2例;觀察組出現6 例(12.77%),其中惡性嘔吐2 例、胸腔積液2例、發熱1 例、肝功能不全1 例,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原發性肝癌為臨床常見惡性腫瘤之一,我國東南沿海為高發地區。據調查,全球每年約有50 萬的新發肝癌患者,其中超過半數的患者發生在我國,肝癌在國內腫瘤致死率中排第3位[8-9]。臨床上根據病灶最大徑將肝癌分為4 個等級:>10.0 cm 為巨型肝癌,5.0~10.0 cm 為大肝癌,2.0~4.9 cm為小肝癌,<2.0 cm 為微小肝癌,以原發性大肝癌較為常見[10]。目前,對于肝癌的治療仍以外科手術切除為主,開腹肝切除術為傳統的治療術式,可實現精準肝切除,但該術式創傷較大,腹腔鏡技術因其切口小、創傷小和恢復快等優勢,逐漸被應用于肝切除手術中[11-14]。但兩種術式的療效仍存在一定爭議,腹腔鏡技術因其自身的限制,對于腫瘤直徑較小、位于肝實質內的病變難以做到準確定位。因此,本研究選擇腫瘤直徑5.0~10.0 cm的大肝癌患者進行研究。
本研究中,兩組患者無復發生存期與總生存期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與以往研究[15]結果基本一致。本研究中,雖然兩種術式手術時間與術中出血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觀察組在術后引流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這主要與腹腔鏡下肝切除術對患者創傷較小有關。腹腔鏡下手術可有效縮短切口愈合時間,加上該術式具有視覺放大的效果,手術操作過程中術野更為清晰,可在多角度放大后,充分對病灶周圍組織的解剖部位進行詳細觀察,避免術中對周圍組織的牽拉,可有效減少對機體的刺激和組織液的滲透,從而縮短引流時間與住院時間。
對于腹腔鏡下肝切除術的研究,多集中于臨床療效與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方面,關于胃腸功能及氧化應激反應方面的探討較少。腹部手術可通過多種途徑對交感神經系統造成刺激,抑制胃腸神經叢的興奮神經元,且精神因素和腹腔內炎癥反應均可對患者胃腸功能造成影響[16-17]。MTL的主要作用是誘導消化期間移行性運動復合波,從而加速胃腸道的排空;GAS則具有刺激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的作用,對促進胃腸道運動及胃黏膜生長有較好的作用;CCK的主要作用在于刺激胃酸及膽汁的分泌,抑制回腸對鈉和水的吸收,同時還有部分調節血糖的作用;上述指標皆可有效反映胃腸功能[18]。本研究顯示,觀察組對上述指標影響更小。腹部手術對胃腸道功能影響機制主要有[19]:①手術對腹壁、胃腸等病灶部位周圍組織牽拉,可引起各部位神經叢的抑制,影響胃腸道激素的分泌;②手術對機體創傷造成應激反應,對GAS 等胃腸道激素的分泌造成影響;③全麻時可抑制M細胞及G細胞的分泌功能,可對胃腸道激素的分泌造成影響。腹腔鏡手術因在組織牽拉及局部創傷的控制方面較開腹手術有明顯優勢,因而對胃腸功能的影響更小。氧化應激反應為臨床手術創傷程度的重要評價指標,MDA及AOPP主要反映氧自由基生成量,SOD則為體內重要的抗氧化物質。腹部手術時可通過以下方面引起氧化應激反應[20]:①術中對機體的創傷可刺激中性粒細胞,從而使中性粒細胞來源的活性氧在降解細胞碎片時產生大量氧自由基,引起“呼吸爆發”,導致出現氧化應激反應;②手術對機體造成的應激反應,使體內兒茶酚胺自身氧化而產生大量氧自由基;③手術過程中使腹腔臟器在空氣中長時間暴露,接觸大量的氧分子而引起氧化應激反應。本研究顯示,觀察組患者氧化應激反應程度明顯較對照組輕,主要與腹腔鏡手術對機體的刺激更小、術中腹腔組織在空氣中暴露程度及暴露時間更短有關。
綜上所述,采用腹腔鏡下肝切除與開腹肝切除術治療原發性大肝癌,兩者的遠期療效及并發癥發生情況相當,但腹腔鏡手術對患者胃腸功能和氧化應激反應的影響較開腹手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