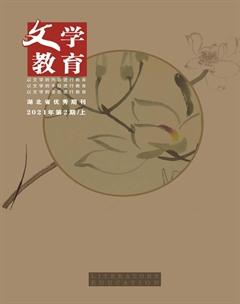家族式的精神涉渡
燈塔是一個堅固的詞語,它驅散了黑暗的恐懼,寄存著人們在絕境中對于生活的懷想與希望,指引著眾人的精神涉渡。江子的《世襲的燈塔》是一篇家族式的生存寓言,岱山的葉氏家族,四代子孫以三條人命的代價締造了燈塔工的守望精神。在長達百余年的時光中,燈塔照亮了大海上航行的人們,卻把葉氏一家的傷痛留給了流逝的歲月。在精神層面上來看,葉家的“世襲”是一種對家族式生活信念的堅守,充滿了明知犧牲但義無反顧的人間大愛。
在書寫《世襲的燈塔》前,我能察覺出江子對葉氏家族史料的提煉以及對詞語的尋找。無疑,燈塔是首先進入江子腦海的關鍵詞,它與葉氏家族從事的職業和身份休戚相關,于是,我們看到前三段江子對于燈塔意義的闡釋。“燈塔,乃是每座島嶼上的必備之物。”燈塔的作用與功能在江子的筆下是一種顯性的描述,從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島與時間意義上的黑夜著筆,江子的描述直接而精準。“對夜晚泅渡的船只,是領引,是慰安,是勸誡,是救贖。”燈塔的重要性在第二自然段又被江子上升到了“神靈的手指”的高度。在一步步的推進之中,江子自然會想到寺廟中的燃燈者,這種引申和聯想使得葉氏家族的職業具有某種神性的特征,即卑賤的職業之中蘊含著人性深處的大愛。換句話說,燈塔工的事業籠罩了一層神性的光輝,他們的職責在于為生命指明航行的方向。
在充分辨析燈塔的意義或曰考據燈塔的精神內涵之后,江子將自己的筆法宕開,回到歷史的細節之中:光緒年間,年輕的漁民葉來榮,陰差陽錯成了孤島上的一名燈塔工。在對葉來榮日常生活的想象中,江子傾注了強烈的個人情感。比如葉來榮是如何消遣時光忍受孤獨的?他是否讀書與喝酒,抑或自言自語和放聲唱歌?這種想象是真切而合理的,它寄寓了一個寫作者對主人公的無限懷想。從光緒到宣統,葉來榮在歲月的更迭中逐漸變得衰老,大海禁錮了他的生活半徑。后來,葉來榮的兒子葉阿岳子承父業,也成了一名燈塔工。在葉阿岳走上海島之前,江子對葉來榮的心理活動進行了合理虛構,葉家父子之間的長談是一次靈魂事業的交接,他們因為守望燈塔緊緊聯系在一起。
不幸的是,葉阿岳在一次臺風襲擊小島時喪身大海。燈塔成為葉來榮一家揮之不去的傷痛,葉來榮送走了兒子,卻將孫子葉中央帶上了海島。葉中央在19歲那年成為一名守望燈塔者,他的身上既有祖父葉來榮的殷殷期望,也有自身對于燈塔事業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堅守。在江子的筆下:“我寧愿認為葉家這一歷經三代的從業選擇隱藏了神性。我愿意認為守望燈塔為生命導航本來就是神靈在場的工作。”江子的話道出了葉氏家族的某種宿命,在為眾人指明航向的工作中,葉氏子孫“難逃劫數”,這儼然是一種神靈的指引。在葉中央守望燈塔的歲月里,他的妻子和女兒在來島團聚的途中喪命大海之中,命運的無情與戲弄再次降臨在這個本來就痛苦不堪的家族身上。
值得慶幸的是,葉中央并沒有從島上下來,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葉氏家族對于燈塔事業的執著和堅守,這種家族式的精神涉渡事業得以繼續。葉中央的選擇帶有某種與命運較勁的味道,展現出一個男子漢骨子里頑強與剛硬的生命質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葉中央“世襲”的是一種高貴的精神品格,一種不愿屈服、固守信念的倔強。在《世襲的燈塔》結尾,江子將葉氏家族的精神進行了適當的延展,那些“在機器時代依然執守手工業時代的倫理和道德的人”,這些在時代車輪無情碾壓之下的鮮活個體生命,他們以一己之力維護著人類固有的美德與倫理,毫無疑問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江子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從葉氏的家族史中提煉出了兩個關鍵詞——“燈塔”與“世襲”,“燈塔”是文眼,“世襲”既是時空的延展,也意味著燈塔精神的傳承。回到現實生活中,我覺得江子對于詞語的尋找也是敏感而精準的,在一次文學活動中,江子以“老區”和“冒犯”為題,以自己特有的語調盡顯江西式的幽默風趣。那天聽完江子的發言,現在看完《世襲的燈塔》,我仿佛能看見一位寫作者在與詞語擦肩而過時的審慎與小心翼翼,他用自己全部的目光打量著這些風塵仆仆的“遠游者”。
周聰,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湖北省作協第二屆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