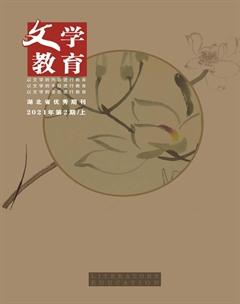淺談蘇軾散文中的儒釋道三教思想
黃昱
內(nèi)容摘要:進入宋朝,儒、釋、道三教在思想層面上進一步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漸被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合一”所替代。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為士人提供了獨特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使宋代士人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性格。作為宋代著名文人,蘇軾無疑是融合儒釋道三教思想文人的代表,蘇軾的散文也成為其儒釋道三教融合思想的重要體現(xiàn)。從蘇軾的散文出發(fā)探究蘇軾對儒釋道三教思想的吸收與轉(zhuǎn)換對于探討蘇軾以及宋代文人處事態(tài)度和當時的文學狀況都有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蘇軾 儒釋道三教思想 散文
中國古代文人思想呈現(xiàn)儒教、佛教、道教三教的對立與融合。進入宋朝,儒、釋、道三教在思想層面上進一步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漸被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合一”所替代。儒家提倡積極入世,鼓勵文人盡己所能報效國家;佛教則教導文人隨緣、淡然;道教追崇歸隱和避世。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為士人提供了獨特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對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轉(zhuǎn)化也讓宋代士人形成了頗具時代特色的文化性格,與前此歷代(特別是唐代)相比,其思想觀念、處世心態(tài)與生存方式等皆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使他們熱情參與政治,而道家任自然、輕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脫的思想又使他們能超然對待人生的榮辱得失。“三教合一”化解了入世與避世的矛盾對立。作為宋代文人的佼佼者,蘇軾無疑是融合儒釋道三教思想文人的代表,蘇軾的豪放豁達的人生觀展現(xiàn)了他對儒釋道三教思想的具體運用。在中國文學史上還出現(xiàn)過由蘇軾及其父、弟創(chuàng)立的以儒為宗,通過融通三教、兼采諸子的蜀學體系。前人對于蘇軾三教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從蘇軾的詩詞入手。本文擬從蘇軾的散文出發(fā),分析蘇軾散文里所體現(xiàn)的儒釋道三教思想。
蘇軾的人生經(jīng)歷十分復雜,自元豐二年(1079年)烏臺詩案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人生經(jīng)歷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軾的創(chuàng)作。蘇軾前期仕途順利,頗受皇帝重用,因而其詩文更多體現(xiàn)儒家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包含憂國憂民的思想。自烏臺詩案后,蘇軾在政治上屢遭打壓,三度被貶,其詩文則更多體現(xiàn)佛教道教尊崇的歸隱、無為,從積極進取轉(zhuǎn)換為對平淡生活的向往、對人生風雨的豁達。
一.前期以儒教思想為主的仁政安民思想和排佛思想
蘇軾早期的儒教思想受家鄉(xiāng)崇儒風氣和家學淵源影響。蘇軾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四川眉州儒學風氣歷來興盛,在蘇軾為家鄉(xiāng)所作的記文《眉州遠景樓記》里有“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jīng)術(shù)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nóng)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jīng)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于郡縣胥史,皆挾經(jīng)載筆,應(yīng)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xiāng)。”蘇軾的父親蘇洵也是頗有名望的儒學家。在地方儒學傳統(tǒng)和家學的教育下,蘇軾從小學習儒家經(jīng)典,并以儒家經(jīng)典所推崇的積極入世、忠君報國、仁政愛民為自己的目標。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在禮部會試時以《刑賞忠厚之至論》居第二名。在這篇文章中蘇軾論述了古代圣明的君主以忠厚為本、慎于用刑的仁政思想。雖然此文中有些典故不可考,但文中所體現(xiàn)的諸如“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等仁政愛民,賞罰分明的治國思想實則是蘇軾儒教思想的體現(xiàn)。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任監(jiān)察告院。此年元宵宋神宗為了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高興,下旨在汴京訂購浙燈四千多盞,在元宵收買時卻壓低收購價。蘇軾對朝廷皇帝的做法極為不滿,于是上書《諫買浙燈策》。在這篇諫文里,蘇軾先指責朝中官員沒有做到為人臣子的本分“皆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又批評宋神宗取悅長輩勞民傷財甚至“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痛陳貧苦制燈者是“賣燈之民,皆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為君者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否則就會失去民心,蘇軾在《諫買浙燈策》所提倡的就是仁政愛民的思想,這與儒教思想的核心“仁”、“仁政”如出一轍。蘇軾對儒教思想的吸收不僅體現(xiàn)在于對儒教積極處世態(tài)度吸收還體現(xiàn)為對儒教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的追求,在蘇軾早期的政論、諫書中,以儒教思想為主的仁政安民思想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此外,蘇軾早期思想也存在排斥佛教的部分。在蘇軾治平四年(1067)所寫的《中和勝相院記》里蘇軾十分直接的指出佛教思想是難以成功的、荒謬的,他認為當和尚對于社會家庭沒有一點貢獻,是一種不明智的做法。此文中的“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于農(nóng)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幸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發(fā)者之多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都是蘇軾早期排佛思想的體現(xiàn)。
不難看出,蘇軾早期的思想是完完全全的儒士思想,崇尚為國家社會做貢獻,因此早期蘇軾不喜佛教。蘇軾真正轉(zhuǎn)向佛教,是在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烏臺詩案”給他帶來的傷害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并在另外的宗教信仰中找尋出路。
二.后期以佛道思想為主的豁達超越思想
蘇軾在經(jīng)歷了烏臺詩案貶官黃州后,從關(guān)注社會政治,轉(zhuǎn)向了自我探求。在閱讀佛經(jīng)、道家典籍與和尚道士交往的過程中,蘇軾逐漸改變了早期對佛道教的看法,因此他在思想上呈現(xiàn)以佛道思想為主的豁達超越。南宋汪應(yīng)辰說:“東坡初年力辟禪學,其后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臆度,以文字解說。”佛教追求的是超越生死和羈絆,認為人的死亡只是存在方式的一種改變,死亡不是一切的結(jié)束,而是新的開始。道家則推崇“無為”,順應(yīng)自然歸隱。佛道思想相結(jié)合呈現(xiàn)的就是一種超脫物外無拘無束的思想境界。
蘇軾于元豐五年(1082年)在黃州所寫的名篇《前赤壁賦》就是蘇軾思想受佛道影響的集中體現(xiàn)。文中的“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和“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所呈現(xiàn)的超然物外與自然合二為一的心理是道教思想的核心,而超越生死存亡的“無我”境界又是佛教所推崇的。在這里,禪和道雙重寬慰讓蘇軾內(nèi)心的痛苦得以解脫,從而達到內(nèi)心的平靜,也就達到了道家所倡的“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此外,在蘇軾于元豐七年(1084年)改汝州安置即將離開黃州時應(yīng)安國寺僧首繼連之邀所作的《安國寺記》中,蘇軾還詳細地回顧了居黃州期間的生活及思想變化。蘇軾從早期的排佛轉(zhuǎn)變成“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這體現(xiàn)了蘇軾經(jīng)烏臺詩案后轉(zhuǎn)向佛老以尋求慰藉,思想開始向佛道傾斜的變化過程。
但蘇軾的尋求佛老,與一般文人所指的以沉溺宗教思想境界回避現(xiàn)實困難,希冀成佛成仙不同,蘇軾的轉(zhuǎn)投佛老并非為了“出生死,超三乘”。在他的《答畢仲舉書》中,蘇軾談了自己對學習佛老的體會和看法。蘇軾尋求佛老其目的是“期于靜而達”,是為了從佛老中汲取思想支持,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凡塵俗事的困擾中達到精神的超越,這也是宋朝大多數(shù)文人所追求的“仕隱”。
三.最終呈現(xiàn)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思想
在仕途通達時,蘇軾表現(xiàn)出積極入世、忠君濟民的儒家思想;在仕途處于逆境時,他又表現(xiàn)出道家的“無為而治”和佛家的“靜達圓通”。蘇軾行儒教之道,卻又從佛老中為自己找到精神支持。蘇軾對儒道佛三教思想兼收并蓄,批判繼承,出神入化,從而構(gòu)筑了詩人完美的文藝境界。在他的《南華長老題名記》就有“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的文字。蘇軾在此文中肯定了佛教與儒教的同等地位,與以往的偏于一方不同,他的思想已經(jīng)真正實現(xiàn)了三教融合。
縱觀蘇軾一生的文章,從前期關(guān)注儒教仁政愛民到烏臺詩案居于黃州轉(zhuǎn)向佛老思想,直至最后實現(xiàn)儒釋道三教思想的融合。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交雜于一身,讓蘇軾的思想最終呈現(xiàn)儒教為主、佛老為輔的“外儒內(nèi)禪”的人生觀和藝術(shù)觀。這種三教合一的思想不僅成就了蘇軾的文章,更成為了蘇軾獨特人格魅力的重要顯現(xiàn)。
參考文獻
[1]張玉璞.“三教合一”與宋代士人心態(tài)及文學呈現(xiàn)[D].曲阜師范大學,2009.
[2]李之亮注譯.唐宋名家文集·蘇軾集[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
[3]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賈來生.蘇軾三教思想探微[J].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3期,第61-64頁.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