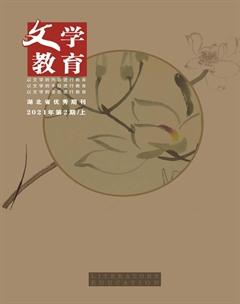芥川龍之介《地獄變》的敘述者與不可靠敘事
彭紹輝
內容摘要: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地獄變》選取故事中的人物“家仆”作為敘述者,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限知敘述,這種模式下的敘述者以“講述”而非“展示”的方式敘述故事,帶上了鮮明的個人傾向性。這種敘述模式與故事內容和風格完美契合,成功地制造了故事懸念,深化了小說內在價值。同時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存在著意圖的矛盾分裂,敘述者根據其個人立場不斷作出與隱含作者言行、價值判斷不相符合的不可靠敘述,加大讀者的理解難度,成功地延宕了讀者發現真相的時間。這為小說制造了令人極為驚駭的心理沖擊效果,帶給讀者更強烈的心靈震撼和更深邃的審美體驗。
關鍵詞:《地獄變》 敘述者 第一人稱 限知敘述 不可靠敘述 隱含作者
《地獄變》作為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不僅深刻地拷問了人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藝術至上的觀念。小說主要講述鬼才畫師良秀生性孤傲怪誕,癡迷繪畫同時也深愛女兒,但女兒受到崛川大公覬覦,在為貴族崛川大公繪制《地獄變》圖時被大公算計,親眼看著女兒被燒死,但也目睹了他想看到的地獄般的景象,最終良秀在倫常與藝術之間的矛盾糾纏中最終自我毀滅。在故事的講述上,小說采取第一人稱限知敘述的模式,借助大公家的仆人的有限視野及其不可靠敘述,與故事內容、風格良好契合,成功地展現了一個氛圍詭譎而又引人深思的奇幻故事。
一.敘述者的選擇
在這樣一部小說中采用第一人稱限知視角的敘述方式,芥川龍之介顯然有著他的特殊用意。首先從小說整體而言,故事本身還是比較簡單的,崛川大公因想占有良秀之女而不得,便利用繪制《地獄變》的機會迫害良秀父女,主線情節曲折之處不多,但給讀者的感受卻非常豐富,這不僅僅在于良秀在面對女兒被燒死時所表現出的既痛苦又喜悅的矛盾感受,也體現在故事的敘述使讀者無法一眼就把作品看穿,促使讀者細細咀嚼,由此加深了小說的內涵,使之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小說安排了在崛川大公家工作了二十年的仆人作為故事的敘述者,他在故事中有自己的獨特身份。作為敘述者,他為讀者講述這個故事,里面的敘述聲音都出自他之口,沒有他就不會有故事的呈現,“他是一個敘述行為的直接進行者,這個行為通過對一定敘述話語的操作與鋪展最終創造了一個敘事文體”[1];同時,他又作為故事中的一個人物,親自參與到故事進程當中。小說的主要角色有五個:大公、良秀、良秀之女、猴子、仆人。仆人重要程度顯然不如主角良秀,作為一個貴族宅邸中的下等人,其身份是無足輕重的,與大公家中的眾多其他仆人并沒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他同時擔任了敘事者這一角色,因而在小說中變得不可或缺,都參與到了故事當中甚至對故事進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很多小說家在創作時都有自己偏好使用的敘事人稱,迪福的代表作《魯濱遜漂流記》采用第一人稱敘事,列夫·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代表作則全部采用第三人稱,敘述者對于小說內容幾乎是全知的,當然第三人稱并不必然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卡夫卡的三部長篇小說也是采用第三人稱,這個第三人稱的視角所看到的事物卻是極為有限的,基本上只等于主角的個人視角,這是全知敘事與限知敘事的區別。過往的第三人稱敘事多采用全知視角這種模式,但當進入19世紀后期之后,在19世紀前中期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極為盛行的全知視角日漸式微,意識流、新小說等前衛的小說技術流派逐漸得到廣泛流傳,過去通常與全知視角相搭配的第三人稱小說也更多地采用限知視角了。芥川龍之介創作的小說中便有諸多使用第一人稱的作品,如《棄兒》、《孤獨地獄》、等,《竹林中》也可以看作是第一人稱敘事的作品,這部短篇佳作的重點在于通過不同人物的口吻進行講述,借助三個角色彼此不同的說辭,造成真相的混亂。第一人稱與第二、第三人稱相比,其特點一個是由于第一人稱敘述者大多都是同故事敘述者,會親自參與到故事進程,透過第一視角帶給讀者一種更加真實的感覺,如同讀者進到故事當中去親身經歷一般,與讀者距離更近;另一個是可以有效地展示主要人物的內心活動,進行心理剖析。當然也有像《棄兒》、《孤獨地獄》這類特殊的作品,其第一人稱敘述者也不是真正講故事的人,他只是在聽別人(松原勇之助、叔祖父)給他講故事,自己再為讀者轉述,因此這種敘述者并沒有參與故事,是異故事敘述者,所以通常也不會有利益相關,這類敘述者一般在敘述時雖然也不時發出個人的意見,不過通常僅限于客觀的轉述,然而《地獄變》的敘述者與此不同。
《地獄變》所采用的正是限知敘事的模式,小說選取崛川大公的家仆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可以很自然地與限知敘事結合起來,因為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所能知道的僅限于他自己的所見所聞,對故事情節的講述是相當受限的,并且仆人不像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中的說書人,要盡職盡責地講清故事的來龍去脈,畢竟說書人靠給聽眾講故事維生,需盡可能適應觀眾的需求,但是仆人既沒有這個責任,也沒這個能力,因為他“生性愚鈍”[2],對別人的事情知之甚少,這個敘述者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對一個或幾個虛構的聽眾(或稱為“敘述接受者”)講述自己對過去事件的見聞,這種講述具有明顯且強烈的個人立場,導致他的敘述傾向性相當嚴重。在一方面,敘述者對事件的了解很不夠,無法透露更多的內情,而另一方面,有選擇性地進行褒貶,對大公有意抬高,對良秀則刻意貶損,。由于敘述者對事件的感知能力有限及其本人的嚴重傾向性,造成了事件真相模糊難辨的狀況,因此作者特意選擇仆人作為敘述者,借助敘述者本身的特性來為小說鋪墊難言其妙的敘事基礎,再配以各種虛實難辨的神怪流言,如大公嚇退鬼魂、良秀夢見地獄等等,成功地給小說籠罩上了神秘莫測的氛圍,驅使讀者去進一步挖掘。從這些方面來看,第一人稱限知敘事是《地獄變》最合適的敘述模式。當然,敘述者的傾向性在小說中不是一以貫之的,它表現出來一定程度的矛盾、分裂,這又涉及到了不可靠敘述的問題。
二.仆人的不可靠敘述
上文已經明確了《地獄變》的敘述者使用的是限知視角,盡管仆人是站在事后的角度回憶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他并未把所有故事細節都一次性地拋給讀者,而是有所保留,在敘述的過程中逐步向讀者透露。作者(或稱之為“隱含作者”)在小說中建立了兩個敘述層次,“(《地獄變》的)敘事由兩種說明相輔相成,即分為明處與暗處兩種。”[3]“明的說明”即仆人站在自己立場所作的敘述,是文本的公開的明白的呈現,“暗的說明”則是潛在的敘述,即有別于敘述者的意圖和價值判斷的作者的真正想法,這表明敘述者的意圖與作者的意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于是造成了不可靠的敘述。
不可靠敘述是一種重要的敘事策略,這一敘事學概念由韋恩·布斯創立。布斯認為,敘述者在敘述中所作出的言行和價值判斷若與隱含作者不一致,那么這個敘述者就是不可靠敘述者,他作出的不與隱含作者意圖一致的敘述就是不可靠敘述。判斷
不可靠敘述者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傳統的修辭性研究方法,即布斯所建立的對比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兩者意圖的方法,另一種是認知(建構)方法,從讀者接受理論著手,聚焦于讀者的闡釋框架。由于這兩種方法互相之間具有排他性,因此一般只選用其中一種方法來對作品進行考察。修辭性研究方法更為傳統,它的衡量標準是作品的規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體、語氣、技巧等各種成分體現出來的作品的倫理、信念、情感、藝術等各方面的標準”,也就是隱含作者的規范。隱含作者的意圖是較難把握的,當他的意圖模棱兩可或者難以察覺時,分析者的判斷就可能出現問題,如同為芥川作品的《竹林中》,這部小說被認為是表現了作者的懷疑主義,多襄丸、真砂、武弘三人的說辭都能自圓其說但又互相矛盾,“在小說內部,并不存在另一個屬于事實真相的‘故事,三個當事人的敘述分別構成了三個獨立的故事”[4]。許多讀者都試圖從小說的種種細節入手希望解開這個謎團,但到頭來都會發現他們的解釋存在難以解決的紕漏,失去了隱含作者的意圖作為標準,盡管三個人物的敘述彼此相斥,也無法通過邏輯分析等方式得出確切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讀者的標準多種多樣,自然也無對錯之分,較難形成統一的認識,因而傳統的修辭性研究方法難以取代,本文依然主要憑借這一研究方法來考察《地獄變》敘述者的不可靠敘述。
敘述者作為敘述聲音的發出者,他是敘述中的話語主體,文本的敘事話語無論與隱含作者的意圖一不一致,都需要通過敘述者的敘述才能呈現出來。它以大公府中的家仆為敘述者,所敘之事僅限于家仆所了解的,正符合小說保留懸念的要求。選取這樣一個處于故事內的人物視角展開敘事,敘述者可以名正言順地體現他的個人立場,畢竟相較于其他模式的敘述者,他擁有具體的身份,可以隨意發出符合自己身份定位的話語,而不像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者被要求保持客觀和中立,所以不可靠敘述在第一人稱敘述中更常見。但在事實上,敘述者即便與隱含作者存在一定的矛盾,他在根本上還是隱含作者的代言人,受隱含作者支配,不會與隱含作者完全割裂,也就是說,敘述者在隱含作者的“操控”下,既要作出與作者意圖相符合的敘述,又要作出不相符合的敘述。
具體到小說內容,從仆人敘述中可知,他“侍奉大公已經二十年了”,或許是出于對大公優待的感恩戴德,或者是出于對權貴的崇拜,對大公充滿了崇敬之情,是個相當“護主”的老奴仆。他在故事開頭便把大公描寫得如若神明——不僅出生前有“大威德的神靈曾經在他的母親的枕邊顯靈”,而且具有“普天同樂的氣度”,連鬼魂也不敢近身相欺,更兼因“德高望重”受到京城百姓的敬奉,“京城的男女老少每每提及大公,無不肅然起敬,仿佛遇到神靈似的”,如此種種,似乎無懈可擊地給大公樹立了一個神明一般的貴族形象。反觀畫師良秀,仆人給予他的描述則截然相反,“從外表看,他是個身材矮小、瘦骨嶙峋、性格乖戾的老者。初來大公府的時候,他經常是一身丁香色的狩獵裝打扮,頭戴一頂軟烏帽,一副謙卑的模樣。然而不知怎的,他的嘴唇卻一片血紅,實在不像老頭兒該有的顏色,仿佛野人般難看”;不光外表怪誕不堪,性格也讓人難以接受,“他的怪癖就是小氣、冷酷、無恥、懶惰、貪婪。其中最要命的是專橫、狂妄,總以本朝第一畫師自居”,敘述者似乎是把自己能想到的貶義詞匯都用在良秀身上了。通過這種近乎詆毀的描述,一個丑陋的怪人形象在讀者腦海中基本得以定格。當然,通觀全文后讀者可以得知,仆人對這兩個人物作出的價值判斷,是與隱含作者的價值判斷有所出入甚至相對立的,隱含作者原本的意圖是揭露大公的惡行并表現良秀對繪畫藝術的癡狂的,因而家仆也就成了不可靠敘述者,他對大公和良秀的描述,存在著眾多與事實相悖之處。
這種“相悖”在《地獄變》中主要以兩種方式出現:仆人自己對大公的評價發生了改變,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小說后半段,最為典型的是仆人對火燒檳榔毛車時大公的離奇神態的描寫;除了用仆人自己的話對大公和良秀進行描述外,小說還添加了許多出自他人之口的“流言”、“閑言碎語”作為輔助,仆人在敘述時屢屢提起這些流言,彷佛聽眾不斷在向他提問,導致他不得不做出回應。仆人作為大公家的老仆,相比于外人更接近事實真相,對流言真假的判斷似乎是比較可靠、有權威性的,然而他對神化大公的傳聞未置可否,對貶低大公的流言則大部分都是否定的,如“人們說長道短,說大公的性格比得上秦始皇、隋煬帝,可那不過是‘瞎子摸象的片面之詞罷了”,在仆人看來大公是愛護百姓、天下為公的;在論及良秀之女時,更是反復出現了多處關于大公好色的傳聞,“大公對良秀之女偏愛有加,完全處于贊賞她愛護猴兒、孝敬父母的心靈,并非世上傳說的好色”;“有人開始散布謠言,說大公喜歡上了良秀之女;還有人道聽途說地謠傳,《地獄變》屏風的創作正是源于良秀之女不愿順從大公。其實,這些事都是子虛烏有……大公對這女孩子本是一片好意,貪戀美色之類的說法恐怕有些牽強附會,實在是毫無根據的謠言”。仆人多次提到了對大公不利的流言,雖然這可能是由于他的聽眾正在傾聽家仆的講述,而且很可能是在聽這個故事之前就曾聽說過有關大公的傳聞了,因此敘述者才一再向他的聽眾解釋,試圖消除他們對大公的負面看法,但這對于現實的讀者來說則更像是一種暗示,反復提到關于大公的流言至少從側面說明了其聲譽是有問題的,絕非如仆人所說的被男女老少“敬若神明”,那么敘述者便顯露出了其不可靠性。當讀者經仔細品讀后看穿了大公的真實面目時,就會明白過來敘述者是刻意對大公進行了美飾,所謂的“謠言”反而是更接近真相的事實。至于良秀的流言,仆人提到的大多是負面的,不僅基本沒有否定過流言還有可能在流言的基礎上添油加醋,進一步丑化了良秀,如仆人認為良秀滿身缺點,對他的評價是相當低的,明顯帶有嫌惡的心態,讀者從敘述者話語中能為良秀找出的亮點可能就只有對女兒的愛以及對繪畫的癡了。
仆人雖然在前半部分對大公的直接評價上進行了美飾,但在后面的幾次事件中,對大公丑惡的掩蓋力度有所減弱,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如實描述,如良秀向大公提出歸還他女兒時,“一向寬宏大量的大公聞聽此言,不由得臉色一變,一聲不吭地低頭端詳良秀的臉,半晌過后才道:‘不可以說罷,就起身離開了”,這與他先前說到的“‘普天同樂的氣度”、“寬宏大量”顯然不相符,只是在這里敘述者還站在大公的立場,有意把重點置于對良秀的膽大妄為的批判上,并且這一細節也體現出大公對良秀之女的看重絕不只是“一片好意”。又如在燒檳榔毛車時,“大公卻緊咬嘴唇,偶爾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目不轉睛地望著車子的方向”,在這些描述里敘述者幾乎就如攝像機拍攝一般對眼前的人、事不加干預地如實“展示”,不再附加帶有立場的修飾,更為接近客觀真相。
小說中有一處不可靠敘述與上文提到的都有所不同,敘述者不是作出了與隱含作者不相同的價值判斷,而是在言行上沒能和隱含作者保持一致——當家仆在某天夜里被猴子引導至一間屋子處時,意外撞見良秀之女受到侵犯。良秀之女趁此機會逃脫,家仆“聽到另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腳步聲”,他起初還試圖尋找,又問良秀之女那人是誰,良秀之女并沒有直接回答,仆人也推托自己“向來愚笨,只了解自己知道的事,其他的事一概糊里糊涂。我也不懂得換個問話方式”。如此便把這一嚴重事件給敷衍過去了。若從以上分析的不可靠敘述角度來看,仆人很可能是選擇用“裝糊涂”的手段來“糊弄”讀者——他在當時或許已經預感到“見到了不該見到的事”會對自己不利,更有甚者,他可能已經猜測出那個企圖強奸良秀之女的人就是大公,但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以及仆人維護大公的一貫傾向而不進一步追問。假若家仆事先知道是大公在那間屋子里做這種事情的話,他極可能不聞不問直接繞路而走了,根本不會去靠近那個屋子,更不用說撞破這件事。
仆人本身并沒有揭露大公的想法,他之所以能在敘述中做到這一點,是受到了作者的“干預”,敘述者與作者之間存在著矛盾對立,這種對立不僅體現在對大公的褒貶上,也體現在對主角良秀的態度上。敘述者作為大公家的老仆,以偏向性極強的敘述對良秀進行污蔑、丑化,隱含作者對此并沒有作出明顯的干預,似乎他也同意良秀確實是一個缺點眾多、難相處的人,但他同時對良秀的藝術精神表現出贊賞之情。良秀對女兒的愛與對藝術的愛原本彼此相容,但在大公的迫害之下,愛女兒與愛藝術成為不可并存的對立項,體現了追求倫常之愛和追求藝術之真的矛盾,這兩種追求的分裂最終導致了良秀的自我毀滅。可以說,小說既在形式上表現了分裂,也在其主旨上表現了分裂。
三.《地獄變》敘事策略的突出意義
仆人歪曲、隱藏事實,顯然是與隱含作者意圖不相一致的舉動——隱含作者要展現事實,揭露大公的丑惡真面目,而敘述者卻用各種手段美化大公形象,掩飾其罪行。從這一點來看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立場是截然對立的,但他們之間必然還存在著“共謀”的基點,那就是講述這個故事,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兩者缺少任意一個則這一文本都不復存在。為了不讓仆人的話語偏離自己的意圖,隱含作者勢必要對其進行干預,糾正已偏離的方向。當然,隱含作者的干預力度必須是適當的,不能夠“喧賓奪主”,破壞了敘述者的敘述。仆人歪曲、隱藏真相,對于小說結構而言有其必要性。這種“闡釋的空缺”同樣是一種常見的敘事策略,相當于給讀者挖了一個“坑”,在后面的進程中再把“坑”填上,“一個‘闡釋空缺最終在文本中得到了填補”[5]。適當地制造“延宕”能有效地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如果過早地把大公的真實面目徹底揭露出來,讀者有了心理準備,會導致小說高潮部分也就是燒檳榔毛車時,不需要等車簾子撩起也早已能根據前文推斷出車里的女子就是良秀之女了,如此便降低了小說的閱讀難度,故事的懸念被削弱,使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丟失了令人驚駭的效果。如此一來小說高潮的威力就被大大削弱了,讀者也失去了突如其來的心理沖擊感。
敘述的不可靠經常會產生反諷的效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覺出了敘述者的敘述不可靠時,就可以接收到這一意味,讀者會跨越敘述者,在敘述者背后與隱含作者進行隱秘交流,達成一定的共識,據此發現敘述者話語中的缺陷,而讀者的發現會為讀者帶來閱讀的快感。在《地獄變》里,大公的真實面目直到最后才得以徹底揭露,閱讀前文時讀者雖然對大公的形象和敘述者的話語心存疑慮,但不能確定,不知作者葫蘆里賣的什么藥,而在檳榔毛車的簾子撩開的那一刻,讀者既為良秀之女要被活活燒死而驚駭不已,同時也看到敘述者之前苦心維持的如若神明的大公形象驟然崩塌。當讀者發覺到這一點后,再回顧前文中仆人關于大公的那些可疑的敘述,就能感到獨特的反諷意味:崛川大公露出了他那好色、兇殘、專橫的真面目后,家仆之前為他說的好話此時非但不再起到任何掩飾作用,反而轉變為對大公的尖刻諷刺,雖然敘述者的本意可能并不如此。而之前為敘述者所否定的“流言”、“片面之詞”,反而彰顯出它們的客觀性,倒是敘述者本身被打上了“片面”的烙印。此外,《地獄變》的敘述策略在客觀上產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小說選擇仆人作為敘述者,打破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傳統敘事套路,不再讓讀者早早地知曉大部分內容信息,而是利用敘述者不可靠的敘述制造閱讀的“障礙”,延長了讀者的閱讀時間,讓讀者更多地感受閱讀過程中的審美體驗。
結構主義敘事學雖然在文學外部研究方面有不可否認的缺陷,過分忽視了文學作品的作家思想、社會文化背景等外部環境,但也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察視角和研究思路,充分挖掘了文本內部的信息。就《地獄變》而言,通過敘事學的深入分析,可以見出芥川有意地通過選取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憑借其天然的有限視野完成對部分故事內容的不可靠敘述敘述,成功地制造了故事懸念,深化了小說內在精神價值,帶給讀者更加強烈的心靈震撼和更深邃的藝術體驗。
參考文獻
[1]徐岱.小說敘事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108.
[2][日]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精選[M].朱園園譯,北京:群眾出版社,2015(1):79.本文所引小說原著內容均出自此書,在此不再一一標注頁碼.
[3][日]中村友.近代作家書簡拾遺十七芥川龍之介(小島政二郎宛),轉引自李東軍.隱喻與悖論:小說《地獄變》“藝術至上”主題的敘事學分析: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研究——大學日語教育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269.
[4]陳葉斐.芥川龍之介小說《竹林中》的敘述學研究[J].日本研究,2003,4:59.
[5]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25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方美學的當代化與國際化會通研究》(項目編號:18XWW003)。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