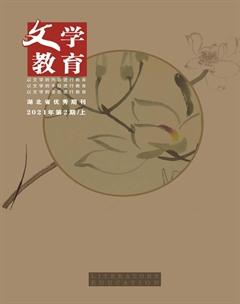試論《項脊軒志》的抒情藝術
尹玉燁
內容摘要:作為千古悼亡之血淚之作,《項脊軒志》的抒情藝術頗具特色,文章從它的移情就景,生活細節點染,以樂襯悲,以物寄情來賞析其一唱三嘆悲惻動人的抒情效果。
關鍵詞:歸有光 《項脊軒志》 抒情特色
古今悼亡之作,不乏膾炙人口之極品。詩有唐·元稹.《遣悲懷》,詞有宋.·蘇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而散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則令人百讀不厭。這些悼亡之作都以其濃郁的悲劇色彩,撼動人心。尼采說:“一切文學吾喜以血書成者。”①《項脊軒志》就是這樣一篇血淚之作,全文借一閣項脊軒抒寫家世中與自己至親的三代女性,紛紛棄世而去的痛傷,以悲情綰結全文,全篇不著一個哀字,卻處處哀情,讀來有潸然淚下之感。正如明人王錫爵曾評歸有光:“所為書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②這種無意感人,卻催人淚下的藝術效果,恐怕要得益于作者大巧若拙的藝術表現技巧。
一.移情就景,張本揚厲
百年老屋,歷經幾代興廢,其破舊可想而知。開篇寫小屋狹小,繼而寫其歷經風雨、千瘡百孔,“塵泥滲漉,雨澤下注”達到無可置案的地步,撲面給人以滄桑、破敗之感。這樣為下文寫家道中路、家庭分崩離析埋下伏筆。“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雞棲于庭。”這種雜亂是家庭敗落的外在表現,然而對于一個在這種變遷中成長起來的敏慧的少年而言,是揮之不去的凄涼。因而第一段文字總體以寫景為主,而景物的主色調是暗淡凄涼的。即使有像始室豁然、蘭竹添彩的亮點也是一閃而過。
寫他沉浸在書香之中,或長嘯或低吟,怡然自樂。這種生活雖然快樂富足,但這位九歲能文,自信絕非“坎井之蛙”的少年,心靈也是極其孤獨的,“昧昧于一隅。按照心即景,景即心的原則,首段寫景實際上給我們展現這個少年心靈極孤獨而凄涼的一面,是作者心靈的真實返照。極靜的,極輕的,籠罩著一層淡淡的哀愁。“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作者采用詩文慣常的以有聲襯無聲,以動顯靜的手法,輕盈的小鳥時來啄食,反襯出小院的至幽至靜,接著寫淡雅、清幽的月色:如流水穿窗而入靜瀉在半墻,桂影清晰如畫,涼風襲來,樹影搖曳,令人心醉。因此靜謐、凄清的月光,雖說“珊珊可愛”,但極幽靜凄清的色彩,清晰映射出作者內心深處濃郁的凄涼和孤獨。
小院及月色的幽謐,也暗寓訪客稀少,這位天資不凡、九歲能文的少年,除了閉門苦讀外,沒有滿座的高朋,借以侃侃抒懷,精神生活是富足的,也是單調壓抑的。可以用祖母的活來印證:“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生活孤寂可窺一斑。
開篇寫景為全文抒寫哀情,張本揚厲,營造了悲情氛圍。如果我們把全文對三代往事的追憶看作是華彥均《二泉映月》的音符,那么哀情則是這首樂曲的主旋律,素淡,凄清的月色,如一首哀婉動人二胡曲的開端,將讀者緩緩帶入往昔憂傷,低沉的回憶之中。
二.敘事現情,細節點染
敘事緊扣悲字,反復詠嘆,先寫家庭變遷、母親早逝、祖母離世。層層推進,紆徐有致,撼動讀者。敘事寫人都用個性化的口語,動作的細節描寫,栩栩如生展現了兩位女性的音容。
作者在《先妣事略》中寫到八歲母喪的情形,一家都哭成一片,而處在懵懂中的作者也不知道為什么,于是也跟著哭,對先妣的回憶,雖借乳母之口,但卻令人心碎。“某所,而母立于茲。”可以想象,乳母一邊指著先母站過的地方,一邊引領作者進入往昔的回憶,彼時彼景,歷歷在目。“兒寒乎,欲食乎?”慈母輕叩門扉,問寒問暖的柔聲細語仿佛歷歷在耳。沉浸在回憶中,久違的親切溫馨慰藉著孤獨的心靈,然而短短的溫馨過后,便是悵然若失,只能倍增傷世之感。“嫗泣,余亦泣,”乳母和我都泣不成聲卻勝有聲,幼年喪母的錐心之痛,深沉的思母之情。這次第怎一個“泣”字了得。
回憶祖母,則是直接回憶,因為祖母過世較晚,但采用手法一致,在表現人物,傳情達意上有異事同工之妙。寫祖母來軒中探望:“吾兒久不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語氣雖然帶責備,但對其小小年紀能閉門苦讀的行為不無欣喜、嘉許。由此推斷,他日必能光耀門楣,于是很自然帶出祖母持笏勉孫:“他日汝當用之,”其言語,望孫成龍的期許溢于言表。而“比去,以手闔門”的動作,使一位舉止矜持愛而不溺的封建長輩形象呼之欲出。“令人長號不自禁。”憶往昔祖母之期許,思今日仕途之失意,有負于親人厚望的愧疚,前途未卜的憂慮交織一起,怎么不化作淚水奔涌而出呢。
個性化的語言,恰如其分表現人物身份神情,簡潔的動作描寫出人物性格,兩者相得益彰,表現人物形神畢肖。平常語平常舉,卻點染了一副凄惻動人的畫面,正有人有所評價的:“辭淺而韻遠,”、“事細而情深。”
這段文字雖采用細節描寫,但用筆十分簡省,敘事寥寥數語,便戛然而止。如回憶先母,只用乳母模仿的一句口語:“兒寒乎,欲食乎。”“以指叩門”的動作,便刻畫出一個溫柔嫻淑、舉止節制的封建良母的形象。只一“言”一“行”便充分展現其慈愛,收到以少勝多,以簡馭繁的效果。抒懷僅用“泣”“長號”點到為止。達到不言哀卻哀無限的境界。
三.凸現樂事,避重就輕
補記部分屬十幾年后所作,但感情與正文部分一脈相承,結構上渾然一體。只是表現方式更為含蓄蘊籍。如果說對母親、祖母的回憶是工筆細繪,那么對亡妻的追憶,當屬疏淡的白描,只是用極簡約的筆淡淡帶出。大約是“曾經蒼海難為水”的緣故,不敢回首往事,暮然回首只會帶來刺心的痛。
對于一個屢屢受挫失意中度過的年輕人來說,幸福、短暫的婚姻帶給他的是超乎常人的歡樂。“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問古學書,夫唱婦隨,志趣相投。讀書之樂,兼有知音相伴,其樂無窮。作者在《請敕命事略》中寫道:“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泊,親自操作……”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善解人意的妻子給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以最有力的勉勵和支持,妻轉述眾姊妹的話更令人浮想聯翩,“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由此推想,妻歸寧常向妹妹提起項脊軒和他的主人,很以處在潦倒中的丈夫為榮。深信刻苦攻讀的丈夫終非“坎井之蛙”。伉儷情深,心心相印可窺一斑。然而唯其情深,才失之痛苦不堪。作者運用樂事襯哀情的手法,悲由喜生,喜愈增悲,令人悲不自勝。
作者中年喪妻,沒有“泣”,也無“長號”。語調是極淡的,可謂“輕描淡寫”:“吾妻死,室壞不修”看似兩件無因果關系,但卻有緊密的情感聯系,正因為痛失愛妻,才人亡室棄,心灰意冷,事事了無生趣。正應了李清照一句詞:“物是人非事事休”深深的悲慟和沉重盡在不言中,接下來,敘事的語調更淡了,看似寫閣子,實際上暗示內心無法言表的悲哀,歷經滄桑,仕途屢屢受挫,欲說不休,不說也罷了。修葺后“稍異于前”是不敢恢復原貌。“不常居”是不愿居,怕的是睹物傷懷。
四.物盛人亡,人何以堪
最后一段寄情于物,物人之間形成鮮明的比照,盡管是“生死兩茫茫”但“不思量,自難忘。”最后一段寫對亡妻的思念,著眼于物,言在此而意在彼。由物徐徐帶出人,然后又收及物。枇杷樹,正因為愛妻手植,睹物如見人,妻死之年暗示恩愛呢喃的往事歷久 彌新。今已如蓋,點出時間在推移,物已亭亭而“人在何處”,“縱使相逢應不識”,歷經磨難,恐怕已是“塵滿面,鬢如霜了”。此處暗用《世說新語·言語》中的典故:“恒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折枝條,泫然流淚”。作者化用典故,又有所取舍,由物及人,宛若天成,點到即止,含蓄蘊藉,將哀情推到極致。就在作者優柔不迫的言語中,我們仿佛看到年年歲歲隨著枇杷樹的生長,作者對亡妻的思念,歲歲年年,與日俱增,內心深沉的悲涼和滄桑也如樹根,不斷隱入地層深處,不再浮于文字表面。
參考文獻
①王國維《人間詞話》
②明·王錫爵《歸有光墓志銘》
(作者單位:甘肅省瓜州縣瓜州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