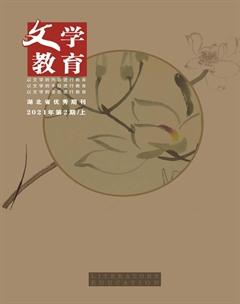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譯文新解
林雅婷
內(nèi)容摘要:歷來學(xué)者對(duì)于“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句話的注解存在頗多爭(zhēng)議,至今無統(tǒng)一的定論。甚至許多現(xiàn)代學(xué)者站在新奇的角度不斷研究,提出新的譯法。本文在總結(jié)目前幾種討論較多的觀點(diǎn)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分析,并闡述自己的結(jié)論。
關(guān)鍵詞:孔子 論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一.引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注解之所以存在較大的差異,首要原因在于句讀問題。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句話不應(yīng)句讀,但多數(shù)學(xué)者持反對(duì)意見,并且提出了不同的句讀形式。大致分為以下四種:1.子罕言利與命,與仁;2.子罕言利,與命與仁;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4.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通過對(duì)比以上幾種句讀方式及學(xué)者提供的不同版本的譯文可發(fā)現(xiàn),眾多學(xué)者討論的焦點(diǎn)在于孔子提起利、命、仁的次數(shù)以及對(duì)這三者的態(tài)度,還有兩個(gè)“與”字的含義及語法,因此本文認(rèn)為這幾個(gè)方面值得深入探討。
二.命和仁的歧義
許多前人在論述時(shí)都會(huì)以利、命、仁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多或少為他們的論據(jù),甚至有學(xué)者統(tǒng)計(jì)出其他傳世典籍中孔子言論關(guān)于這三字的用詞情況。學(xué)者們對(duì)“利”的態(tài)度爭(zhēng)議不大,這里不做贅述。
仁字存在較大爭(zhēng)議,大致分為兩種觀點(diǎn)。一種認(rèn)為“仁”雖在《論語》中出現(xiàn)一百多次,但也為孔子少言的對(duì)象。例如何晏、刑昺認(rèn)為“寡能及之,故希言。”[1]楊伯峻則詳細(xì)解釋了孔子“罕言仁”的原因:“《論語》中講仁雖多,但一方面多半是和別人問答之詞;另一方面,仁又是孔門的最高道德標(biāo)準(zhǔn),正因?yàn)樯僬劊鬃优家惶岬剑阌杏涊d。不能以記載的多便推論孔子談的也多。”[2]
有學(xué)者反駁楊伯峻先生,認(rèn)為其觀點(diǎn)太過牽強(qiáng)附會(huì)。如周遠(yuǎn)斌在《論語校釋辯證》中提出:“楊伯峻的解釋,也過于拘泥于言之多少了。這一章,其實(shí)并不重在孔子言及者多少,而重在指出孔子思想上的傾向性。”[3]本文認(rèn)為楊伯峻先生的說法是矛盾的,如果不是孔子多言仁,后人又如何能從中總結(jié)出仁是孔子所提倡的核心思想?因此不論是從仁出現(xiàn)的次數(shù)還是孔子對(duì)仁的態(tài)度進(jìn)行討論,孔子是多言“仁”的。
歷來爭(zhēng)議最大的是“命”。從數(shù)量上看,孔子提及“命”的數(shù)量比仁少,比利多,無法通過數(shù)量判斷。從態(tài)度上來說,學(xué)者也有異議。何晏、朱熹等學(xué)者支持孔子“罕言命”的說法。南懷瑾作出具體解釋:“這里的命是廣義的,包涵生命來源的意義而言。孔子在教育方面,知道哲學(xué)上生命來源的道理很難講得清楚,所以很少講。”[4]
另一種觀點(diǎn)是根據(jù)孔子所說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認(rèn)為他敬畏且稱贊天命。錢穆支持此種看法,他指出:“孔子所贊與者,命與仁。”[5]還有學(xué)者提出與前兩種不同的觀點(diǎn),如姚小鷗、呂廟軍認(rèn)為孔子只是在感嘆天命,無奈地將失敗原因歸于天命,并不是稱贊。
本文認(rèn)為《論語》中的具體言論無法明顯界定孔子對(duì)“命”持贊許態(tài)度。處于古代社會(huì)的孔子對(duì)于命無法明確了解,因此持敬畏的態(tài)度,想表達(dá)敬畏之心,言論中也會(huì)涉及到“命”。加之常佩雨、金小娟兩位學(xué)者所做的研究可以證明孔子多言“命”:“近期出土的文獻(xiàn)如‘上博簡(jiǎn)14余篇的孔子言論中,命、天合在一起高達(dá)29次,這一數(shù)據(jù)表明了命確實(shí)是孔子經(jīng)常討論的哲學(xué)范疇。”[6]所以本文認(rèn)同孔子多言“命”的觀點(diǎn)。
三.“與”的歧義
(一)與的詞性
在古代,與字的具體含義及用法已有多種,且“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存在兩個(gè)與字,因此與的具體理解也存在頗多爭(zhēng)議。按詞性分類可以將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分為以下六種:
(1)與作連詞,表并列關(guān)系,譯為“和”。何晏、朱熹等都將“與”做此理解。
(2)與作動(dòng)詞,譯為贊許。梁代皇侃注:“與者,言語許與之也。”[7]
(3)與作動(dòng)詞,為“舉”的假借字,譯為稱引。周干濚先生提出:“舉,《說文》以為‘對(duì)舉也,段玉裁注:‘謂以兩手舉之,亦即推高,可引申為稱引。”[8]
(4)與作動(dòng)詞,譯為順從。元人陳天祥在《四書辨疑》中提出:“與,從也,蓋言夫子罕曾言利,從命從仁而已。”[9]
(5)與作語氣詞,同“歟”,常用于句末,表提頓,不譯。例如王丹丹在文章中表示“后一個(gè)‘與字訓(xùn)為語氣詞‘歟。”
(6)與作介詞,譯為“跟”。傅允生認(rèn)為:“與作為介詞,其作用在于引出有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的雙方。”[10]
詞的翻譯最終要回歸文本,因此本文結(jié)合古漢語的語法及“以經(jīng)證經(jīng)”的方法進(jìn)行分析。在《論語》中,共84章出現(xiàn)“與”字,詞性多為連詞、動(dòng)詞和語氣詞。在古漢語中,如果是三個(gè)以上的并列性詞語作賓語,通常省略連詞直接句讀。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提出,如果按照古漢語的語法規(guī)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形式應(yīng)為“子罕言:利、命、仁。”而將兩個(gè)“與”作連詞,譯為“和”并不準(zhǔn)確,且不符合前文孔子對(duì)利、命、仁的態(tài)度的結(jié)論。此句中的“與”在名詞之前,作語氣詞翻譯也不符合語法。而84章中有33處是同一章中出現(xiàn)了兩個(gè)以上的“與”。不難發(fā)現(xiàn),如果“與”作為不同詞性翻譯,大多是句式不對(duì)稱,如“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如果作同一詞性翻譯的,一般都為對(duì)稱句式,如“可與共學(xué),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quán)。”加之孔箏提出:“《論語》中,把一個(gè)動(dòng)詞性的詞直接帶上一個(gè)名詞的現(xiàn)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且在構(gòu)成句子的時(shí)候有故意的強(qiáng)調(diào)而不避開用同一個(gè)動(dòng)詞的情況。”[11]例如“子絕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因此本文認(rèn)為“與命”、“與仁”是對(duì)稱形式,兩個(gè)“與”字為同一個(gè)含義且都作動(dòng)詞的觀點(diǎn)更符合語法規(guī)則和《論語》記錄的習(xí)慣用法。
(二)與的含義
“與”作動(dòng)詞在《論語》中多譯為參與、給予和贊許這幾個(gè)意思。本文前面已經(jīng)總結(jié)了孔子對(duì)命的態(tài)度只是敬畏,即孔子對(duì)命的態(tài)度沒有確切的評(píng)價(jià),因此將“與”翻譯為“贊許”和“順從”都不合適。雖然在《論語》中出現(xiàn)的“與”無通“舉”的用法,但有學(xué)者發(fā)現(xiàn)“與”、“舉”通假現(xiàn)象在其他出土文獻(xiàn)中是多見的,例如“白于藍(lán)先生提出:與舉:《五行》:君子知而與(舉)之。”[12]
多數(shù)學(xué)者未從邏輯這一角度進(jìn)行論述,因此本文結(jié)合這一角度對(duì)“與譯為稱引”這一觀點(diǎn)作進(jìn)一步論證。古人在說話與習(xí)作時(shí)都會(huì)講究邏輯性,前后內(nèi)容相關(guān)甚至對(duì)稱,《論語》的記錄形式也多以對(duì)稱為主。蔣方在其文章中提出:“論語基本上是一事一錄,每條語錄的意義自足完整。如果將此句斷成兩截,按照體例,就可以分為兩條記錄,那么‘子罕言利可以成立,‘與命與仁卻不能成立,因?yàn)槿珪鴽]有缺少主語的記事。”[13]這樣看來,若將“子罕言利”和“與命與仁”進(jìn)行句讀,前后兩句的意義各自不完整,就必定得有關(guān)聯(lián)性和邏輯性,那么將“子罕言利”譯為“孔子很少談及利”,“與仁與命”譯為“贊許(順從)命,贊許(順從)仁”,前面是說明談?wù)摰亩嗌伲竺鎱s在說態(tài)度,就顯得前言不搭后語了。因此,本文認(rèn)為在前人的觀點(diǎn)中,“與”譯為稱引更合適,“稱引”有引用、稱述的含義,具有“言”的意義,用更加直觀的詞語可解釋為“談及”,能和“罕言”形成對(duì)稱,更符合語言的邏輯性。
四.總結(jié)
綜上,根據(jù)利、命、仁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和孔子對(duì)這三者的態(tài)度,以及語法、邏輯這幾個(gè)方面對(duì)“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具體含義進(jìn)行推導(dǎo),本文得出的結(jié)論是:句讀形式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譯文:孔子言語中少談及利,多談及命,談及仁。
參考文獻(xiàn)
[1]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下冊(c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南懷瑾.論語別裁[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
[3]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4]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6
[5]周遠(yuǎn)斌.論語校釋辯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7]常佩雨,金小娟.出土文獻(xiàn)孔子言論參照下的《論語》新解——以《子罕》首章為例[J].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33(04):33-40.
[8]傅允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辨析[J].孔子研究,2000(04):123-125.
[9]蔣方.也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國(guó)學(xué)網(wǎng)http://www.guoxue.com/p=13836)
[10]孔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釋正[J].成都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教育科學(xué)版),2008(04):103-105.
[11]呂廟軍.“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新釋[J].邯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02):88-90+93.
[12]王丹丹.“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新解[J].佳木斯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30(06):106-107.
注 釋
[1]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M].下冊(c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742。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6。
[3]周遠(yuǎn)斌.論語校釋辯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63-164。
[4]南懷瑾.論語別裁[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頁366。
[5]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206。
[6]常佩雨,金小娟.出土文獻(xiàn)孔子言論參照下的《論語》新解——以《子罕》首章為例[J].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33(04),頁38。
[7]同上注,頁742。
[8]常佩雨,金小娟.出土文獻(xiàn)孔子言論參照下的《論語》新解——以《子罕》首章為例[J].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33(04),頁35。
[9]同上注。
[10]傅允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辨析[J].孔子研究,2000(04),頁123。
[11]孔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釋正[J].成都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教育科學(xué)版),2008(04),頁103。
[12]常佩雨,金小娟.出土文獻(xiàn)孔子言論參照下的《論語》新解——以《子罕》首章為例[J].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3,33(04),頁38。
[13]蔣方.也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國(guó)學(xué)網(wǎng)http://www.guoxue.com/p=13836)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