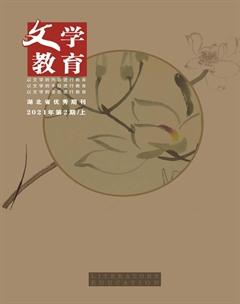論魏晉六朝文學的“絕處逢生”
陳鴻遠
內容摘要:《文選》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選集著作,“選學”作為影響歷朝歷代的顯學,在近些年來已逐漸重拾其應得的關注,但依然缺少精深而細致的探索與研析。正如黃侃在《文選平點》卷末中所題:“八代名篇此盡儲,正如乳酪取醍醐。”[1]被收入《文選》中的作品具有醍醐般的深厚價值,值得細細品味。若探討這些醍醐之作是因何制成,筆者以“絕處逢生”作答,意即指出,《文選》中的作品正如乳酪取醍醐那樣,經歷熾焰煅燒方能降生于世。但畢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2](32),原著所集浩如煙海,猶能體現“絕處逢生”的,還屬魏晉六朝文學。
關鍵詞:《文選》 魏晉六朝 絕處逢生
魏晉六朝時期,戰亂不斷、疫病橫行、社會動蕩、幾乎人人自危。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時刻,卻先后誕生了曹孟德、阮嗣宗、謝靈運等名家;傳誦出建安風骨、魏晉風流等文史佳話。魯迅稱這一時期是“文學自覺”之時代,李澤厚稱其為“人的覺醒”時代,宗白華評述其為“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3](142)。總結下來,毋庸置疑的是,這段歷史于后人而言,是文學佳作層出疊見的美好傳奇;于當時的文人墨客而言,卻是既解放又痛苦的絕境。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憂憤出詩人,文學作品亦得以“絕處逢生”。本文以時間為軸線,兼采魏晉六朝數位代表作家們的部分作品,來闡釋上述“絕處逢生”之主題。
魏晉六朝時期,天災與人禍雙雙降臨,其時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甚至命喪其中;目睹這般慘狀的有識之士有感而發,執筆著文。而這些文人或仍積極入仕,或選擇遠離廟堂。前者夾雜在強權與門閥制度的復雜交替中為其所累,后者則雖看似瀟灑恣意、自由暢快,內心卻同樣不無痛苦。受內外刀槍的無情撻伐,作家們或是萬念俱灰,耽溺于對極樂世界的幻想無法自拔;或是極力保有清醒的自持,沉痛著將所見所思都書寫成章;抑或放任心緒,縱情高歌,試圖以此紓解苦悶;又或者經歷曲折嘗試后愈發無措無求,只愿以尚有的筆墨才能,寄身于遠離塵囂的自然萬物之中,聊以慰藉。這幾種生存狀態之中,后三者所創佳作精品尤為經典。正是在這樣的痛苦絕境中,文章篇制應運而生,讓千百年之后的我們得以一聆“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4](57)的現實絕唱。
一.感于戰亂,憂時濟民
在漢末的歷史卷軸上,曹操不僅是一位掀卷時代風云的權謀奸雄,還是一名忠誠地直述史實的文學家。在其一生當中并不算多的詩文遺珠里,反映滾滾硝煙之下生離死別的將士百姓、明里暗里作奸作惡的當權者等人物的詩篇尤為突出。試看其數篇代表作中的幾句——《薤露行》里的“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5],《蒿里行》里的“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6],這不正是孟德身兼政治家宏大視野與文學家記錄之思的表現嗎?再聚焦《蒿里行》這首詩,“鎧甲生蟣虱”[7]將將士的困苦直陳其上,“萬姓以死亡”[8]便將這份沉重的嘆息灌之以更廣闊的社會,“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9]則是對蕭瑟現實的環境復刻,方方面面的感觸集結為一,最終化成“念之斷人腸”[10]之悲涼慨嘆。可以看到,曹操的挽歌絕非單單記錄自己的情思,他那軍事家與政治家的宏闊心胸不屑于小家子氣的欷歔碎語;也并不滿足于記錄一人一地,他的詩文是“漢末實錄,真詩史也”[11]的,一人一事、一花一草不叫歷史,群像紛涌、斗轉星移才得以作數。這樣的結果當然有個人性格所致,但放眼其所處的環境,不難發現,若不是風云馳逐的動蕩社會勾起了他的揮毫熱情、悲苦蒼涼的慘淡人世引發了他的慷慨本色,那豈會有如《苦寒行》般紀事、《對酒》般述志等名篇得以在絕處中逢生呢?
而在風云變幻的漢末,因感于短戈兵戎之亂象而援筆的典型當中,還有王粲及其《七哀詩》。試舉其一為例,“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12]可以看到,同樣是出于對戰爭現實的感懷,王粲的筆觸較之曹操,退卻了政治家的博大雄壯之感,而多了一份從微處著筆的細膩。作者善于通過人事物的微小典型來反映普遍的社會現實。路邊的饑婦無奈拋棄自己尚處襁褓間的孩子,這不是廣闊的群像,卻更能引人涕下,仿佛看見了烽火連天的土地之上,到處是生離死別之痛;聽見了哀泣聲此起彼伏,觸碰到了身死之人再也回不來、幸存者不知何去何從的悲哀。就像王粲在詩中坦然直言,“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13]最后,詩人還由此及彼,想象那泉下之人,如若看到在世親人竟是如此存活,想必也“喟然傷心肝”[14]了。總結而言,這系列詩作實在是集詩人之痛苦、他人之痛苦、社會之痛苦于一身的“痛苦”之作,是“絕處逢生”的又一“幸運兒”。
二.感于命運,因寄真情
在建安文人集團當中,曹植是最為重要的中心之一。相比其征戰四方的父親,曹植可謂既承父志又拓新風。這與他的人生前后分期是息息相關的。前期,即其13歲之前,隨父而過的動蕩軍旅生活,見證到的群雄并逐之盛況,無不使其漸生滿腔政治熱情與壯志雄心,這使得他當時的詩風樂觀開朗,昂揚豪邁,同時也為其日后歷久不衰的對政治功名的熱情打下基礎;之后,在短期的游宴詩賦生活之后,曹植逐漸落入人生的牢籠中,生活上被曹丕嚴格監視、物質上愈發困苦、精神狀態高度壓抑。這前后的精神與物質的雙落差塑造了更加為后人所熟知的曹植。他的政治理想已不可得,于是訴諸詩端成了唯一的抒懷方式。《贈白馬王彪》便是這樣一首集大成之作。面對本就廣且深的江河,卻發現自己無橋可走;改走平常土路,大雨又要來阻擋行徑的步伐;無奈換成登高山,卻又人疲馬病——“伊洛”“霖雨”、“東路”“高崗”[15],前者象征人生里無窮無盡的困境,后者寓示被不斷阻隔的希望之路。隨后,子建又通過用典,如引父親詩句作“去若朝露晞”[16]、借物自況,如借“歸鳥”與“孤獸”[17]二者,既表對比,又以此表意,等方式,來寄托自己濃郁的哀思。可見,不同于其父,曹植的詩文更多是感于個人命運,因苦痛寄真情。
進入正始時期,社會思潮與文學創作都有了極大的變化。隨著道家思想與玄佛思想逐漸深入,深感官場敗壞、政治黑暗的士人們逐漸疏離、乃至否定儒教禮法等“身外之物”。阮籍、嵇康便是其中的部分代表人物。他們展示出了重抒情,更重哲思的新傾向,也就是玄遠情趣的審美追求。究其根源,即如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所言:“社會生活中提出的種種需要解決的問題,必須作出理論的回答”[18]。換言之,阮籍、嵇康等人不再滿足于單純的情感宣泄,而是渴望從思想的玄妙中擷取有助于表達情感者,為己所用,注于詩文之中。如阮嗣宗在《詠懷》組詩中所記,半夜時分“不能寐”,于是借琴聲以解悶。但坐處琴鳴之中,聆聽四周生靈的聲響,卻終得“憂思獨傷心”;只身坐在“空堂”,極目所及皆是觸人傷懷之景物,“我”就像那“孤鳥”“離獸”一樣,即使思念親友,卻也只能獨自嘆息[19]。這樣的“格式”在阮籍的詩作當中極為常見:由身邊景物“觸而生懷”,其間雜糅著多種多樣的慨嘆,或是抒發歲月蹉跎之音、或是書寫生命憔悴之脆弱、或是寄寓孤獨思親的寂寞。同為真情流露,相比前代文人的抒情,阮籍這類詩作更多地融合了哲思的體悟,使得詩篇更加深遠、余韻悠長。而嵇康亦在《贈秀才入軍》、《與山巨源絕交書》等作品中,既流露真情,又將自己的人生體悟、元旨追求融入其中。而在這些文人看似不顧世俗禮教,似乎盡顯瀟灑風流的背后,卻是阮籍任車前行,無路可走時方停下來“慟哭而反”[20];是劉伶等一眾名士借酒澆愁愁更愁;是“非湯武而薄孔周”[21]的嵇康終惹殺身之禍。生死誰更傷?或許正因現實已是窮途末路之絕境,這些文人們才或逃避或無奈地選擇了借詩文以抒懷的方式吧。“誰可與歡者?”[22]“誰與盡言?”[23]一樣的痛苦,一樣的“絕處逢生”之佳作,一致的嗟嘆如斯。
三.潛入自然,聊以自慰
進入西晉,這個速盛驟衰的短暫王朝,政風表面上寬和到了極致,乃至到了爭相炫耀斗富的局面。這個時代的文人或自發地耽于富貴奢靡,或被統治集團拉攏而成鞏固政權的棋子。羅宗強先生說這個時期是“沒有大歡喜”“沒有大悲哀”,這個時期的士人亦是“沒有激情”[24],大抵是從哲思的角度而談的。而確如先生所言,這一時期雖然流傳有“二十四友”“潘江陸海”等美話,但這些文人中,除左太沖詩承建安外,大都一摒建安的慷慨和正始的玄悟,而是懷抱“士當身名俱泰”[25]的政治追求,多落得為之喪命的悲劇。
真正雕琢出上承正始玄言,下銜山水田園之風的,當屬陶淵明與謝靈運這兩位文人。此時西晉已被東晉所取代,前朝那近乎癡狂的感官享樂與物質追求,以及與之截然相對的官場血雨,讓西晉的文士們自覺地開始反思,開始關注國破家亡與自身的何去何從。在警示自己勿落前朝窠臼的同時,他們逐漸形成了一股益趨閑適寧靜的心態,所追求的境界也化為脫俗之美。但這樣的“改頭換面”是現實的慘痛代價換來的。在詩中自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26]的陶淵明,歷時三十年才永離“塵網中”。如此漫長的游宦生涯,豈全都是出于生活之無奈?若如此,那他便不會提筆而留“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27],也不會對祖輩“裕隆勸夏,豕韋翼商”的偉績贊嘆以“歷世重光”,更不會直抒“有志不獲騁”與“前途漸就窄”[28]。聯系具體背景,我們似乎也很容易聯想到,在門閥制度盛行的當時,出身寒微,始終被譏為“小人”的陶淵明,是多渴望建功立業以一掃冷言。或許正是因為官場黑暗,實辱士節,陶淵明才會寄身于田園之中,即使“草盛豆苗稀”[29],也能“悠然望南山”[30]吧。也正因這幾十年歲月的起伏沉潛,陶潛的詩文多了玄理與情思交融的理趣,頗有“質而實綺”[31]之美。的確,這是一位喜樂皆直言的“誠實”作家,既寫讀書時的“不樂復何如”[32],又記“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的蕭瑟、“傾壺絕馀瀝,窺炤不見煙。”[33]的落魄。這正如袁行霈之釋義:貧窮之狀,非親歷寫不出。淵明心中有不平,亦有疑問,所謂“貧富常交戰”,如此才真實。[34]但另一方面,淵明筆下的田園鄉村,似乎總是小宅屋舍、柳蔭桃李、村莊縹緲煙、吠犬與雞鳴的和諧交融[35],這固然真實而樸直,但這樣的恬淡情景卻是詩人主觀感情的強勢傾注——陶筆下的農村田園景色寧靜、淡雅,似乎是與官場的喧鬧與污穢截然相反的世外桃源,但一如詩人的情思并非局限于閑適情趣和田園暢意,現實的農村也并不完全是其筆下的那般美好。其言在此而旨歸于彼、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寫法,確使得最為平凡不過的炊煙、雜草都蒙上了一層道法自然、心境雋永的哲思意味,給人以無限遐想與啟示。但這背后是怎樣的矛盾心緒和痛苦掙扎,便不得而知了。
晚出生幾十年的謝靈運,與陶同屬返歸自然一派,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文風文貌。出生于家族鼎盛顯赫時期,卻逢士族地位下降的時代浪潮,這使得身擁才氣的謝靈運既有著狂放任性的肆意,又裹挾了憤慨與偏激的悲哀。而在家族財富與社會地位的矛盾作用下,誕生了謝靈運明麗豐盈、才氣精琢的所見所感。從《山居賦》的句子:“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羅行布株,迎早候晚。”[36]之中,可以看出詩人的家中境況。此時呈現在詩人眼前的并非炊煙渺渺、草盛苗稀的古樸鄉間,而是頗有得意、足稱豐腴的富意圖景。一如羅宗強所評:巖居穴處未必有詩,山水的美只有在生活溫飽的前提下才能從容領略。而這份源于家庭基礎的天生優越,在詩人的工筆興頭上便可窺見。[37]謝確實多記出游,而詩句中所寫的水之波光、夕暉暮色,似乎都被渡上了一層華美精致的外殼,以精巧的連續剪影之貌浮于筆端,最終化成“潛虬魅幽姿,飛鴻響遠音”、“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38]等佳句。但在謝靈運執著地以筆雕琢自然,將所見所感都凝練于才華盡顯的語言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詩人此番做法的原因。若從文學本身看,自然是謝靈運對陶淵明式的寫意與樸素心有不滿;從所處環境看,謝向內面臨著“仕”不達意、“隱”不甘心的矛盾,向外則屢遭彈劾、深受集團相爭之苦。由此看來,其暢言之意愜,似乎既包含山水愉人之樂,又是其借自然抒懷,暫別“進德智所拙”的無奈。如是而生的諸篇作品,便也是“絕處逢生”之作了。
隨著東晉結束,南北朝開啟,陶謝兩大名家也逐漸湮沒在歷史紅塵中。但歲月更迭,不敵人才輩出。一如沈約、謝朓等名士先后降生,中國文學的進程也在不斷演進,延續至今。四聲八病被一代文士們提出,似乎一經誕生便以其嚴苛肅然的面貌震懾著旁觀者與參與者。這近乎匠人色彩的細密規矩,與山水交融,與濃情相合。但涕泣如謝朓望鄉,發出“誰能縝不變”[39]的哀鳴;又如沈約有感別離,愁述“何以慰相思”[40]。名篇固然燦若繁星,點綴歷史的天空,但其生之痛苦,又有誰人曉呢?只希望如蕭統所信,椎輪大輅,踵事增華[41],歷史巨輪滾滾向前,前人之事業也能在后世中得以繼承,開出更加絢爛的花。
參考文獻
[1]黃侃.文選平點[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胡適.胡適文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32.
[3]宗白華.意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142.
[4]泰戈爾.飛鳥集·園丁集[M].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57.
[5]曹操.薤露行
[6][7][8][9][10]曹操.蒿里行
[11]淡懿誠.魏晉南北朝詩選評.陜西:三秦出版社,2004:1
[12][13][14]王粲.七哀詩.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3卷
[15][16][17]曹植.贈白馬王彪.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4卷
[18][24][37]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9][22]阮籍.詠懷.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3卷
[20]劉義慶.世說新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下之上
[21]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43卷
[23]嵇康.贈秀才入軍
[25]劉義慶.世說新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下之下
[26][29]陶淵明.歸園田居
[27][28]陶淵明.雜詩.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30卷
[30]陶淵明.飲酒
[31]葉嘉瑩.與詩書在一起[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32]陶淵明.讀山海經.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3卷
[33]陶淵明.詠貧士
[34]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5]陶淵明.桃花源記
[36]謝靈運.山居賦
[38]謝靈運.登池上樓.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2卷
[39]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北京:中華書局,文選第27卷
[40]沈約.別范安成詩
[41]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文選序
(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