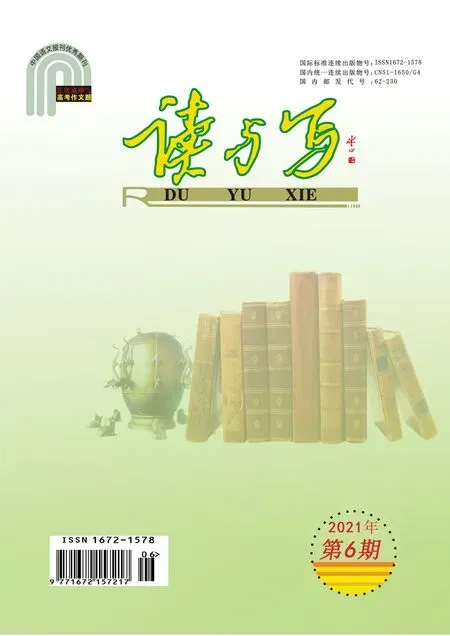基于單元整體的自讀課教學(xué)探索
——以《一棵小桃樹》《帶上她的眼睛》為例
陳以勒
(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溫州新星學(xué)校 浙江 蒼南 325800)
開發(fā)學(xué)生智力,培養(yǎng)學(xué)生能力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前教育改革前進(jìn)中的一個(gè)重要課題,“教育就是啟迪學(xué)生的智慧”這句話體現(xiàn)在語(yǔ)文教學(xué)上,是通過(guò)訓(xùn)練聽、說(shuō)、讀、寫來(lái)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語(yǔ)文核心素養(yǎng)。本文將以部編本初中語(yǔ)文教材七年級(jí)下冊(cè)第五、第六單元的教材為例重點(diǎn)闡述自讀課的教學(xué)實(shí)踐心得。
1.教讀課應(yīng)為自讀課做好準(zhǔn)備,打好基礎(chǔ)
教讀課教什么?在以往的傳統(tǒng)教學(xué)理念看來(lái),教學(xué)者一般通過(guò)整體把握、品味語(yǔ)言等手段來(lái)加深學(xué)生的理解和體驗(yàn),在沉浸式閱讀中,深化學(xué)生“原生態(tài)的感悟和思考①”。將課標(biāo)的學(xué)段目標(biāo)要求細(xì)化成一個(gè)個(gè)知識(shí)模塊,落實(shí)到各個(gè)單元中,形成了單元整體目標(biāo)教學(xué)(見下表:七年級(jí)語(yǔ)文教材各單元知識(shí)細(xì)化表)。

從表中不難看出,部編本教材的單元知識(shí)已經(jīng)形成一個(gè)循序漸進(jìn)的體系,學(xué)習(xí)閱讀這項(xiàng)技能,必須學(xué)會(huì)這一技能的“每一個(gè)分解動(dòng)作”。比如部編本初中語(yǔ)文七年級(jí)下冊(cè)第五單元的閱讀策略,是學(xué)習(xí)托物言志的手法,單元導(dǎo)語(yǔ)“建議運(yùn)用比較的方法閱讀,分析作品之間的相同和不同之處,以拓展視野,加深理解”。該單元編排的教讀課文是宗璞的《紫藤蘿瀑布》,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筆者預(yù)設(shè)了三個(gè)對(duì)比——“紫藤蘿花與瀑布的對(duì)比”;“文章兩處寫到紫藤蘿花的對(duì)比”和“紫藤蘿花與人的命運(yùn)的對(duì)比”。此外,在這三個(gè)對(duì)比中,向?qū)W生滲透“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篇內(nèi)比較”和“篇篇比較”的方法。
通過(guò)這兩個(gè)單元教讀課的教讀實(shí)踐,是為閱讀策略和閱讀方法的掌握提供例子和示范,也為后面自讀課的教學(xué)做準(zhǔn)備。
2.自讀課應(yīng)該是教讀課的應(yīng)用和價(jià)值體現(xiàn)
在每一冊(cè)教材中,教讀課和自讀課篇目的比例大約為3:1,所以就教學(xué)而言,或者就教材安排比例而言,教讀課是主體,自讀課只是補(bǔ)充,但是就教學(xué)效果甚至學(xué)生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而言,教讀是一種準(zhǔn)備,是一種基礎(chǔ)的儲(chǔ)備,更是架起課內(nèi)外融通的橋梁。
單元的存在,本來(lái)就是一種“類”的集聚和組合,所以,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一定要單元整體目標(biāo)的大局觀之下,理清單元課本中各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理清各語(yǔ)文要素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比如閱讀與寫作,知識(shí)與能力以及課文之間的共性與個(gè)性等。在部編本初中語(yǔ)文七年級(jí)下冊(cè)第五單元的第18課,賈平凹的《一棵小桃樹》中,作者明寫小桃樹的“身世”,同也時(shí)暗寫了作者自己的經(jīng)歷。這兩條明暗線索的敘述就使小桃樹和“我”建立了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是需要用“比較閱讀”的方法對(duì)比“小桃樹”的成長(zhǎng)歷程與“我”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的異同點(diǎn)以及二者之間的交叉重疊處。接著,在三處“交織處”的品味中,隨著“語(yǔ)言品味”的層層推進(jìn),三處之中的情感變化,也成了比較閱讀的另一種詮釋和運(yùn)用。在課堂的最后一個(gè)環(huán)節(jié),筆者將賈平凹的《一棵小桃樹》和宗璞的《紫藤蘿瀑布》進(jìn)行對(duì)比閱讀,讓學(xué)生在對(duì)比閱讀之中進(jìn)一步體會(huì)“托物言志”這一寫法在閱讀中的把握和在寫作中的運(yùn)用。所以從一進(jìn)入本文的“整體把握”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開始,一直到本課教學(xué)的末尾——“課外拓展延伸”環(huán)節(jié),“比較閱讀”這一單元知識(shí)目標(biāo)在經(jīng)過(guò)教學(xué)《紫藤蘿瀑布》一課時(shí)的學(xué)習(xí)準(zhǔn)備之后,一直貫穿課堂始終,并且順利抵達(dá)“托物言志”這一單元整體目標(biāo)。所以自讀課對(duì)閱讀方法實(shí)踐是教讀課閱讀方法學(xué)習(xí)的檢驗(yàn)和運(yùn)用,也是該閱讀方法在學(xué)生自讀經(jīng)驗(yàn)中的價(jià)值體現(xiàn),更是對(duì)新教材要“緊扣文本特質(zhì)和凸顯單元目標(biāo)”②的實(shí)踐探索。
3.自讀課應(yīng)該成為溝通課內(nèi)外閱讀的橋梁
在美國(guó)作家莫提默·J.艾德勒看來(lái),閱讀者“應(yīng)該是依照讀物的性質(zhì)和復(fù)雜程度,讓你用不同的速度來(lái)讀”③,葉圣陶先生也認(rèn)為對(duì)待每一篇文章“老是這樣細(xì)磨細(xì)琢……研討到三四個(gè)鐘頭,是不行的”④。他們都認(rèn)為,閱讀應(yīng)有快有慢,應(yīng)該在敏捷上訓(xùn)練提取重點(diǎn),應(yīng)該在速度上訓(xùn)練技巧。這樣看來(lái),閱讀能力的核心是體現(xiàn)在閱讀方法的使用上。
再看部編本初中語(yǔ)文七年級(jí)下冊(cè)第六單元的自讀課文——?jiǎng)⒋刃馈稁纤难劬Α芬晃模P者在教學(xué)中嘗試設(shè)計(jì)了一系列任務(wù)單。在通過(guò)對(duì)“瀏覽”這一閱讀方法的實(shí)踐運(yùn)用中,讓學(xué)生提取有效信息來(lái)完成任務(wù)單,試圖抵達(dá)“思考與質(zhì)疑”這一單元目標(biāo),在最后一個(gè)任務(wù)單中,筆者大膽嘗試將課內(nèi)閱讀延伸到課外,即讓學(xué)生根據(jù)本課所學(xué)的任務(wù)單內(nèi)容,自己設(shè)計(jì)《喂,出來(lái)》一課的任務(wù)單,并合作完成該任務(wù)單。總之,我們只有將教讀、自讀和課外閱讀融為一體,緊扣文本特質(zhì),凸顯單元整體,以傳授閱讀策略和方法為支點(diǎn),不斷激發(fā)學(xué)生閱讀興趣,從而抵達(dá)語(yǔ)文核心素養(yǎng)。就目前初中語(yǔ)文教學(xué)現(xiàn)狀而言,需要一線教師對(duì)自讀課重要性的更深層次的認(rèn)識(shí),才能將溝通課內(nèi)外閱讀的橋梁慢慢架起,讓學(xué)生能夠通過(guò)教讀課方法的學(xué)習(xí),在自讀課中的實(shí)施、運(yùn)用,并在今后的課外閱讀實(shí)踐中走得更長(zhǎng)遠(yuǎn),更穩(wěn)健。
注:
①章新其.《以科學(xué)態(tài)度推進(jìn)部編教材教學(xué)》.
②闕銀杏.《新常規(guī)之下的教學(xué)策略與指導(dǎo)》.
③摘自莫提默·J.艾德勒《如何閱讀一本書》.
④摘自葉圣陶《葉圣陶語(yǔ)文教育論集》.